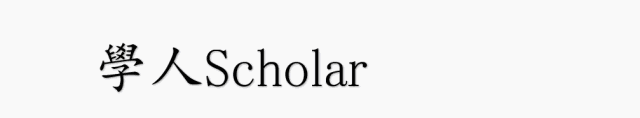福州黄巷葛家:葛兆光先生的家族史


独家抢先看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一
从籍贯上说,我是福州人,虽然我出生在上海。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兴填籍贯,所以我填表也好,办护照也好,各种证件上都写的是“福建福州”。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从小在福州长大,虽然大半生在上海、北京、天津和贵州打转,但终究叶落归根,近退休的年龄从贵州回到福州。一直到去世,一辈子操着浓重福州风味的普通话,他算是真的福州人。
葛家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之一的黄巷里,有一处老宅。在现在福州的各种坊巷志或者旅游书里,都把它叫做“葛家大院”,也算是一处名胜,这里就是我的老家。我父亲一直很得意地对我们说,葛家大院原来的大门口,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丹井传家远,黄楼卜宅长”,用了东晋道教中人葛洪的典故,说明这是葛家祖上传下来的。但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宅最早是不是葛家的,也许,在我的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时买来的,我父亲曾说,早年葛家大院的大门上方还悬挂了“中宪第”,二门还挂有匾额上书“会魁”二字,可我一直没有查出葛家哪一代有这么好的科举功名。所以,我怀疑这个院子原本是别姓的,只是葛家后来买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各种书里,它都叫“葛家大院”。传说中,它还是唐代一个叫黄璞的文人的旧居,传说晚唐黄巢闹事,大军越过仙霞岭,打到福州的时候,因为尊敬黄璞是读书人,下令不得焚烧这里的民宅,它才得以保存下来。但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几分想象,几分编造,谁也说不清。葛家大院毗邻另一个清代名人梁章钜的故居,两个宅子中间有一个“黄楼”,但长期以来,为了黄楼究竟应当归属谁家,葛家和隔壁争执了很多年。
老宅过去确实是阔气过的。据说,左右两边原来好几大片宅子原来都是葛家,院子里有七口井,一处池子,俗称“七星八斗”,花厅也有山石叠成的假山和雕梁画栋的亭阁,还有一处不小的水池。不过,1979年我第一次回到福州老家的时候,那个大院已经破败不堪,穿过原来很不错,可已经瘦身再瘦身的天井,七八家人已经把这个有些历史的老宅,分割得七零八落,原本有假山亭囿小池的花厅,也早已经堆满杂物,上面瓦间漏水也望见星星,下面则晴天满是晾晒衣物雨天满是接水锅盆。一直要到政府想发展旅游,重建三坊七巷作为旅游的景点,这才重修了大门,今年(2013)夏天我回去看的时候,原来很破败的大门,突然变得很古雅堂皇,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二
更有趣的是,在福州一些旅游书上,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传说,就是葛家出自古麻剌朗国。古麻剌朗国倒是真的,《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说,“古麻剌朗,东南海中小国也”,据说,大概位于现在菲律宾棉兰老岛,明代永乐十五年(1417),中国派了中官张谦去传达天朝诏令,海道遥远,张谦大概在那里待了三年。永乐十八年(1420),麻剌朗国国王幹剌义亦奔就“率妻子、陪臣随(张)谦来朝,贡方物”,永乐皇帝就给了他们如同苏禄国王一样的待遇,为他们颁赐了印诰、冠带、仪仗、鞍马等。可惜的是,这个国王回国路上生了病,永乐十九年(1421)便死在福建。于是,随同诸臣便留在福州为其守丧,因此寓居在福州,成了这一方人氏,传说中的葛家祖先就是陪臣中的一个。这原来是个故事,真的还是假的?不太清楚,记得当年福建电视台也来采访和拍摄过葛家,也许,是因为黄巷这里所谓三大姓“毛、萨、葛”都算是外来人口?萨家过去就是蒙元时代的色目人,传说祖上是雁门萨都剌,元末迁到福建。毛、萨、葛都是以前地方志里应当归入“流寓”的那一类人。不过,现在为了发展旅游,杜撰噱头,说这里曾经有过中外交流史上的“遗迹”,所以以讹传讹,我们也只能“假作真时真亦假”,随它去了。
葛家究竟来自哪里?过去,连我父亲也说得不太清楚,但没有疑问的是,葛家原来应该住在福州城外的洪塘国屿一带,我父亲晚年给我写信,说他小时候曾经去国屿的葛家祠堂参加过祭祖。1990年代那里大兴土木,要把过去的坟茔拆掉,曾通知葛家去迁祖坟,我二伯匆匆赶去,一块大碑已经毁坏,另一块小碑很幸运地保存下来,这是一块清代康熙年间的石碑,约高八十公分,宽五十公分,篆文题额为《皇清敕授儒林郎蔚庵葛先生墓志铭》。有了这块碑,我才把祖上的历史渐渐解开。
三
《皇清敕授儒林郎蔚庵葛先生墓志铭》碑文,是一个叫翁煌的人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撰写的,篆额的则是另一个叫林文英的,而书丹的则是自称晚生的蒋晟。据这位翁先生写的碑文说,蔚庵先生也就是我这个祖上,叫做葛焕(1647-1702),字子章,蔚庵是他的别号。给他撰文书丹篆额的三位,我没有专门去考察过,不过,看来都有些功名,但我的这位祖上蔚庵公,却好像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根据碑文记载,虽然他的祖先也曾在明永乐年间中进士并督学山左,但后来的子孙却很难跨过科举那道“荆棘之门”,蔚庵公也只是“少攻儒业,卒入成均”,并没有中过进士,据《福州侯官县志·耆旧录》的记载,只是一个监生而已。他可以被写出来夸耀的事情,主要是在当地作了一个有力量的乡绅和有道德的典范。据说,他“素好行善,闻人有义举,必心羡之,曰彼何幸,乃得好事行之?常出镪,为人完聚骨肉,匪直匍匐救丧而已。遇后生寒酸,出贽礼,劝之卒业,往往因而成名”。按照翁煌碑文的说法,“闽中盐政,不至大坏,实先生力也”。但是,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乡间儒生的善行,与福建的盐政坏不坏有什么干系?不过,他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乡绅,经营了洪江江山也就是国屿那一个葛家的基业。据说,他为了家族,先购买了“烝尝田”以防万一,也建造了七世坟地,把两百年来的家族坟地整饬一新,他又害怕老人寂寞,特别在城里买了夏屋,“迎奉入城色养”,不知道这个“夏屋”是不是就是黄巷的这一片老宅,如果是,那么这个宅子姓葛,至少也有三百多年了。
碑文里面说到,蔚庵公的先人讳回公,“由永乐进士,督学山左”,既然中过进士,似乎不像是从古麻剌朗国刚刚来的外国人,看来我们追溯上去,还是中国的读书人。一直到蔚庵公葛焕,仍然是“雅喜读书,款延师傅,训诲子侄”,后来,我父亲那一代葛家人,也曾延请了一个本家叔叔作私塾老师,从小就读四书。看来,“丹井传家远”,不是因为信了葛洪炼丹,而“黄楼卜宅长”倒是因为奉了孔老夫子,能读书的缘故。
四
按照碑文的记载,蔚庵公葛焕,先娶陈氏,续弦王氏,共生有子六女三,陈氏孺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大粱,蔚庵公去世的时候是“郡廪生”,次子大埏,那时是“国学生”,三子经邦,那时是“郡庠生”,都算是读书人。王氏生了三个,叫大培、大疆、大超,大概蔚庵公去世的时候还小,碑文中没有记载他们的身份。二伯曾经问我,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中间都用了个“大”字?为什么老三又偏偏名字又不用“大”字?我也讲不清楚。不过这以后,大梁一系的葛家,则按“元运开泰,保世滋昌,渊源孝友,欲振家声”这十六个字排辈分,我爷爷是“滋”字辈,我父亲是“昌”字辈,我本应是“渊”字辈,只是到了我这一代,天地翻覆,革除旧习,就再也不按照这个辈分起名字了,只有台湾大伯家的儿子还用这个“渊”字起名儿,而我弟弟葛小佳1990年代给国内写文章时,之所以用“葛佳渊”这个笔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诗经·唐风·葛生》),说的并不是葛姓的“葛”而是植物的“葛”,不过,葛藤覆盖荆棘,杂草蔓延遍野,倒也可以用来形容葛姓一族在福州逐渐生根。据我父亲说,蔚庵公之后支脉繁盛,我们就是长房大粱的后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似乎是中国的规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长盛的家族,除了官方护佑的至圣先师孔家之外。以前,潘光旦先生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说嘉兴有长达十几代一直兴盛的家族,代代出人物,这也许是比较少的,潮起潮落,兴兴衰衰,在中国传统时代的乡里很常见。葛家也不例外,蔚庵公之后,虽然家族还算是绵绵瓜瓞,但在仕途上葛家并不太兴旺发达,所以地方志、乡绅录里面也不见记载。
直到我爷爷投笔从戎,当了军人,福州黄巷葛家才好像真的要“重振家声”了。
五
我的爷爷葛滋承(1890?-1952),大概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和蒋介石、毛泽东等是同辈人,都是在乱世浊流里面混出来的。在这个中国社会重新洗牌的时代,人的命运很诡异。生逢世道巨变的人,或者从绿茵而辗转泥途之中,沦落下僚,也可能鲤鱼翻身跃过龙门,一下子成为人上人,全看运气如何。晚清那个时候,福州马尾办过船厂,办过船政学堂,办过最早的大清海军,黄巷的“毛萨葛”三家中的萨家,就因为办海军而出了很杰出的人物,这就是既当过大清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又当过民国初年海军大臣的萨镇冰(1859-1952)。我的爷爷不知道和萨家有什么关系,反正是远亲不如近邻罢,也作了这个大潮里的一个弄潮儿。1922年,当时的海军总长李鼎新派了杨砥中,在马尾成立海军陆战队的统带部,曾经发展很快,在福清、长乐、连江、厦门都有驻军,到1928年编为两个旅,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据说,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大概二十年代末,爷爷就从营长一直当到了海军陆战队混成旅的副旅长。
这里又有一件有趣的事儿。民国那会儿,也许当官需要资历或学历。我爷爷有学历,号称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学员”,算起来,和著名的叶挺、顾祝同、邓演达、薛岳,都是同一级的同学。保定军校原来是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在民国初年,名声仅次于黄埔军校,也是赫赫有名,1912年到1923年间共有九期学生毕业,里面出了很多战将。很多年以后,我弟弟在美国教书时,特意去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保定军校的资料,发现确实有“葛滋承”这个名字。可是,听我父亲晚年病榻上的叙说,才发现这是一个颇搞笑的故事。原来,我的爷爷压根儿就没去军校读过书,用他的名字去军校真的读了军事学的,是他最小的堂弟,也就是我的四叔公。换句话说,我爷爷用了四叔公的毕业文凭,而四叔公却用了我爷爷的考试成绩。中国这种冒名顶替之风,也许源远流长,不是现在才滋生出来的,难怪以前科举时代考试的时候,有作弊,有枪手,也有小抄。
更有趣的是,四叔公学成文武艺回来,却并没有货于帝王家。他毕业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却压根儿不愿意进入军界做事,原因据说是他发痴一样地爱上了一个女子,就是我后来的四婶婆,为了这个据说很漂亮的女子,他天天呆在家中。这也许可以理解,一方面四婶婆当年可能真的很漂亮,1990年代我在福州还见过她,从她老年时的相貌,也可以想见她年轻时确实很秀气;另一方面,我猜想是保定军校文凭写的是“葛滋承”,我爷爷凭了这个文凭可以当官,四叔公没有这个文凭,在海军就得从下层干起,从小受宠的他也许不愿意吃苦。所以,他就在我爷爷手下当了一个副官,据说是在庇护下吃干饷,根本不去当差,整天宅在葛家大院里面。不过,或许是因为我爷爷当了官,出钱把黄巷葛家大院又重新整顿一番,弄了好多葛家堂兄堂弟来一起住,就由我奶奶主管家务。顺便说一下,我奶奶叫何红蓉,中医世家出身,在福州也算名门,她的同父异母妹妹嫁给我爷爷的部下,这个人叫什么忘记了,后来曾在邱清泉手下当装甲师师长,1949年以后出走香港,辗转台北,最后定居美国,好像这位姑奶奶很长寿,一直到2000年前后,我弟弟还去加州她家去看望过她。在我奶奶的主持下,这个时候的葛家大院,似乎又兴旺起来。
我父亲葛耀昌(1922-2004),就出生在这个大院里。
六
父亲是爷爷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就是我的大伯,他比我父亲大不少,大学时代在上海学化学。据我父亲说,他上大学时常常出入舞厅,花钱如流水,差一点儿就娶了上海舞女,被我爷爷严厉制止,甚至威胁要断钱断粮才作罢。抗战后期,听说曾经到遵义火柴厂工作过,后来台湾光复,1946年就去了台糖就职。父亲下面有两个妹妹,就是我的五姑、七姑,也都随大哥去了台湾。我奶奶曾经短暂去过台湾,帮着照料大伯一家和两个姑姑,但1948年为了照顾我爷爷,又回到福州黄巷,此后天各一方,一直到死,也再没见过她的这几个子女。他们一直留在台湾,直到1990年代,他们和我父母亲才在香港再次聚首,那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据说,后来我的五姑和七姑到福州郊外去祭拜爷爷奶奶,哭得像泪人一样。
说起来,爷爷的四个子女中,父亲排行是老二,但葛家却用大排行。祖父一辈兄弟的孩子统统混算,我的大伯是老大,老二即我的二伯,却是我祖父弟弟的孩子,所以,后来我的堂兄弟们总是把我父亲叫三叔或三伯。他出生后葛家家境大概是最富庶的,所以,父亲的童年记忆都是欢天喜地,什么过年大吃大喝,什么福州坐大水的时候在天井划船等等。2003年夏天,他胃癌手术住院,我去医院陪护,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小时候的读书经历,他先是读私塾,由同宗一个当过云霄县知县的长辈坐馆,教他读四书,这位私塾先生也姓葛,就是祖爷爷之叔伯兄弟,据说很严厉,但父亲是爷爷奶奶宠爱的孩子,我猜想他当时一定学得不好,常常被打手板心,所以后来改弦更张,去读新式的英华学校,据说,在洋学堂里面,他旧学古文算好的,但是新学即数学和英文却不好,不过,英华学校很有名,总算后来也考取了当时设在上海的暨南大学。
可是,父亲上暨南大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暨南大学撤到福建,先在三明,接着在武夷山继续课程。后来,我父亲回忆这一段时光,最喜欢讲那时暨南大学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是何炳松是校长,不过,尽管何炳松是中国有名的大史学家,可我父亲并不学历史,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一个是他的同学里面,后来有一个当过副总理的吴学谦,但吴学谦后来当大官,同学从来也没有联系过,也没有沾过半点光;再有一个,就是他在福州家里带了不少洋钱出来,出来的时候,怕日本鬼子搜查,大洋都绑在腰上,所以,尽管当时山里的暨南大学伙食极差,但他可以时不时拿出大洋在茶馆里吃鸭子,这倒是真的,也符合我父亲那种老饕性格。我曾经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那时根本没有好好上课,他也毫不忸怩地爽快承认,他原来上的是法文系,但考试总不及格,于是,二年级转上外贸系,改学英文,好容易才毕了业,于是一辈子就干了对外贸易这一行。
七
海军陆战队的差事并不好做,抗战时期,海军陆战队很快就丢了船,海军变成陆军,我爷爷随着部队,辗转到了江西、湖北和湖南。1945年,中国八年抗战总算胜利的时候,我爷爷正在湖南芷江警备司令部任职,曾经亲历了日军投降仪式。不过,那时他已经厌倦了军旅生涯,就在湖南倒腾了两车药材,辞去了军职回到福州。也因为这个缘故,国共战争的时候他没有参与,1949年后这段戎马历史侥幸没有被追究,直到1952年患病去世,还算平安一生。
可是,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做事的父亲,却被簸弄到巨变之中。海关原本是常言说的“金饭碗”,可1949年前后他却失业了,生活陷入困境。那时,他已经与我母亲结婚,金圆券大贬值,人心惶惶,据说,那时他为了尽快花掉手里的钱,曾经急急忙忙拿一麻袋纸钞,匆匆地抢购了一件英国呢子大衣。尽管有我外公和爷爷两家作后盾,生活不至于无法维持,但是,他心里却很苦闷烦恼。我父亲原本性格就很不安分,福建人的性格也很勇于冒险,于是,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冀朝鼎的鼓动下,在我出生之前的1949年,就悄悄跑到已经解放的南京,进入共产党的军政大学学习。按照后来中国大陆政府的规定,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的人,可以享受“离休”即老干部的特殊政策,他也算赶上了这个尾巴,这是他后来很自鸣得意的地方,就好像当时灵机一动,买了一支好股票一样。
不过,尽管他一直很想跟随潮流,但潮流却总是在嘲弄他,一辈子都不得意。后来细细想,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来他的阶级成分不好,父亲算是国民党军官;二来他娶的是上海资本家女儿;三是四兄弟姐妹中有三个在台湾,也就是说他算“台属”。更要命的是,他结婚时的男方证婚人葛滋韬,也就是我父亲后来常常说到的“韬叔”,居然是军统特务,这个军统特务偏偏又是我爷爷的堂兄弟。后来我才知道,葛滋韬别名徐勉,抗战中曾经在军统的闽南站当过副站长,1948年我父母结婚的前两年,他已经去了台湾,转行办起了经济通讯社,大概那时正好在上海,就代表我爷爷做了男方证婚人。1995年我去台湾访问,还见过他和他的两个弟弟,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和善老头儿,并没有传说中军统特务那种凶残狡诈和深沉。可1950年代我父亲在向党“交心”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无所隐瞒,便把这个事儿说了出来,没想到这给他带来无穷的后患。尤其是,他还常常口无遮拦地讲一些自觉高明的话,这总让他的上司或上司的上司很不爽,所以,几乎每一次运动来了都不好过,申请入党好些次,党也始终不要他,可每次折腾,却都少不了折腾他,最终是每下愈况,一会儿从北京被下放到定县农村劳动,一会儿从北京被贬到天津当中学教员,最终又从北京被下放到贵州,在贵州东南的一个县城一蹲就是近二十年。
我从出生后,父母去了福州,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又到了天津,我却一直在上海外公外婆家住,福州黄巷葛家,好像与我没有太多关系。但1957年要上小学了,外公外婆下了狠心,让我回到父母身边。于是,沿着京浦线咣当咣当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当时在天津的父母身边。从此,福州黄巷葛家的历史,就开始和我的人生交集,我也从此一点一点地,融入了这个黄巷葛家大院的烟尘往事之中。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