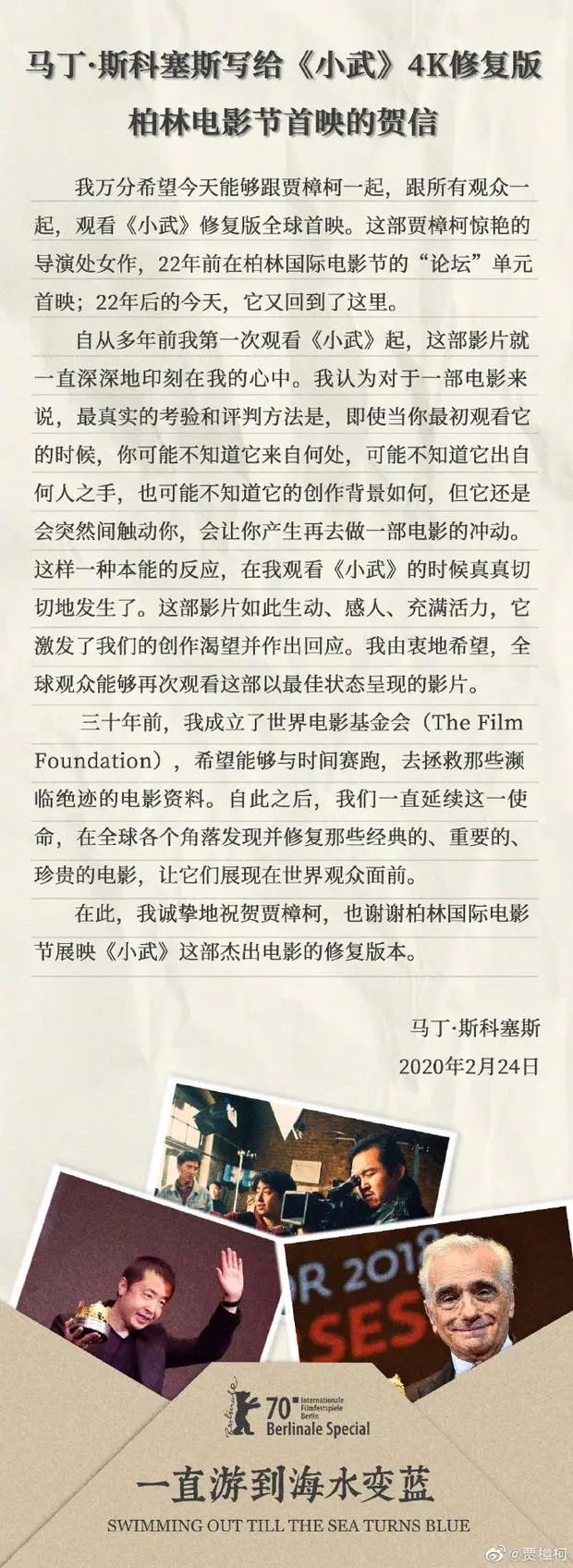贾樟柯:当年他如果拿起那把枪,美国就少了一个导演
于贾樟柯而言,参加刚刚闭幕的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一方面,国内的疫情让他深切关注,他也在新作首映式上发表了相关看法:
“我们出发时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来到柏林电影节,但我们来了。我们觉得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电影和人民一起存在。”(贾樟柯,2020年2月21日下午)
另一面,今年是他从这里出发,步入影坛的第22年——1998年,《小武》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并获奖。如今,《小武》又作为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庆典的特别节目,以高清修复版的新面貌进行了全球首映。
《小武》海报
本次《小武》的修复工作,由马丁·斯科塞斯创立的世界电影基金会组织。马丁·斯科塞斯,著名意大利裔美国导演,不久前,他执导的黑帮电影《爱尔兰人》入围第92届奥斯卡奖,此前,还有《赌城风云》、《飞行家》、《纯真年代》等经典电影作品广为人知。
马丁·斯科塞斯与《爱尔兰人》
2月25日,贾樟柯在个人微博发布了斯科塞斯写给 《小武》4K修复版柏林电影节首映的贺信。信中,斯科塞斯表达了自己对《小武》的偏爱,也深切呼吁经典电影资料修复的价值,全文如下:
我们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摘选自贾樟柯作品集《贾想》,也是关于二人的故事。18年前,贾樟柯和马丁·斯科塞斯因《小武》知遇,18年后,两人又为《小武》共同庆贺——这也为这部电影的“复活”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
在回忆录里,贾樟柯亲切地称马丁·斯科塞斯为“我的‘长辈’”,感谢他告诉自己要“坚持低成本”,这也是他将自己作为导演的理想、自由和创作方向贯彻至今的原动力。
《马丁·斯科塞斯——我的“长辈”》
作者:贾樟柯
1996年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念书,并不知道香港有许多外国导演和演员的译名,跟大陆的差距很大。
比如我们叫戈达尔,他们叫高达,我们叫特吕弗,他们叫楚浮。那时在香港独立短片展和余力为刚认识,闲来无事便一起喝茶吃饭,昏天黑地大谈艺术。我们谈了许多各自心仪的导演,他突然对我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对“马田”电影的看法,因为谈得抽象,没有涉指任何一部具体的作品,我听了半天不明就里,便问他马田是谁?原来他说的“马田”是拍《出租车司机》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他们翻译成“马田”,我一直以为是国内哪个姓马的导演,后来我们大笑,这也算是迷失在翻译中。
《出租车司机》剧照
在我学习电影的过程里面,马田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在导演技术上对我有很大帮助,那个电影应该是多机拍摄,能在整个切换过程里面,学到一种新的分镜的方法。以前我喜欢场面调度,在现场通过观察空间、想象人物的行为路线来进行场面的调动,以此解释剧情。《喜剧之王》则以人物的动作为分切支点,一个动作多个角度拍摄,多个角度拍摄的动作剪辑在一起,形成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1996年的时候电影的资讯还很少,人们对大师心怀尊敬并有神秘之感,马丁·斯科塞斯对学电影的学生来说,好像一颗璀璨的星星,高高在上无法靠近。
2002年我带着《任逍遥》参加戛纳电影节。马丁·斯科塞斯是短片单元的评审主席。当时听说他也在那里,就觉得自己那样热爱的一个导演现在竟住在同一个小镇上,或许哪天在街上就可以看到。
《任逍遥》剧照
有一天组委会请吃饭,突然外面大乱,就见一个矮个子的老人走了进来,很多人跟他寒暄,他的出场像一个总统。我没认出他是谁,他穿过人群寻找他自己的位置。这时我的日本制片在我旁边,突然用胳膊碰我,他说那是“马丁·斯科塞斯”。
这时候马丁·斯科塞斯已经走到我们旁边了,我站起来,跟他握手,我说我是中国人,那个时候我发现,在无数的人走过来、无数的手伸向他的时候,他的焦点非常地沉稳,他跟每一个人握手,都会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会照顾到每一个人。当他看着我的脸的时候,他说“中国”“长城饭店”,我用英语重复了一句“长城饭店”,他解释他80年代去过北京,住在长城饭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很快被人簇拥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从戛纳电影节回来之后,一天我正在家里糊里糊涂地睡觉,突然收到了一个传真,拿起来一看,没有想到竟是老马写来的。他在传真里面讲:“我在戛纳见过你,当时场面很乱。结束之后,我的助手告诉我,那个中国小伙子是拍《小武》的导演,我看过《小武》,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那个时候不知道你是谁,没有和你好好聊天。如果你到纽约的话,下面是我的联系方法,我们可以见一个面。”
贾樟柯、赵涛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现场
机会很快来了,差不多8月份的时候,纽约影展向《任逍遥》发来邀请信,我从来没有去过纽约,就跟制片人周强决定去一趟纽约。周强在纽约上的大学,毕业快十年了没有回去过纽约,他也想去看看。当然我们这次纽约之行多了一个节目,我们可以去拜访马丁·斯科塞斯,要去跟他见面。我们给马丁·斯科塞斯发了一个传真说几月几号放《任逍遥》,会去纽约。很快他回信说,他正在忙《纽约黑帮》的剪辑工作,但他会协调一个时间,见一个面。到10月份,我和周强两个人拖着行李上了飞机。
电影节的活动在林肯中心,肯·琼斯来找我,他是林肯中心的节目策划,写了非常多关于东方电影的文章,是在美国推动亚洲电影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认识是在1999年的旧金山的电影节,他那年当评委,不仅颁给《小武》最佳影片,还把《小武》的录像带给马丁·斯科塞斯,因为他还是马丁·斯科塞斯的助手,所以马丁·斯科塞斯能看到《小武》。他在不同学校交流讲学的时候经常介绍《小武》,包括推荐给斯皮尔伯格。其实在美国,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没有很多的壁垒,像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也是从实验电影过来的。
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克
去他办公室所在的公寓,进了电梯之后,发现电梯里人很多,我和周强都没有说话。同去的还有他的助手肯·琼斯,琼斯个子很高,我仰头看他,他一直在笑我,我有些不知所以。一回头看到马丁·斯科塞斯就站在我的旁边,大家马上笑了起来。那时我觉得我有一些紧张,但这紧张很快在笑声中消失了。
进了他的办公室后,桌子上已经摆了很多点心,我觉得有一点像小时候去看长辈的感觉。大家坐好之后,沏了中国的茶,他说你吃一点,是特意为你们买的。那是些意大利的点心,这时你会觉得我们不是为电影而来,只是来探望一个长辈。他一直冲我们微笑,像看一个孩子,他自己不吃,我们吃了很多点心。
我们从《小武》开始聊起,我以为他会从专业的角度进入来谈这个电影,但不是。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吗,我说可能我拍摄的人的阶层,人的那个处境,跟你最初拍电影的时候喜欢拍摄的人一样。他说你只是说对了一半,你拍摄的这个人非常像我的叔叔。
他说:“叔叔是在意大利街区工作的,有一年假期我跟他说我要挣钱,他说你第二天来办公室吧。结果他给了一张写着地址的纸,发了一把枪给我,说你给我去追债,把钱拿回来。”马丁说他当时拿着枪都哆嗦,幸亏没有去,如果去追债的话,可能美国就多了一个黑帮,少了一个导演。他说小武这个人好像他自己的叔叔,看到王宏伟在电影里面晃来晃去,就好像看了他的叔叔一样,特别亲切。
《小武》剧照
做导演太久了,很难变成一个普通的观众,但马丁没有。他跟你谈电影,没有谈调度怎么灵活、结构怎么样。他只说他的叔叔,只说他的往事,我觉得他可以全身心进入电影,又可以从电影出来,就像一个得道的老妖怪可以随意畅游。
谈话的中间突然有送快递的人进来,交给他一个邮包,打开之后是加州大学的学生寄给他的作业。我问他教书吗,他说不教书,我问他那为什么有学生来信,他说我这里是公开的,谁都可以寄作品来。我非常感动。我自己刚拍短片的时候多需要人帮助啊。
但他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你不要以为是我帮助他们,其实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是他们在帮我。我每次看到这些学生的作品,就可以知道我有多老,我是上个世纪的人,他们做的是新的电影,他们教我知道什么是新的电影。此话一出,屋里变得非常安静,每个人都被他的话感动。
《纽约黑帮》幕后,马丁·斯科塞斯与莱昂纳多
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说他准备去剪接,要肯·琼斯陪我参观他的电影资料库,他有几百个电影拷贝的收藏,三十五、十六毫米的拷贝,LD、VCD、DVD、VHS录像带都有。横跨了很长时间,我看到布列松的、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拷贝,我问肯·琼斯:他看吗?他说:经常看。之后我们去他的放映室,助手说他会抽时间在这里看他喜欢的电影。我看到这些,心想将来一定要印一个《小武》的拷贝送给他。
他的工作环境,以及整个办公室的结构,会让人感觉他整个人都生活在电影中,这里不是一个抓经营的办公室,而是一个制作车间,是一个热爱电影的淘气孩子的玩具室。参观结束,马丁也准备好了他的剪辑工作,有一个老太太在那里和他一起工作。
他介绍她是从70年代拍短片一直合作到现在的剪辑师,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男的,有点像司机,马丁又介绍说,这是我一直合作的编剧,我们从《纯真年代》开始合作。他有自己的一个电影团队,都是老友,风雨几十年的搭档。他们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他们是艺术上的合作者,是在艺术上可以互动的同事,同时又像是家庭成员,非常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
我们在剪辑室里看他工作,他在剪辑开场打斗的场面,他突然停下来对我说:“我昨天看了《战舰波将金号》,我有很多疑问,我要问爱森斯坦。”说完了后他继续他的工作。他工作的背景是整个电影历史,不但有当代电影,还有20年代的默片,你会觉得他工作的参照系统是全人类完整的电影经验。我一直在看,看他怎么跟工作人员交谈,他们非常默契。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占他时间太久了,就和他告别。大家一起走出办公室,在我上电梯的时候,他突然招手,我走近他,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保持低成本。”然后转身回了办公室。
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大家谁都没有说话,每个人都在想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所谓保持低成本,他的意思是坚持一种理想,一种导演的自由,一种创作的方向。强调保持低成本,也是他正在面对的困境,当时他的那个电影投资一亿多元,投资公司要求他们将片长剪短,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争议。这句话是他对我的鼓励,也是对他自己创作困难的表达。突然间我的心里又多了一些对这个老人的怜惜。
原载《生活》第三期(2006年)
本文节选自
《贾想 I :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