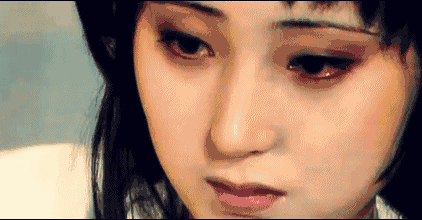林黛玉对爱的期待,化解了贾宝玉的混沌


独家抢先看
0 1
当歌德在《浮士德》中写上“永恒的女神,引导我们前行”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无意中道出了一个为人们尤其是男人们所忽略的事实:正如历史创造总是由男人承担的一样,男人本身又总是由女人启悟和塑造的。虽然夏娃来自亚当的肋骨,但偷吃禁果的一刹那却由夏娃传递给亚当。在女人的灵性面前,男人往往显得不无迟钝。假设这世界上没有女人,男人就会变得浑浑噩噩,如同一汪死气沉沉的泥潭。女人是人类这具有灵性的动物中最具灵性的部分,如果人们把自己称为文化动物的话,那么女人便是一道永恒的文化灵光。
◎春去夏来,芒种前后的大观园大概是最美好的时刻。
男人对女人的持续不断和不知疲倦的追求,乃是他们对于这道灵光的永恒向往。
经由这道灵光的照耀,男人才完成了自身人之为人的构建。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伊里亚特》中,海伦造就了整整一代古希腊英雄连同特洛伊男子汉;同样,在塞万提斯的笔下,没有杜西尼娅的这道阳光,唐吉诃德形象就无以成立。如此等等。
◎《伊利亚特》里的海伦
或许是西方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这种秘密,他们有了辉煌的骑士时代,有了那个“Ladyfirst”的人文传统。遗憾的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呈现出来的正好是相反的愚昧颟顸。一部二十四史,只见男人的蛮横,不见女人的灵光。早先的女娲形象,在这部历史中不是被视作褒姒或杨贵妃式的祸水,便是如同西施和王昭君那样被男人政治玩弄于股掌。这种昏暗在文学作品尤其在《水浒传》那样的强盗小说中尤为可怕。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杨雄杀妻,一个个全杀得理直气壮,豪情满怀。
女人本来就是爱情的象征,但她们被贬被杀的理由恰好仅是偷情或媚人的罪名,一如晴雯的枉担虚名,含冤屈死。按照这种昏暗的逻辑,假如特洛伊战争发生在中国,那么战争的内容就不是攻打特洛伊城,而是争相杀死海伦。女神般的海伦在中国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站在断头台上的妖怪。
历史的野蛮就是这样形成的。女人作为人本意义上的灵物与爱情俱绝,从而只不过是男人采阴补阳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器皿。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年代,人们才逐渐看见了诸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这样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如同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使这个昏暗的世界初露晨曦。
02
这就是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文化背景。
作为大观园中神明般的少女,林黛玉形象荟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优秀女子的全部灵气,以其惊人的才情卓然而立。
过去在《西厢记》、《牡丹亭》、《金瓶梅》一类小说戏曲中被小心翼翼晦暗不明地展示的放浪美丽,在林黛玉形象如同一轮朝日喷薄而出。人格的独立,灵魂的自由,第一次在这个少女身上获得了生动的体现。其意味的动人一如夏娃刚刚睁开眼睛看见亚当、看见伊甸园、看见自己的一刹那。
为此,夏娃受到了生育痛苦的惩罚,而林黛玉遭到的则是无望的爱情期待。
同样的悲壮在《创世纪》中被诉诸创造的苦痛,在“世纪末”中被诉诸期待的无望。前者是女人为历史付出的代价,后者是少女为灵魂作出的奉献,这种奉献形式的结构不是向……爱情的期待,而是向……期待的爱情。
这种的爱情形式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叛逆。因为在以往那些云遮雾障的爱情故事中,爱的指向不是奉旨完婚式的世俗认同,就是入梦化蝶式的畏惧退避,更不用说那种对浊男的绝对依附。既然在一部没有爱情的历史和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上,爱情本身就意味着无望,那么还不如在指向上将它付阙:既不指望奉旨完婚,也不幻想双双化蝶,而是以一个等待的形式傲然伫立;等待自身,等待未来,等待戈多。
正如在贾宝玉的形象结构中灵魂先行自身一样,在林黛玉形象结构中,先行自身的是无望的爱情期待。由色而空的形式结构,在林黛玉形象是由浇灌到还泪;因此,色的空,在此呈现为浇灌的还泪。由于浇灌的不可能在世复现,还泪便成了期待着的过程本身。
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过程。亚当的肋骨之于夏娃的先行规定性,在此被诉诸了诗意十足的浇灌。须知这浇灌前提蕴含了多少男欢女爱的历史内容。远溯《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后有曹植《洛神赋》的淋漓云雨,飞扬神采;及至宋明之际,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几乎写尽了男女床笫之间的现世欢乐。然而所有这一切两性间的创造性欢娱,在《红楼梦》里全都被抽象为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即神瑛侍者之于绛珠仙草的浇灌。生命由此定格为一个优美的造型,凝练的线条自上而下飞泻流动,草木有知,泪水涟涟。美丽的故事就这样生成了。
以浇灌为先行自身的林黛玉形象,以还泪为其在世形式。当贾宝玉认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时,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林妹妹是泪水的化身。泪水为水中至尊,不是自然的天地之气,而是灵魂的现身形态。也许正是泪水的这种至尊意味,才有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当然,林黛玉作为泪水形象还不啻是对暴虐的抗争,因为与这泪水直接对应的灵魂形态乃是作为贾宝玉形象原型的顽石。宝黛爱情的在世形态,由于抽象了色的前提,变成为以泪洗石的凄婉意象。
毋庸置疑,无论是大观园之前还是之后一段时期内的贾宝玉,是稚气的,混沌未开的。而且,他的这种天真起初与史湘云的蒙昧极为相近,直到有一次他听见史湘云规劝他立身扬名时,才将对方与自己断然划分开来。这种稚气和混沌,用小说中的说法便是玉的蒙尘。蒙尘是贾宝玉寓世沉沦的必然方式,尘世的诱惑即便在这天分极高的少年,也不是没有魔力的。再说,按照由色而空的逻辑进程,不经由蒙尘,又何来的清澈?需要指出的只是,忠心耿耿的洗尘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被世人讥讽为小性儿的爱哭的尖刻的少女林黛玉。
《红楼梦》的读者十有八九不能理解林黛玉没完没了的哭泣。人们往往按照世俗的生存原则衡量这样的哭泣,从而作出世俗的人际评判。殊不知,正是林黛玉这一次次的哭泣,一点一点地洗净了那块沉沦寓世的顽石。想当初贾宝玉是多么的蒙昧糊涂,既倾心林黛玉之灵巧,又仰慕薛宝钗之仙姿。即便在听到《葬花辞》恸倒山坡的当口,内心深处也是将林黛玉、薛宝钗乃至袭人、香菱搅作一团,这与其说出自性爱的弥散状天性,不如说缘自贾宝玉与生俱来的稚气。而尘世的混浊,又不断地将这稚气混同于须眉浊物的浊气。每每在这样的当口,林黛玉一场泪雨倾盆而下,使天地间顿时变得清新起来,从而使贾宝玉获得沁人心脾的空气,焕然一新地面对沉沦着的世界。然而,泪为灵魂之形,毕竟又终有尽时。“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林黛玉泪尽之时,便是贾宝玉彻悟之日。
且不说林黛玉奔月时刻的如何凄绝人寰,即便是晴雯之死,也已经使贾宝玉写出了如同“毁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那样的激愤之言,更何况林黛玉泪尽时刻对贾宝玉的沉痛打击。因为宝黛爱情那种在世的还泪性质,致使宝玉这块顽石离不开泪水时时刻刻般的洗涤。在此,爱的快感在双方全然集中体现于泪的痛楚。事实上,无论按照心理逻辑还是生理科学,往往是哭而不是笑成为爱的高潮。林黛玉的眼泪是对贾宝玉最为兴奋的刺激,而且刺激所至,直抵灵魂。一个是爱哭,一个是爱见哭。这就好比当今歌星之于听众观众,林黛玉因为有贾宝玉这一天生的知音和感应者,她才哭得其所。如果说,贾宝玉的灵魂以顽石为形,那么林黛玉的灵魂以泪水为状。泪不尽,石不醒;泪尽石醒,人去园空;一个奔向月宫,一个悬崖撒手,整个美丽的故事就这样结束。
03
还泪使林黛玉成为引导贾宝玉前行的女神,还泪的这种在世形态使宝黛爱情以向……还泪的结构互相关联。泪水在林黛玉意味着无尽的期待,在贾宝玉意味着不断的净化。山石无水则不灵秀,宝玉没有黛玉以泪相洗,也许会与贾琏无异。泪水规定着林黛玉的形象造型,也造就了贾宝玉的返璞归真,使由色而空的灵魂自我实现成为可能。这是一幅绝美的还泪图:透过迷蒙的泪雨,一个看见了自己的知音,一个找到了导引的女神。这是眼泪之于双方的关联结构,也是小说所叙的那条灵河的寓意所在。灵河者,林黛玉之泪河也。灵字既谐音于林黛玉之林,又意寓了灵魂的灵意。
与泪水构成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的在世形态相应,这一在世形态的特征便是期待的焦灼以及与这焦灼有关的尖刻。“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几乎就是这位期待者的自画像,而“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则道出了环境的险恶和生存的紧张。如此焦灼和紧张将这个病如西子的娇弱少女折磨得心力交瘁,但同时又将其口锋砥砺得如同一把锋芒毕露的利剑。林黛玉不是一个斯巴达克斯式的斗士,但她必须面对与她为敌的整个世界,并且其险恶不亚于斯巴达克斯在斗兽场上面对的景象;构成与生命的草木质地与形成巨大反差的外部世界的沉重高压,迫使这个泪流满面的少女以其犀利的口锋傲然相向。
所谓林黛玉式的尖刻就是这样形成的。
林黛玉那种心较比干多一窍式的玲珑剔透和敏锐细腻的惊人才华,除了洋溢于一首首凄美的诗作,几乎全都倾注在她之于世人的尖刻上。天生的高洁品性,使她睥睨一切,皇帝在她眼中也不过一个臭男人而已。既然本来就是世外仙姝寂寞林,除了对爱情的无望期待一无所有,那么任何装模作样的言谈举止都成为多余。纯真的心地在此体现为惊人的坦率,见一个打趣一个,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世人的种种丑陋和可笑。女儿本来就是水做的骨肉,更何况这颗泪做的灵魂,在这种罕见的晶莹面前,任何世俗的浊物都难免心惊胆战和自惭形秽。当然,也正因如此,林黛玉形象才招致世人的种种非议。这与其说是非议对象提供给非议者以非议的口实,不如说是非议者面对这种高洁时的卑怯和嫉恨。
因为人世如此污浊,即便上帝开口也不会美言相向,何况林黛玉这样的烂漫少女。当然,人们不敢对上帝放肆,因为上帝教诲人类反省自身的方式通常不是采用告诫,而是诉诸洪水、灾荒、瘟疫、战争之类的惩戒。相形之下,林黛玉式的尖刻毕竟只是温和的告诫,只伤面子不伤身,致使在听惯了皇上圣旨和上级命令的世人那里非但不觉得震聋发聩,而且还敢嬉皮笑脸地胡乱诋毁;即便小说再三点明林黛玉的仙子来历,人们也照样无动于衷。由此可见,贾宝玉的确是非凡的,因为唯有他在林黛玉的尖刻面前不是感到咄咄逼人,而是显得毕恭毕敬。他知道林妹妹从来不说混帐话,林妹妹一开口,不是揭露谎言,就是说出真相。事实上,仔细想想林黛玉的所谓尖刻,其中又有哪一句说错,哪一件事说偏,哪一个人说走眼了呢?世人如果能有贾宝玉那样的灵悟,也许就不会在这种尖刻面前忐忑不安了。
◎“我所居兮,清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我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04
一方面是流向贾宝玉的眼泪,一方面是指向世人的尖刻,构成林黛玉作为期待者形象的两个侧面。当然,在林黛玉的期待中不无对婚姻的指望意味,但这种指望不是薛宝钗式的攫取利益,而就是林黛玉式的实现爱情。虽然就爱情的本义而言,仅仅是两个人的对话和权益,但在中国社会及其历史上,这个两人之间的愿望从来没有在两个人之间实现过。因为且不说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本身在历史上具有多大可能性,即便可能,也必须通过张生和崔莺莺式的奉旨完婚才能兑现。
爱情必须经由婚姻的包装,而婚姻本身又绝对不考虑爱情。尽管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婚姻向来就是群体性的家族事务。在《红楼梦》里,人们可以读到大量的婚姻事例,不仅与当事人双方毫无关系,而且家族统治者将当事人推入他们所设计的婚姻事务中时,冷漠得就像在从事牲口买卖一样。按照这样一种群体性的组合规则,当事人的婚姻愿望只有在与家族利益全然一致并且同时也成为家族统治者的择配意向时,才有可能如愿以偿。
薛宝钗遵循这样的规则,因此获得了她想拥有的婚姻,尽管这婚姻所实现的与其说是她的个人情感不如说是其家族的利益。然而,在这样的规则面前,林黛玉恰好是个犯规者。她所指望的婚姻除了自己的爱情愿望什么都不考虑,这就注定了她那爱的正当愿望和权利与家族联姻的世俗利益和权力之间的冲突及其悲剧性的结局,更何况在她的爱情要求中所蕴含着的,还是过于理想化的纯洁和高尚。
以泪水为形态的爱情期待对于净化贾宝玉的灵魂固然至善至美,但这种期待之于浇灌这一性爱本身的追求而言,却纯洁得令人怵然。这就好比纯情少女之于初恋对象的理想化规定,苛刻得足以让对方发疯。清纯的泪水可以洗涤灵魂的污垢,但难以将爱情推入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正如大观园此景只应天上有一样,林黛玉的此情也只有在天国才能实现。即便是西方爱情故事中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之类的纯情程度,也及不上林黛玉所期待的爱情之晶莹。由于情的高洁,所以爱得苛刻。如此的缠绵悱恻和铭心刻骨,在一般的凡夫俗子不是魂飞魄散,便是逃之夭夭。然而,爱情的灵魂维度就在这样一种爱情理想中被确立起来,掠过尘世的丘陵沟壑,如同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一样,直指高远的天空。
在林黛玉期待的爱情面前,人们可以看到又一种天、地、人的结构方式,即与妙玉、宝玉、湘云结构相似的黛玉、宝玉、宝钗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林黛玉象征着天空,贾宝玉象征着世人,薛宝钗象征着浊世。天空是贾宝玉先行自身的导引女神,世人由林黛玉的在世形态泪所洗沐,浊世是贾宝玉寓世沉沦的生存共在。
在此所谓木石前盟乃是天国的灵魂之盟,所谓金玉良缘则是世俗的利益联姻。灵魂与利益经由贾宝玉这个人的环节碰撞冲突,最后各得其所:林黛玉得其灵魂,将贾宝玉引渡向天国;薛宝钗得其躯壳,把贾宝玉拖入世俗的婚姻泥潭。换句话说,贾宝玉的灵魂交付爱情,其躯壳则抵押给婚姻。这种爱情和婚姻、灵魂和躯壳、天国和尘世的裂变和各自归位,结束了大观园世界的一切景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所谓“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片死寂的景象。
由此可见,林黛玉期待的爱情不是世俗的、色欲的,而是精神的、空幻的。人们可以说这种爱情因其浓郁的理想色彩而虚无缥缈,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这种虚无缥缈竖立起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文维度,斯宾格勒将这一维度称之为第三进向,亦即在平面的长和宽之外的第三个维度:高度,或者纵深。人之为人不是因为其世俗的平面的生存进向,而是由于其精神主体的存在空间。人凭借这第三进向在精神上(而不只是在生理上)站立起来,成为万物之灵。而林黛玉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展示了她所具有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
相对于贾宝玉的混沌未开,林黛玉可谓灵性十足。她一跨进贾府便留意到各色人等的差别异同,诸如贾母的怜惜,凤姐的喧哗,邢、王二夫人的深藏不露,赦、政二舅舅的避而不见,更毋须说,在众人中一眼认出那位“倒像在哪里见过的”表兄贾宝玉,一个命定的知己。正是这样的灵性,什么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无论是凤姐的花胡哨,还是薛宝钗在佩物上的特别留心,抑或贾宝玉用心不专的飘忽摇摆,她都能一针见血地当场点出。如此惊人的敏锐不是可以用天资聪颖一类判断解释得了的,因为这种资质所基于的乃是人格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
05
当年鲁迅曾感慨地说,一部《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者,独宝玉而已”。我不想在此贬低鲁迅的判断是否偏颇,但可以肯定的是,《红楼梦》中领会悲凉之雾者不仅不独宝玉而已,而且首先不是宝玉,而是作为无望的爱情期待者林黛玉。是林黛玉在《葬花辞》中率先感受到生存的紧张,是林黛玉在《五美吟》中大胆颠覆了昏暗的历史,又是林黛玉在《桃花行》中深切领悟到大观园世界的末日将至,更不消说这位少女以泪洗玉的艰苦行程,使贾宝玉得以一步步趟过尘世的污泥浊水,完成向天空的最后飞跃。
除了因为天性善良,这位少女在薛氏母女的兰言爱语下曾经蒙受过伪善者的欺骗,她在整个故事中始终不合流俗,傲岸卓立。在省亲场面上,她写出“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清新诗句;在杯光觞影中,她于行酒令的当口脱口而出的是《牡丹亭》和《西厢记》的词文。她会不假思索地随手扔掉皇上经手的赐物;而面对薛宝钗的“珍重芳姿昼掩门”,她就是展示出“半卷湘帘半掩门”的风流潇洒。她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她更不趋炎附势,如同薛宝钗那样审时度势地朝贾母说上句把中听的话,或者点上一出老太太爱听的戏文之类。
她的副本形象晴雯尚且身为下贱而心比天高,更何况她自身在爱情追求上的执着连同与此相应的对自由的渴望。她不是不明白她的爱情期待究竟有无希望,但她抱定“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人生宗旨,心甘情愿地走向无望的天空,“一抔净土掩风流”。可见,她那红拂般的卓然识见,来自她不畏赴死的决心和不入浊流的心胸。毋庸置疑,这意味着她将付出什么样的生存代价,然而,人的维度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这里不再奉行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的苟活原则,而是昂然宣布:不自由,毋宁死!
◎晴雯撕扇
这样的人格和灵魂断然扬弃了生存的圆滑,从而张扬出精神的高贵连同存在的诗意。生命在此不再顺从于生存的烦忙,而是指向体验的辉煌。也就是说,在这里的原则不是世俗利益的获得,而是人生审美境界的抵达。
所谓第三进向,在此全然体现为生命的审美观照。
正是这样的审美观照,人们可以在林黛玉的爱情期待中领略到当年党锢气度、魏晋风度那样的贵族神韵。毋须任何标榜,其间诗意自在,灿烂闪烁。因为人格的高标,便有了灵魂的如此光芒。过去在李白、杜甫乃至苏东坡、辛弃疾等等须眉骚客的诗词作品中没能读到的璀璨诗意,此刻全然闪烁在了作为《红楼梦》诗魂的林黛玉形象及其一篇篇歌吟中。
相形之下,李白的佯狂、杜甫的忧伤、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辛弃疾的“栏杆拍遍”,在这样的诗魂面前全都显得不无做作。不管这些男人们如何手舞足蹈,捶胸顿足,由于他们在人格上的不独立和灵魂深处的不自由,不是有失尊严如李白,就是流于贾政式的所谓方正清肃如杜甫;苏、辛二位算是宋词大家,一放开喉咙便是铺天盖地,一会儿擎苍牵黄,一会儿金戈铁马,可惜不过是一派豪放的浑浊;而且越豪放越浑浊,越浑浊越豪放。这股浊气最后酿成一幕抱起孩儿皇帝奋力投江的忠烈喜剧,让人弄不清楚那位宋末忠臣究竟是留取了丹心还是犯了谋杀罪。难怪《红楼梦》选择从女娲补天开卷,因为作者实在是被这么一部须眉浊物的历史伤透了心。
0
以泪洗面的在世内涵,焦首煎心的期待过程,尖锐犀利的面世口锋,卓然高贵的人格灵魂,这一切构成了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的形象造型。这一造型与小说开卷处的女娲补天形成一种互补性的象征意蕴。如果说,女娲补天在小说中意味着对历史的感慨以及对重创历史之可能性的向往,那么林黛玉作为一个爱情期待者形象所寄托的则是为《红楼梦》所独具的人文精神。
这种精神的主要内容在于:是女人,而不是上帝,塑造了作为历史主体的男人;因此,要想把一部陈旧的历史翻向新的一页,首先应该确立的不是象征着力量的男人,而是象征着审美的女人。因为坚实的石块要成为美玉,得经由流水的洗濯,或者说,浑浊的力量经由审美的观照才会显得厚实而不愚昧。力量本身总是蒙昧的,没有女人的灵性加以导引,就会使历史充满血腥的暴虐。
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发现人是万物之灵的时候,真是应该再补上一句:女人乃是万物之灵中最有灵性的部分。正如男人如同石块,坚实,浑厚,象征着力量和创造;女人好比流水,清灵,柔美,象征着理想和审美。男女之间在天然质地上的区别,造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司空见惯的性别指向,男人永远倾心女人的美丽,女人永远崇拜男人的力量。
由于男人天生的物质性,他们在心理指向上始终渴望精神的审美的世界;又由于女人天生的精神性,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趋于物质的世俗的烦忙。因为男女共同的天性在于,自身缺少什么就渴望和倾向什么。当人们说男人总那么好色,是因为作为力量的象征,他们缺少美的灵气;而当人们说女人往往很物质很具体时,则是因为她们本身太精神太抽象太审美太虚无缥缈。有了山峦的坚实险峻,却企盼行云流水的飘逸轻盈;有了流水的清澈晶莹,又希望拥有群山诸峰的伟岸超拔,如此等等。因此,《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孩儿家玩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浊物——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揭示出了历史创造的人自身创造的全部奥秘。
当然,这样的奥秘是在两个向度上揭示的,一个是女娲补天的向度,一个是林黛玉向……期待的爱情向度。人们在补天向度上读到的是有关历史创造的神话,在期待向度上领略的则是有关人自身创造的意象。
作为上帝的现身,女娲示演了她的炼石补天。如同《山海经》所记载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故事一样,历史的创造在此不是以具体的史志而是以象征的叙事呈现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补天者是女娲,但实际上补缀天空的却是女娲所创造的炼石。如果说女娲是与耶和华一样的上帝形象,那么炼石就如同亚当那样是上帝所创造的男性造物。上帝制作亚当或者炼石,但他并不直接创造历史。这是上帝作为造物主的本义所在。因为历史的创造是由男性造物们直接承担的,即便是像蛇和梅菲斯特这样的撒旦形象,也只推动历史的创造而不直接参与其中。直接的创造者角色由亚当或浮士德扮演。然而,当我说男人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时,同时又意指女人是历史创造主体的创造者。这之间的关联在于:正如男人总是面对历史一样,女人总是面向男人。
男人要通过历史的创造显示其在世的力量,女人往往通过对男人的创造而拥有世界。
就男人而言,他通过创造与历史合一,同时又通过女人与自然相接;就女人而言,则是她通过男人与世界合一,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自然意味塑造男人。这样的创造链环在创世纪时代,可以说是秩序井然的。蛇将创造的秘密告诉夏娃,然后夏娃再告诉亚当,最后亚当揭开蒙昧时代进入艰苦的创世劳作。同样,在《伊里亚特》中的历史创造也经由自然到人到历史的正常过程,由海伦创造英雄,再由英雄创造历史。然而,这到了《浮士德》时代,从自然到人到历史的创造链便被打乱了,梅菲斯特不是通过女人作中介而是把浮士德直接领出书斋,就好像蛇把夏娃撇在一边而把亚当直接引诱出伊甸园一样。由此,创造不经过审美的过渡而直接进入历史,使历史显得暴虐和残酷。
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女人的牺牲或曰甘泪卿的悲剧便成了势在必然。不管浮士德对此如何忏悔或因此如何向往海伦,都改变不了这样的残酷性,从而洗不干净自己作为没有审美意味的创造者的罪孽。至于历史本身,也因为这种自然到人到历史的创造链的被破坏而走向没落,并且无可挽回。顺便说一句,有关西方历史的这种没落,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中是以文化生命进入文明过程这样的轨迹加以描述的。
相形之下,这样的没落在中国历史上则早已发生。人们在《山海经》故事中还可以看到些许女性崇拜的痕迹,包括在后羿的故事中,嫦娥在夫妻间的地位也不像后来的女子那么低下。然而,先秦以降,嫦娥们便如同《浮士德》中的甘泪卿一样成了历史进程的牺牲品。历史的生成越来越不具备审美意味,不仅权术肆虐,盗寇蜂起,即便道德伦常也变成了暴虐的屠夫。随着生存上的安全感的日益失落,人际术泛滥猖獗;又随着两性之间的创造意味的逐渐窒息,房中术瘟疫般风行。
◎《浮士德》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了士大夫自欺欺人的生存策略,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功立德立言之道,更是将女性的创造性质弃之如泥。除了在从事房中术和传宗接代的内室里或床笫间,整个一部历史中几乎看不到女人的身影。偶尔出现几个,也是道德审判的对象,而不具有丝毫对于男人的创造意味。世界就这样沦落了,历史就这样僵死了;也正因为这样,《红楼梦》才开宗明义地推出女娲补天的神话。
有关这种补天的历史创造意味,拟在后面章节论述贾元春—王熙凤—贾探春形象的系列时详细阐释,在此指出的只是,女娲补天过程中的炼石意象。我认为炼石是与补天相连系而不相同的神话意象。如果说补天象征着有关历史的创造的话,那么炼石则暗寓着女人之于男人的创造。由于以往历史过程中由自然到人到历史的创造链的破坏,《红楼梦》一开卷便请出女娲修补那个女人创造男人的审美环节。不管将来的命运如何,小说竭力要在历史过程中注入审美因素。这样的炼石意象具化到小说叙述的故事里,便是林黛玉的以泪洗玉。
◎女娲补天
虽然贾宝玉是一个拒绝创造的男人,而林黛玉也不以立功扬名为然,但在她的爱情期待中却于一种末世姿态中提供了一个醒世的信息:历史进程亟需注入审美因素。也即是说,在男人创造的历史上,应该具备女人炼石的前提。虽然历史的使命总是由男人担当,但导引历史的却不是帝王圣贤,而是永恒之女神,以及为这女神所显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
当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在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油画中将自由之神诉诸美丽的女子时,他根本不会想到这样的灵感早就在《红楼梦》的林黛玉形象上光芒四射了,更毋须说矗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塑像之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灵魂意味。遗憾的只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不是直接从《红楼梦》中读出这样的审美意味,而是从那座坚固的雕像追溯到那幅著名的油画,然后蓦然回首,那人却是——轻灵飘逸的林黛玉。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领略了林黛玉形象在灵魂意义上的审美意味,那么同样可以省悟的是,这个形象与其说是作者情之所至,不如说是一个小说醒世的象征。尽管小说本身不具有任何醒世意向,但林黛玉形象却的的确确是《红楼梦》留给后世的精神遗嘱。遗憾的只是,有关这一精神遗嘱,领略者寥寥。也许唯有壁立千仞的陈寅恪,在他的《柳如是别传》中续写了这样的遗嘱,推出了一颗同样自由的灵魂,并且具有同样独立的人格,站在死寂的历史路口放射着同样灿烂的审美光芒。
这就是林黛玉期待的爱情的历史文化内容。
林黛玉爱情期待的最后一个象征意味,便是等待戈多式的期待本身,作为爱情期待者的林黛玉,她的期待过程是以泪洗玉;那么她的期待指向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希望、理想或者结果、结局,而就是期待本身。这种期待就像矗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塑像一样,沉默而执着,迷茫而久远。等待戈多的意味不在于戈多的是否存在,或者会不会到来,而就在于等待本身的过程。同样,作为期待者的林黛玉的期待,也不在于所期待的爱情能否实现,而在于期待过程中的以泪洗玉。就《红楼梦》本身而言,林黛玉以这样的期待完成了小说留给后世的精神遗嘱。这个遗嘱的主要精神在于: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浊物。进入历史的男人只有经过水的洗礼,才会使历史的创造具备应有的审美意味;而历史的生命或者说活力也就取决于审美意味的有无。水枯,石则烂;石烂,历史终。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世人醒悟过来吗?
文章节选自:《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
作者李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6-09
图片:网络 责编:辣辣
■ 凤 凰 网 文 化 ■
时 代 文 化 观 察 者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