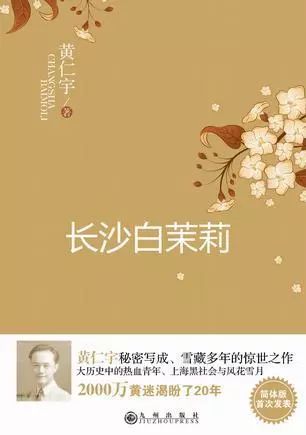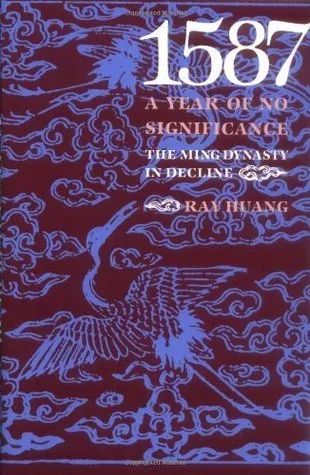黄仁宇写出了最畅销的历史书,却也留下无数争议


独家抢先看
说起最著名的历史著作,十有八九,会有人提及《万历十五年》。在黄仁宇之前,我们不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它似乎只能在象牙塔之内乏人问津;但黄仁宇之后,不仅明史走入了公共阅读的视野,整个历史学都在大众范围内引起一场又一场关注热潮。与此同时,围绕着黄仁宇史学观及治学方法的各种争议也接踵而来。
撰文| 宗城
黄仁宇把自己活成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传奇。他本来是单纯的学者,安居象牙塔,但过了六十岁,由于太久不出新书,考核不达标,他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学术之路拉响警报。可是,人生大起大落,令纽普兹分校没想到的是,第二年,黄仁宇就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万历十五年》,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从此以后,他的每一本书都成了畅销读物,有人崇拜他,还筹办了"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
他的一生有很多巧合和趣事,这种巧合甚至贯穿生死。黄仁宇于2000年1月8日离世,坊间传闻:那一天他去看电影,突发心脏病。在通往电影院的路上,黄仁宇笑着对夫人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不想一语成谶。
在民间,黄仁宇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大师,但在史学界,黄仁宇更像一位“旁门左道”,国内主流的明史专家并不太采纳他的看法,甚至有人专门分析黄仁宇的作品硬伤,批评他的治学态度。生前身后,黄仁宇誉谤一身,如今,当我们回顾这位历史学家,剥开漫骂与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争议,也许会对后人更有启发。
大历史
现代性的不合时宜
黄仁宇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为“奇侠”式的学者。有生之年,他留过学、参过军、当老师、做学问,一本《万历十五年》,让他被誉为最会讲历史的作家。
他之所以立志成为历史学家,与父亲的遭遇有关。他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但十多年的动乱让父亲厌恶革命,最终只是在时代的夹缝中苟活幸存。黄仁宇曾说:“他(父亲)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美籍华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曾辍学参军,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余英时),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著作。
做学问后,黄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写了本《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在那本书中指出:明代财政注重形式,但官僚体制和老百姓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因此无法建立有效的税收体制。这本书的观点影响了《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没有这本书,就没有《万历十五年》。
除《万历十五年》外,黄仁宇比较卖座的书还有《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在这些著作中,“大历史”是一个屡被提及的词。黄仁宇认为:惟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总的来说,“大历史”是要求学者从宏观视野去把握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去诉说特定朝代的更替演变。
身为学者,黄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计算精神。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这在《中国大历史》中尤为明显。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历史》与《万历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黄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农耕社会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这其实是西人研究中国史的典型思路,在他们看来,不同社会形态、经济体制的确有落后和先进之分,后者往往会被美名为“现代型”或“现代性”,而前者的代表就是中国的农耕社会和封建政体,《中国大历史》要讲的就是“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与农耕社会的冲突”。
《长沙白茉莉》
除历史著作外,黄仁宇还有一个写小说的爱好,他曾用笔名“李尉昂”发表小说。《汴京残梦》、《长沙白茉莉》等就是他的小说作品。如果不做学问,黄仁宇估计会成为一位勤勉的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写得不如历史书出色,说教的部分太多,语言仍具有明显的“史学腔”,在驾驭人物上也缺乏细腻,不像在写小说,倒像是一位史料讲解员。
在写法上,黄仁宇模仿了明清话本和民国通俗小说的路数,披挂着硬朗的理性外壳,骨子里却有些鸳鸯蝴蝶的温柔。他自认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可以义无反顾地追一个姑娘,也能在抗争爆发时就勇敢参军。他爱出风头,喜欢体验战士的感觉。抗战时,他身为总司令部的人员,偶尔会冒险一探无人地带,哪怕这对战事没有多少助益,而当中国军队在隘口附近折损两辆轻型坦克,他还冒险观察被日军烧毁的坦克。“用手指触摸被点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
1587
从“没有意义”到“大转折”
说黄仁宇,还是绕不过产生巨大影响的《万历十五年》。
四十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畅销不绝,分析这个现象,不是一句“写法新奇”就可以打发掉。1587年表面平静,却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这是万历登基的第十五年,是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去世的年份,黄仁宇认为——这是大明王朝的转折年。1587以后,大明朝已经走向死路。
《万历十五年》
和过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万历十五年》避开了繁冗的史料钩沉,而是以几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观点。书中,万历不满于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缛节制约;申时行每天都在进行烦闷无聊的工作;戚继光走向生命的尽头;李贽则面临一个王朝的绞杀。1587年,文官阶层纠结于鸡皮蒜毛的琐事,统治机构则小心维持着僵化的道统。黄仁宇认为: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技术。同时,这个政权在中后期过度重视道德而轻慢法制。
从申时行(编者注:明代著名大臣)的命运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公主张和谐少事、信奉儒家经典、强调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论,久而久之,他成了调解员,却无法像张居正那样改善官僚的办事能力。
可是,申时行想要平衡文官集团和皇帝的关系,和谐少事的苦心经营却并没换来同僚的理解。最终,次辅许国公开了他与万历皇帝的一封通信,申时行彻底失去了文官集团的信任,他只能辞去首辅之位。
重道德轻法制和技术,到头来因为莫须有的德行问题黯然离去,申时行恰恰是被自己维护的体系给赶出去了。在这个体系里,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程序是否合理。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风评,一方面不敢任用技术人才,一方面巴结名士,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
与申时行形成对比的是海瑞和张居正。海瑞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他有不错的办事能力和执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强、疏通河道、推行一条鞭法,以举人出身在明朝做到中央官员。海瑞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巨大激情,为了自己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奋斗,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可海瑞这个人悲剧在于:世人只把他当道德符号,而不看重他的技术能力。到他死的时候依然如此。万历十五年,海瑞去世。“北京所有的官员哀悼他,连皇帝也亲自写祭文哀悼他。”如《大明王朝1566》的作者刘和平所说:“他们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张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领,他反对用道德代替技术,主政十年,他重用技术人才,可为此经受了巨大的压力,死后惨遭抄家。
利益被切割,文官集团决定拿张居正的私德做文章。张居正试图以一己之力提高官僚集团的技术,用一套世俗的行政效率来解决大明朝的问题,却忽视道德在保守官僚心中的分量,于是被群起围攻。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是在用一己之力推动他的改革,他用的是巨大的权力,可在制度上,张居正缺少变更,这让他的改革果实难以保留。而且,张居正不但要面对保守文官道德上的苛责,还要面对皇权的反扑。所以,张居正死后,明朝政治重回老路。
明朝官场之所以会形成用道德代替技术的风气,与当时的文化有关。有政治学者曾指出: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它异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文化决定了政治生态,明朝也不例外。明朝是一个理学风气盛行的时代,表面上以儒学为本,却有两大力量交织和冲突,一个,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保守官僚,一个,是推崇陆王心学的新兴官僚。但无论何者,都对个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时期的中国,本来就有浓厚的人治氛围,历朝历代,号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于是,明朝官僚重道德轻法制也就不足为奇。
争议
理性看待黄仁宇
与畅销伴随的,是巨大的争议,史学界对黄仁宇作品及其大历史观的批评早已有之。最大的争议,是黄仁宇对“历史分析”的文学化。黄仁宇在记叙一个历史人物时,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但多形容、少依据。比如写《万历十五年》,讲到申时行、海瑞、张居正这些人物,黄仁宇费了不少笔墨写他们的“心态”、“行为”,可这种揣测依据在哪?他并没有提供,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藏匿于大历史观下的是黄仁宇“重判断,轻解释”。黄仁宇是一位造词高手,“大历史观”、“洪武型财政”、“数字化管理”是他爱讲的词,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词,却解释不足,让人云里雾里,使得主流学术界很难接受。学术界并非不允许新的观点,比如仇鹿鸣对三国历史的研究,他提出“司马懿并非儒家大族的代言人”就是对陈寅恪观点的“异议”,这个“异议”建立在详细的论证和对最新史料的把握上,所以,仇鹿鸣的观点很快被史学界接受。
除了知乎、豆瓣的网友,学术界也不乏批评黄仁宇的文章。比如万明的《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朱晓鸣和易承志的《历史的逻辑与<万历十五年>——兼论其中的某些疏漏》以及潘叔明和许苏民的《<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他们主要批评了黄仁宇引用史料的错漏。其中,潘叔明和许苏民有一个很尖锐的看法,他们认为:黄仁宇的学术偏见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
《中国大历史》
其实,黄仁宇的学术态度与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这位浪漫而张扬的湖南长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国的学术训练,又直观感受到那一时期不同社会生态中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使得黄仁宇积极拥抱现代性,强调技术与法制的作用,而对农耕社会与宗法传统持以批判态度。
对于争议,黄仁宇没有回避,他不断重申和补充自己的“大历史观”,《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和讲稿集里就有他的回应。他首先反对把历史人物从具体语境中剥离,轻率地进行道德判断,所以他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同时,他主张把局部历史纳入整个大历史的生产演变中,观察者介入历史进程的同时,把握历史中的空间互动和故事性。《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这一系列观点的实践,戚继光被从“抗倭英雄”的语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个道德符号。
当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黄仁宇的叙述魅力和他对明史传播的巨大推动作用。
吴思说:“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这种汪洋恣肆是黄仁宇讲述历史的特点,他总是站在高处,试图将历史的肌理纹路娓娓道来,读他的书,纵横捭阖的气息扑面而来,哪怕观点不同,读罢仍会享受。黄仁宇在历史叙述的贡献或许更大于他本身的历史观点,他开辟了一种别开生面的书写方式,市场的反馈证明其行之有效。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了中文版的《万历十五年》,初印的2.5万册一销而空。直到今天,这部作品仍十分流行。
《黄仁宇全集》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争议,为的不是对逝者横生指责,而是重新审视作品及所谓的“黄仁宇现象”。尽管存在错漏,但黄仁宇的作品仍为学术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启示。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学术写作也不必拘泥于陈腐形式,如果说黄仁宇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写法兼顾了少数的精英与非专业化的读者,证明枯燥的史料也能转换为引人入胜的生动叙事。
有趣的是,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肯定数目字管理,认为数字化商业社会是比农耕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恰恰由于“精密的数字化管理”。他的“业绩点”(FTE)不达标,治学思路也不符合现代性学术生产所推崇的“专业分工”。对一位学者而言,被辞退是一个巨大的挫败,这也是黄仁宇一生的难言之隐。
当更“进步”的社会形态将自己赶出门外,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进步”也要打上巨大的问号?更何况,那个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推崇的计算理性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目睹。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再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推崇“计算”、更高度分工,知识分子被哺育为专家,城市市民用工具理性打量走过的每一个人,我们甚至可以预言自己的未来,赛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这个时代,黄仁宇所担忧的问题解决了吗?黄仁宇已经离开,他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时代的难题,也是今人治学应该反思的困境。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