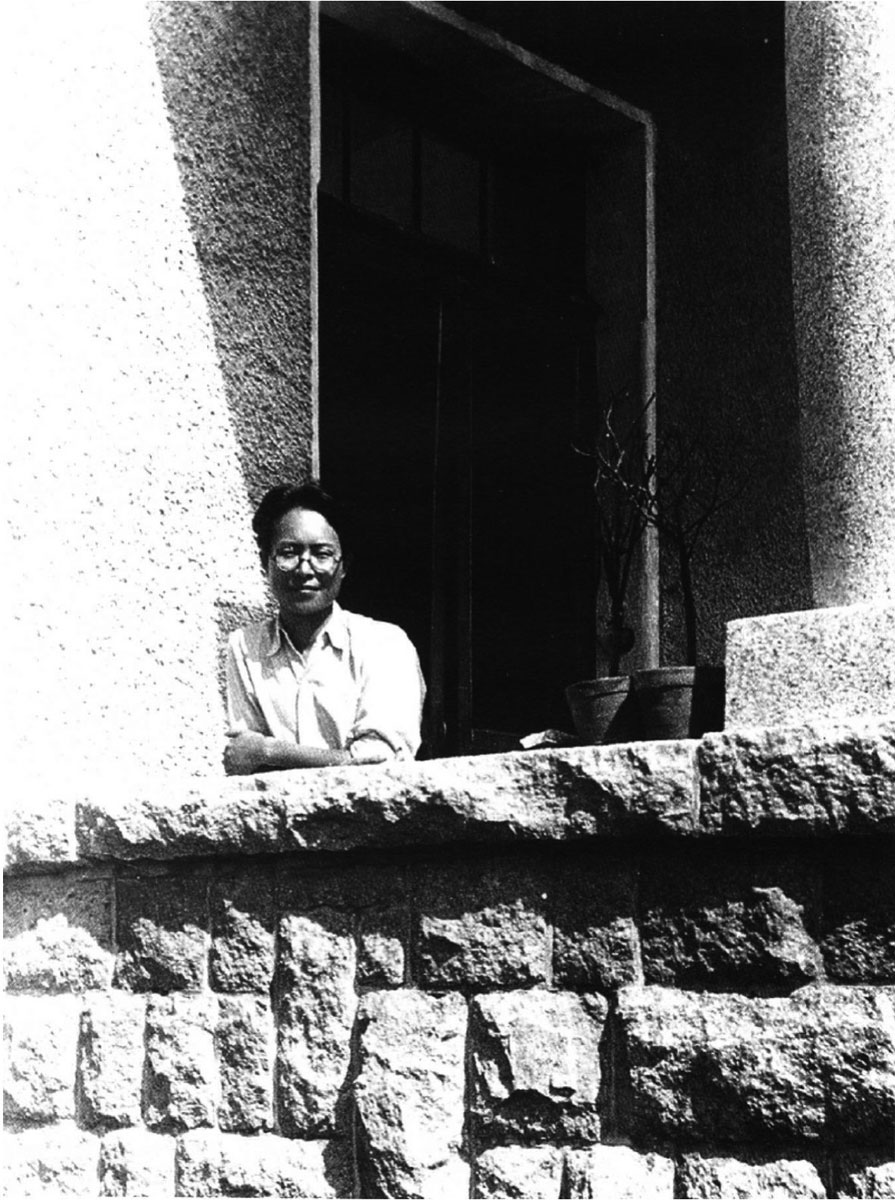青年沈从文:我得去认识生活以外的生活
36年前的今天,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沈从文的人生,大抵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生里,他写《边城》、在北大任教,后半生里,他封笔不作,转向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关于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曾有发文: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而那个写《边城》的沈从文,也早已为大众读者熟知。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中,记录了一个你或许不知道的沈从文。在开始写作以前,他曾是一个爬树、赌骰子、说粗话的“顽童”。母亲怕他走上歪路,把他送去当了兵。几年后,他自觉“在军队里混不是办法,要来读读书”。
在写作的早期,沈从文因为误会,被鲁迅“伤害”,这使他感觉屈辱;又因其才华,被徐志摩“赏识器重”。
封笔之后,沈从文后半生的道路是漫长的,而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他的路途同样漫长。阅读《边城》,固然是走近沈从文的好方式,但了解其从顽童变为著名作家的过程,才能发现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沈从文。
下文摘选自《沈从文的前半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我得去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湘西小城镇筸,诞生了一个男孩,名叫沈岳焕。等到这个男孩长大,产生出改变人生的意识和渴望,要一个人自主地去闯荡世界的时候,确定改名为沈从文。为了叙述的方便, 本文从一开始就称他沈从文。
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回乡,用柯达相机拍摄凤凰虹桥,这是他唯一存世的风景摄影。
沈从文四岁,母亲开始教他认字;五岁时,沈岳荃出生,母亲要照顾新生婴儿,就让他跟着两个姐姐,到一位女先生处念书。女先生是亲戚,他那么小,坐在书桌边的时间,怕是没有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多。六岁那年春天,正式上私塾,因为早就认识不少字,记忆力又好,比起其他孩子,过得可谓轻松。
夏天,他和幼小的弟弟同时出疹子,沈从文记得,“两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院中廊下,但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我的弟弟病后雇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照料得法,他便壮大异常。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了。”
第二年,家里给沈从文换了一个管教更严的私塾,以防已经出现过的逃学情形,不料反而更糟。他跟从几个较大的学生,特别是一个姓张的聪明表哥,“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我最先所学,同时拿来致用的,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免不了有逃学失败、谎话被识破的时候,就得罚跪,“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河中的鳜鱼被钓起,天上飞满风筝,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树木上累累的果实——神游于外,处罚的痛苦也就忘掉了;而且,“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如此顽劣,实在伤了军人父亲的心;他是第一个赞美这个儿子明慧的人,本期望这个儿子将来即便不做将军,却可能比做将军还要高些。
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既然已经开始对一本自然、社会的大书产生出强烈兴趣和冲动,他就要遏止不住地翻阅下去。《从文自传》有一章标题为《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描述一个儿童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具体情形,特别突出的是身心亲近自然的真切感受,同时还有对于日常人事和生活现象的浓厚兴趣,譬如上学路上经过的各种小铺面、小作坊,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民间手艺,诸如此类。
“大书”的比喻,与后来沈从文喜欢用的“教育”这个词相连。当这个小孩开始读这本“大书”的时候,这种“教育”也就开始了: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教育,也不同于新式学校制度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概念宽阔得多,也更根本,更有深入骨髓的影响。它是以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为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而进行的不停息的自我教育过程。“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一九三二年,沈从文在青岛。(叶公超摄)
几乎从一开始,这颗向宽广世界敞开的小小心灵,就被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带进了永远不会满足、也就永远停不下来的没有边界的探寻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阔大——
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的利用自己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希奇。最希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分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太多了。
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答解。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剸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里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02
“爬树,赌骰子,还学会了粗话野话”
一九一五年,沈从文入新式学校,先在城内的第二初级小学,半年后转入城外的第一初级小学(今文昌阁小学);一九一六年暑假后升入高小。
新式学校比私塾宽松、活泼得多,沈从文不必再逃学,但心思仍然在课本之外的空气、声音、颜色、味道,他充分动用“各样官能”来接收、消化各种东西。爬树,泅水,甚至赌骰子,给老师起绰号,还学会了粗话野话。
沈从文读高小的时候,地方上受蔡锷讨伐袁世凯战事刺激,军队改革,小小的凤凰一下子出现了四个军事学校,用新式方式训练青年。有教官饭后课余教教小孩子,顷刻间就能召集一百人左右。一个受过训练的同学问沈从文愿不愿意进预备兵的技术班,有机会补上名额当兵。“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沈从文的母亲正想不出如何管教这个日益放肆的孩子,此时有这么一个机会,既能考一分口粮,而且受严格的训练,总比在外面撒野好,就答应儿子去做兵役的候补者。
伏虎图(沈从文绘,发表于《西湖文苑》一九三三年第二期,署名季蕤)
训练期间,营上的守兵出现缺额时,就会分配名额给技术班考选,沈从文考过三次,都没有考取。后来主持的教官调走,这些预备兵也就只好解散。这次训练大约持续八个月左右,“起始在吃月饼的八月,退伍是开桃花的三月。我记得那天散操回家,我还在一个菜园里摘了一大把桃花。”
这是一九一七年,沈家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坏。为偿还沈宗嗣几笔大的债务,家里卖掉了大部分不动产;比沈从文大两岁、美丽而骄傲的二姐,死了;夏天,沈从文高小毕业。往后怎么办?
母亲看开了些,以为与其让我在家中堕入下流,不如打发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凤凰军官杨再春带兵路过山城,母亲向这个有点亲戚关系、过去的老邻居说及情况,他应允沈从文用补充兵的名义,随同部队到辰州驻防。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照习俗祭奠河鬼,谁也不敢下河。沈从文烧过纸钱,把酒倒入水中,一个人在清静的河水中拍浮了两个钟头。晚饭后母亲领他去杨家,他才知道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当兵了。“七月十六日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
这个少年离家时,没有不舍的感伤,没有愁苦一类的阴郁情绪,相反,他内心几乎是雀跃地呼应即将展开的宽广世界和幻想中的自由生活:
离开了家中的亲人,向什么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将来便有些什么希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分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中人分离的痛苦。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
03
“察觉到鲁迅对他的恶意,沈从文伤了自尊”
沈从文到北京第二天,按照通信地址,去西城某条胡同找大姐和姐夫。开门的正是大姐夫田真逸,见了他很惊讶,问:为什么到北京来?他回答说,在军队里混不是办法,要来读读书。田真逸哈哈大笑。进屋见了大姐沈岳鑫,大姐也笑。距离沈从文少年从军,大姐连夜为他准备行李,已经过去了六年。
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正在农业大学读书,星期天进城来小客店看沈从文,一问每天房钱得六毛,即刻就要他结了三天的账,带他到前门附近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在西厢房一个窄小房间里安顿下来。这个会馆是清代湘西辰沅永靖各府县修建的,专为湘西人入京赶考、官吏留京候差等落脚。会馆管事的姓金,是沈从文的远房表亲,沈从文住在这里的好处是不用花房钱。黄村生还向门房说好,一月花一块钱,每天供应热水;附近包伙食小饭店,一月六块钱,每天送一菜一汤两顿饭。
黄村生还带沈从文去宣内大街京师图书馆分馆阅览室参观过一次,从此这里就成了沈从文常来的地方,特别是冬天,有烤火设备,有热开水,他几乎每天都在大门前等待开门,所读既有新报刊,也有美术考古图录,各种杂书,不问新旧,看得懂的就看。
沈从文常去的地方还有小市的一家专卖外文旧书和翻译文学的小铺子,穷学生光顾的特别多。据说郁达夫有不少德国文学珍本旧书,是从这里收的。他用的方法十分有趣,看中某书时,故意问伙计:这书怎么不全?本来只有三本的,却要第四本。书店伙计不识德文,当然不知道有没有第四本,于是再减价出售。沈从文不懂外文,他来看翻译书,来熟了,可以随意借去,连借条也不需要。从这个小书铺,他借看了许多翻译小说。
一九三八年,沈从文在昆明,七月下旬开始创作《长河》。
不用说,这个时候的沈从文还没有明确的“文学意识”——作为现代学科划分出来的一个独立领域的“文学”,并没有在他那里占据特别的位置,他只是想读书,宽泛地读书,文学是他读书的一类,除此之外的种类,还庞杂得很。但同时也得说,文学对他的“兴味”,如同历史文物对他的“兴味”。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是迄今所能找到的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写的是小公寓里一个无业的青年向某先生寻求生活的方法,却没有邮费而最后只能把写好的信撕毁。由此开始,沈从文连续为《晨报副刊》写稿,初期作品大多刊载于此。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京报·民众文艺》周刊发表沈从文总题《狂人书简》散文中的前三篇;他意外的是,有一天,两个编辑——项拙和胡也频——来到他公寓的小房间,三个人——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和一个退伍的陆军上士,沈从文这样称呼刚认识的朋友和自己——“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第二天又见面,又是“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胡也频带着一个圆脸长眉的女子来看沈从文,她就是丁玲。沈从文也曾和胡也频一起去丁玲住的通丰公寓,见到她的小房间潮湿破烂,和自己住的“窄而霉小斋”也差不多。
顺理成章,《狂人书简》接下来的六篇,以及其他几篇文章,也在《京报·民众文艺》相继发表了。
与胡也频、丁玲相识未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本与沈从文无关,他却被牵扯到事件的“中心”:
丁玲于苦闷茫然中,给鲁迅写信,渴望得到指引;鲁迅日记四月三十日有“得丁玲信”的记录。鲁迅当然不知道丁玲是谁,有人——一说是孙伏园,一说是荆有麟——告诉他,笔迹很像沈从文。鲁迅极为生气,沈从文竟然化用一个女人的名字给他写信。丁玲得不到鲁迅的回信,两个星期后回湖南了。
但此事并没有结束,“后来,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过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胡也频所以会用这么奇怪的名片,是因为他听说丁玲死了一个弟弟,他愿意做她的弟弟;其实他二十二岁,比丁玲大一岁。热恋中的文学青年,做什么都不奇怪,他只是没考虑鲁迅会怎么想。
我的画成为怪东西了,因此只得搁笔,不再涂抹,不过来一个水鸟浮江图看看。(此信或当在十二月初到)(沈从文绘,见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五日复王际真信)
鲁迅内心反应的过程,在后来给钱玄同的两封信里有清晰的呈现:《京报·国语周刊》七月十二日第五期发表了沈从文的民歌体诗作《乡间的夏(镇筸土话)》,鲁迅当天给周刊编辑钱玄同写信,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
七月二十日又一信,说得更详细——因《乡间的夏》一诗中有“孥孥唉”字样,鲁迅就用“孥孥阿文”指代沈从文;沈从文《狂人书简》系列中有两篇,那个写信人落款即为“孥孥阿文”,或者鲁迅看过,并留意到文章里面的这个署名?——“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也耳矣。”
后来,鲁迅得知确有丁玲其人,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但是,对于误会沈从文,未见有什么表示。
沈从文不久就得知了此事和鲁迅对他的恶感。这场莫名其妙的误会,当然有伤一个无辜而倔强的年轻人的自尊;尤其考虑到两个人的“身份”差别巨大,一个是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一个是已经公认为新文学最有成就的作家,沈从文的屈辱感恐怕很难消除。两个从未见过面、从未交往过的人,由此产生心理隔阂,以后就再难交往。虽然从理智上,此后他们彼此对对方的作品都做出过很高的评价,感情上却没法走近了。
04
“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的过程到纸上。”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晨报副刊》五四纪念号有一篇《大学与学生》的文章,作者唯刚,即北大教授林宰平,谈到“好些有用的青年,多数只是困在饮食男女上”,并以“学生”的作品,见个中情形。他引用了沈从文的文章。沈从文以《遥夜》为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篇散文,林宰平从三月九日发表的第五篇中,抄出几个段落——这里也重抄一遍,从中可以感受沈从文初期一类文字的风格:
日来的风也太猖狂了,我为了扫除我星期日的寂寞,不得不跑到东城一友人校中去消蚀这一段生命。诅咒着风的无聊,也许人人都一样。但是,当我同你在车上并排的坐着时,我却对这风私下致过许多谢忱了。风若知同情于不幸的人们,稍稍的——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那能有这样幸福?你那女王般骄傲,使我内心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眶外时,我以为同坐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那冷酷的视线投到我身上,露出卑鄙的神气。
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我那能再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你大概也见到东单时颓然下车的我,但这对你值不得在印象中久占,至多在当时感到一种座位宽松后的舒适罢了!你又那能知道车座上的一忽儿,一个同座不能给人以愉快的平常而且褴褛的少年,心中会有许多不相干的眼泪待流?
林宰平写道:“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
沈从文作《致唯刚先生》,发表于五月十二日《晨报副刊》,他说自己写文章不过是“想从最低的行市换两顿饭吃”,“于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着的人”哪里能冒充大学生,“人家大学生有作有为时时在以改良社会为任务的多着呢。并且开会,谈政治,讨论妇女解放,谁个不认真努力?”“万不想到先生会注了意,指出来为一个学生代表作品的例子,而加上这些够使我自省伤心的话!”他负气似的结束道:“‘替社会成就什么事业?’这些是有用人做的。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
等一会儿我就得点蜡烛吃晚饭了。曾家河下游一点点。(沈从文绘,蜡笔画,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致张兆和信)
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他来见面,得以了解这个年轻人的处境,给他很多鼓励和实际帮助。沈从文自此对林宰平终生以师相称。
五月份,北大的丁西林介绍沈从文到创办不久的《现代评论》做收发员,收入当然微薄,但由此与主编陈源、文艺编辑杨振声等相熟,以后在《现代评论》发表了不少作品;六月下旬,沈从文短暂离开北京去东北锦州,大哥沈云麓在那里以卖炭画教炭画为生,他去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七月即无果而返;七、八月间,林宰平介绍他在京兆尹薛笃弼的秘书室任书记,这份差事因薛即将离任而很快终止。
林宰平托梁启超致书熊希龄,为沈从文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八月,沈从文到了北京西北郊的香山。
沈从文晚年回忆此一时期得到的关心和支持,说了这样一段话:“用笔刚好得到出路时,于北京认识了许多对我此后一生工作和生活影响极大而持久的师友。这些师友中年纪最大,影响最深,关系最久,应数林宰平先生;年纪最轻,帮助最多,理解特深,应数徐志摩先生。”
沈从文九月与徐志摩第一次见面,之前有过通信。他到徐志摩的住处,松树胡同一所小小洋房,拜访的情景,多少年之后还历历在目:
我这么一个打烂仗出身的人,照例见生人总充满一种羞涩心情,不大说话。记得一见他,只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他就明白,我是个不讲什么礼貌的乡下人,容易从不拘常套来解脱一切拘束,其时还刚起床不久,穿了件条子花纹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铺一面谈天,他的随便处,过不多久就把我在陌生人前的羞涩解除了。只问问我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且就从枕边取出他晚上写的两首诗,有腔有调天真烂漫自得其乐的念起来。
因为早知道我在《现代评论》作个小工,专管收发报刊杂事,且和叔华夫妇相熟,经常在陈家作客,且可肯定叔华夫妇一定早已在他面前说了我不少好话。……不到一点钟,就把一小卷似乎用日本纸写的长信递给我来欣赏,且一面说这信是封刚从美国寄来的,你读读看,内中写得多真诚坦率又多有情!原来是他的好友林徽因女士来的一个长信。他就为我补充这个朋友的明朗热情种种稀有的性格,并告我和写信人的友谊种种。那时他还未曾和陆小曼结婚。对人无机心到使人吃惊程度……
徐志摩从十月一日起接编《晨报副刊》,当日刊出《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章大张旗鼓地罗列约请撰稿的各方朋友。在这一份名单中,文学青年沈从文得以跻身学者、教授、诗人之间,显见徐志摩对他非同一般的赏识和器重,日后大量发表他的各类作品,也就很自然了。名单中不少人,后来和沈从文有亲近的交往。
接下来一件事,更见出徐志摩的性格和他对沈从文的护爱。他从前任刘勉己留下来的稿子中,找到一个沈从文四五篇作品的册子,就把其中的一篇《市集》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了,并写《志摩的欣赏》,附在文后一并刊出: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这篇两千多字的短散文,放在沈从文全部的作品中来看,并不特别出色;但是它出现在一个作者写作的初期,“因为眷恋故乡的梦”而写湘西生活情景,为“保全乡土趣味原故”而处理文字,其主题和方法以后会得到不断发挥、充实、丰富,并从中产生沈从文最优秀的作品,成就他独有的文学事业。
沈从文见到文章刊出,却极为不安。因为这篇稿子之前已经在《燕大周刊》发表过,胡也频看见后又转载到《京报·民众文艺》上。他赶紧写出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解释“小东西出现到三次”的原因,并说:“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填到篇末,还加了几句受来背膊发麻的按语……”《晨报副刊》登出这篇声明,有意思的是,徐志摩又加了一份答辞: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徐志摩的率性跃然纸上,对沈从文的照拂之心也袒露无疑。
就算从当时来看,沈从文确乎也值得徐志摩以及其他人热心相助:他那么勤勉,努力,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就发表了六十多篇作品。若干年后沈从文被讽刺为“多产作家”,其实他从一开始写作就是多产的。与其关注作为结果的多产,不如体察他何以几乎用全部的力量来做这件事。
这里面有以稿酬缓解生活压力的因素,这是一个现实的解释;大量写作更内在的原因,是强烈的尝试冲动和把这种冲动快速付诸笔端的实践:这些包括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初露才华,但无疑都是急切的尝试之作——他并不明确地知道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所以他要不停地摸索、练习、实验,要多个方向试一试,试一试各种体裁,各种写法,要大量地、持续不断地尝试。
本文节选自
《沈从文的前半生》
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理想国
副标题:1902-1948
出版年: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