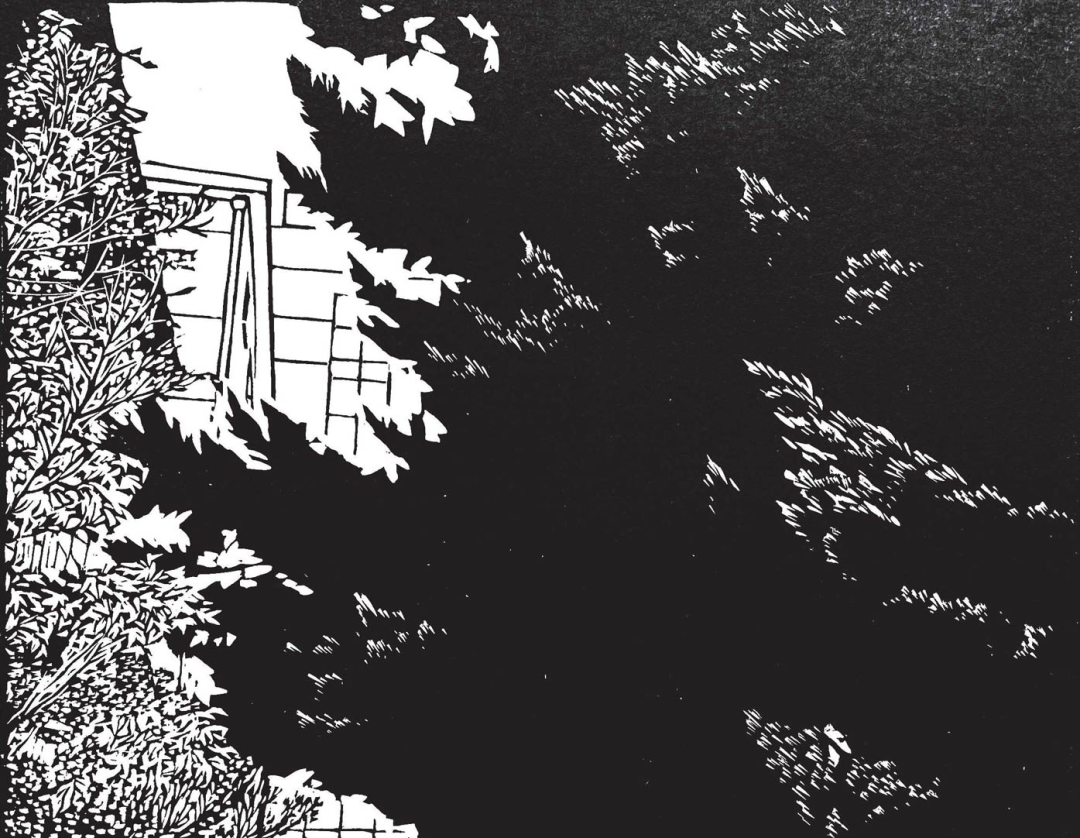听到鸟儿叫,我就知道春天来了
北京,冻结了一个冬天的河水开始变得柔软,远远看去,流动着绿色的光,河边的枯树枝的尖处,冒出褐色的花苞,像发痒的青春痘,再过几天,大概就会爆开。北京如此,别处的春天恐怕也已经来了,只是还未全面盛开,尚潜伏在一些细微的地方。比如鸟鸣声里。
作家申赋渔的散文集《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恐怕正适合早春来读。鸟对春天的感受比人要来得敏锐,若是你已能听见窗外的鸟鸣,那么走出门去吧,找到你的城市里春天的踪影,欢迎在留言区给我们分享。
下文摘选自《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
我一直在想,鸟儿有没有理想?
在我厨房的天花板上,住着一窝山雀。工人在给厨房吊顶的时候,多打了一个出风口。从墙外能清楚地看到这个洞。我不反对鸟儿在我的屋檐下、窗口或者任何一个角落里搭窝。我甚至很喜欢。这是它们对我的友善与亲近。我希望它们利用这个洞。我以为工人在吊顶时,会从里面把这个洞堵上的,然而他没有。所以鸟儿并不是把窝建在这个洞里,而是从这个洞,深入到了我的房间。窝就搭在我的天花板上。这么一来,我的天花板就成了一块葱郁的草地,一个隐蔽的灌木丛,甚至是一小片幽暗的树林。
图源自书中
我长时间地坐在厨房的餐桌边上,倾听着头顶上小鸟们的动静。我吃饭原本就很简单,极少煎炸炒烹,油烟机也很少打开,现在我更是尽力不发出什么动静。我泡一杯茶,拿一本书,一大早起来,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坐着。
在我醒来之前,小鸟早已醒了。鸟妈妈不断地从窗口掠过,给小鸟送小果子和小虫。只要鸟妈妈一过来,头顶立即变得嘈杂喧闹。这一窝至少有四只小山雀,鸟妈妈一定忙坏了,整天都在觅食。偶尔,它会在外面的栾树上歇一歇。它没有鸣唱,只是咯咯地咂着嘴,仿佛在思索或者叹息某个棘手的难题。生活就是这样,每家都有自己的困扰。
巢中的小雏鸟是自在快活的。它们断断续续地发出细嫩的咿呀的鸣叫。鸟类学家们称之为“次鸣”。这是雏鸟在学着鸣唱。它在唱给自己听,一边听,一边完善自己的曲调。对于雏鸟而言,这是它一生中极为关键的时刻。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它大概永远也学不会好听、精准、有意义的鸣唱了,它会变成哑巴,它甚至无法生存。虽然许多鸟儿的鸣啭是天生的,可是天生的曲调也要练习。在本能的鸣叫之外,歌唱的本领也有高下。这个高下,将决定着它们的未来。
山雀要学会一种别人听不到的高频呼叫。那是一种奇怪的“嘶”“嘶”声。当大型的捕食者或者某种巨大的危险迫近时,山雀就要发出警报,让同伴们赶快躲避。我相信,当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厨房里喝茶时,雏鸟们已经开始这种性命攸关的尝试了。它们天生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与山雀相比,人类在这一点上就显得有些茫然无措。我们常常对悄然而至的危险一无所知。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恰恰来自于我们的同类。我们很难发出类似于“嘶”“嘶”这样的警报。人与人之间没有这样诚实的约定。我们发不出。我们不被允许发出。我们发出了,也很少有人在意或者明白。我们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悲剧在我们身旁上演。或者在旁人的注视下,我们一步步走向深渊。我们不像鸟儿那样爱自己的同类。
山雀另外要学的一个本领,也让我深受启发。我们或多或少地,都会处在某个噪音之中。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网络之中,噪音无处不在。每当此时,我们除了加大嗓门,制造更多的噪音,试图压制之外,别无他法。如此一来,噪音层层叠加,最终谁也听不清谁。人人都变得愤怒而戾气十足。这样的环境最终会变得令人厌恶,甚至充满着恐惧。
而山雀不是这样思考的。每当噪声增大之后,山雀们从来不增大自己的声音,而是改变自己鸣啭的频率,用一种更加清晰而理性的声音对话。它们鸣唱的对象只是同类,对于其他鸟类或者动物,声音的大小毫无意义,甚至只会给自己带来威胁。
电影《小森林 冬春篇》
虽然鸟儿对噪声也是极为厌恶,事实上,噪声对于人类的危害要比对鸟儿大得多。鸟儿们耳蜗的毛细胞会定期更换,如果受到了损害,它们总能自我修复。可是人类则不能。我们耳蜗的毛细胞受伤了,只能坏掉,再也不能重生。而我们对此却很少在意。我们已经习惯于喧闹,并在这喧闹声中不断地提高着我们的嗓门。人的年纪渐长,受到的损害不断地堆积,听力越来越减弱。而我,大概很快就听不到小巧灵动的戴菊鸟高频的鸣唱了。
我们总试图让别人更多地听见自己的声音,同时却又关闭着自己的听觉。然而每一只鸟儿都知道,发出声音是为了对话。
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一只山雀总能接收到另一只山雀的频道。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哪怕它的声音再细微,它表达的意思再曲折,它想诉说的情感再绵长。
芒种刚过,正是山雀的鸣唱最为婉转动听的时节。这是它们恋爱的季节。所有恋爱中的雄鸟,大脑都处于一种特别的兴奋之中。它们的歌声变得更缠绵、更明亮,变得千回百转。它全身的力气都用在歌唱上。它的大脑被歌唱的冲动完全占据了。每天早上,我都被这些让人痴迷又心碎的歌声叫醒。这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刻。
天还没有大亮,我在睡梦与醒来的边缘。然后就听到乌鸫的鸣叫。它的歌声既有着青春的甜蜜和冲动,又带着一种令人忧伤的深沉。乌鸫在哪里呢?听不出来。它在地上跳跃着,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它不停歇地歌唱,追逐着另一只矜持又高傲的乌鸫。
这时候不要起床,还早。眼睛也不要睁开,要用耳朵去听。乌鸫的歌声只是起了一个头,歌手们正陆续赶来。
“叽咯”“叽咯”,这是大山雀。大山雀就在屋后这棵高大的栾树上。它一直重复着同一个单调的旋律,等你有些厌倦了,它调子一变,突然就吐出一串柔美抒情的音符,像是飞快地说了一句情话,又立即装作若无其事。然而另一只山雀对此心知肚明。整个春天里,它们一直不知疲倦地玩着这个情感游戏。然后在夏天,一窝叽叽喳喳的小鸟儿就诞生在我的天花板上。
尾随着大山雀歌声的是相思鸟。它才是真正的歌唱家。什么样的调子对它来说都是轻松自如。每个音节之间都几乎没有过渡,直接滑过去,又是无懈可击地动听。甚至来不及听,一连串的音符已经像泉水一样流到心里。相思鸟不是唱给我听的,然而我还是被它的多情深深打动。所有美丽的声音背后,一定饱含着最真的爱恋。
相思鸟的情歌很快被一只金丝雀打断。它突然吐出长长一串颤音。它的歌词绵长得无边无际,它不用换气,就那样不停歇地表达着内心的欢喜。这种喜悦是不管不顾的,是淋漓尽致的,又是曲折灵动的。在这扣人心弦的颤声之中,它突然又唱出几个高音。就像春花次第开放的原野上,突然长出几棵挺拔的小树,树上满满的都是花朵。
金丝雀的雌鸟很少歌唱,即便唱出来,也是单调无味。可是它喜欢雄鸟的长歌。雄鸟的歌声越是繁复,雌鸟筑巢的速度越快。在最兴奋的时候,它们之间相互沟通的,将是人类听不到的一种声音。它们喜欢用高频的颤音对话,这是不被打扰的情话,也是幸福的顶点。爱不是简单的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动力。它推动并改变着彼此的命运。
可是这动力,不是无限的。鸟儿的大脑承受不了这种可怕的、疯狂的燃烧。大脑对于能量的消耗是惊人的。人类的大脑在启动之后,它动用的将是人体百分之二十的能量。鸟儿和人一样会消耗巨大的能量,它们大脑的容量要小得多,所以更加不能承受这样的激情。
鸟儿比人类更有谋略。它们会关闭自己的大脑。恋爱季节一过,它控制鸣唱的中枢神经开始萎缩,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再重新生长。如果不这样,它们对情感的激烈投放,会毁灭自己。人类永远做不到这样的收放自如。所以人类不会像鸟儿那样浓烈,也不会像鸟儿那样宁静。人类总是备受情感的煎熬,在一种胶着的痛苦中寻找稍纵即逝的安慰。
山雀的一种 图源自网络
人类对鸟儿之间的浓烈之爱与美好表达是羡慕的。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曾经用音符记录椋鸟的鸣啭。田园诗人约翰·克莱尔也曾用词句临摹夜莺的歌唱。人类的音乐与诗歌根本不能表达鸟儿鸣唱的精妙。我觉得并不是人类的手段不够高明,而是我们对鸟儿的情感一无所知。
鸟儿其实是在用它们的生命在歌唱。它们在歌声中寻找恋人,在歌声中努力生存。鸟类学家克雷布斯爵士和他的同仁们用一系列繁复的实验证明:一只鸣啭动听的山雀会占有更大的领地,会拥有更多的配偶,会活得更加长久。
在我的头顶上,小小的山雀一直在鸣叫,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在学会飞翔之前,它先要学会鸣唱。在这鸣唱里,寄托着它们对未来的理想。这是个什么样的理想呢?我并不同意鸟类学家们的意见。我认为小鸟儿只是希望在长大之后,能有另一只鸟儿和它好好说话,彼此什么都懂。
02
“我大概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一只白鹭”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走到阳台上,跟河对岸那只白鹭打一声招呼。
白鹭要么停在河边那棵青杨树上,要么停在对岸那幢空无一人的房屋的阳台上。它从来不看我。
冬天的时候,河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棵乌桕树。所有树的叶子都落尽了,只有乌桕树上挂满了白色的小果子,像是开了一树的梅花。这些果子是鸟儿们过冬的食粮。每天都有成群的鸟儿在树上一边啄食,一边叽叽喳喳地闲聊。在冷寂的冬天里,只有这棵树是最热闹的。独来独往的白鹭,每天也有许多时间在这棵树底下徘徊。它一边察看着河面上的小虫、小鱼、小虾,偶尔侧过头,打量一下树上的热闹。这棵乌桕树是鸟儿们的客厅。这个冬天很冷,下过两场大雪,白鹭一直置身于众鸟之外。
春天来了,乌桕树上的小果子被鸟儿们啄食得干干净净,整棵树只剩下光秃的枝条。叶芽迟迟不长。作为一个客厅,太冷清、太单调了。
图源自书中
鸟儿们把客厅转移到了那棵巨大古老的枫杨树上。枫杨的新叶一下子长满了所有的枝条,整棵树散发出一种热情、好客的气息。喜鹊、乌鸫、斑鸠、大山雀、小山雀等等,都聚到了这里。一群一群地飞来,又一群一群地飞走,忙碌不停。毕竟是春天了,不能像冬天那样懒散。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白鹭选择了河对岸那棵青杨做自己的落脚点。
不论是晴天雨天,它都站在那里,像一个总在冥想却始终不得开悟的修行者。它看也不看这棵枫杨树上的热闹。它一直站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偶尔飞出去,在天空中盘旋几圈,或者在河滩浅水里散一会儿步,它又回到青杨树上,并且总站在同一根树枝上。这时候,青杨的叶芽儿刚刚冒出一点,整棵树才有那么一点点的绿意,刚刚苏醒,还睡眼蒙眬。那棵枫杨呢?已经成为整个河岸上最繁华喧嚣的闹市。这都与白鹭无关。春天的白鹭仍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知道在坚持什么。它和所有的鸟儿都格格不入,它显得孤独又骄傲。
谷雨之后是立夏,立夏之后是小满。枇杷树结了一树的果子,石榴开了一树的小红花。枫杨的叶子从嫩绿变得深绿,现在已经是苍翠的了。茂密的树叶和长串的花朵把树枝压得弯弯的,树冠已经不堪重负。小鸟儿们也没办法在上面停驻了,叶子太多太密,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夏日来临。鸟儿们可去的地方太多了,河岸上已经不存在一个大家常聚的中心。许多鸟儿进入育雏时节,成双成对地飞来飞去,大家已经没有兴趣聚在一起消磨时光。白鹭还是独来独往,只是看上去有些落寞和憔悴。
雨季改变了一切。所有树的叶子都变得茂密,都从简笔勾勒的线条,变成了大片的色块。放眼望去,已经辨不出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界限。小河两岸的树木,构成了整片的树林。一只鸟儿,甚至不用展开翅膀去飞,只要轻轻跃动,就能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在这面目模糊的大色块之中,唯一清晰的是白鹭栖息的那棵杨树。
杨树的树干长到十多米高的时候,伸出两根枝丫。枝丫像两条健壮修长的胳膊,一直往上,拥抱着一片淡蓝色的天空。从这两条胳膊上长出来的枝条也是疏朗的,也是朝着天空伸展出去。虽然经过一个春天的生长,叶子也变得宽阔肥大,可是丝毫没有破坏整棵树的结构。杨树在一大片的树木之中,显得俊朗挺拔,卓尔不群。因为它的挺拔和疏朗,我能清晰地看到每一片叶子被风吹动时跳舞的样子。
天黑了,杨树高耸在淡淡的月光底下,我看不到叶子在动,可是我仍然能听到风吹动它的声音。它的声音节奏分明,清澈悦耳。这棵树是白鹭真正的好伙伴。在我看来,白鹭与青杨是一个整体,两者惺惺相惜,密不可分。
季节的变换,导致了小河两岸景物的变幻,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悲欢离合。我日日生活在这里,默不作声地观看着这一切。植物生长的轮回,昆虫的爱恨情仇,动物之间的生死之战,村民们的来来去去,轮番在这个荒凉的小村中上演。我没有和任何人产生亲密的联系,他们都是陌生人。他们会引起我内心波澜的起伏,可是并不与我息息相关。只有这只白鹭,它每日和我相伴,我们已经不可分离。
我每天早上都向它问候。它每天都来。它每天都来,就是回应我的问候。在向它问候之后,看到它停栖在河的对岸,我的心就很踏实,很满足。只有在问候了白鹭之后,我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当我工作累了,或者突然想起它的时候,我就到门外去看它。它有时在,有时不在。不在的时间长了,我会心怀焦虑。不过最迟在傍晚,它就会出现。
往往是这样,我坐在书房里,忽然感觉到窗外有一个白影掠过,我就立即走到外面的阳台上。这时候,白鹭已经飞到很远的地方,成了一个小白点。我盯着这个似乎就要消失的小白点,盯着。然后,它就又飞了回来。它的翅膀伸展开来,在天空中滑行,仿佛向我展示它最为自豪的一面。这样飞上几个来回,它就消失了。我很想知道它去了哪里?它的窝筑成什么样?它有没有自己的伙伴?好几次,我想象我也变成了一只鸟,一只白鹭,可以和它一起飞。我飞不起来,我大概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一只白鹭。
白鹭的一种 图源自网络
在做梦的时候,我曾经也是能飞的,飞得与这只白鹭一样好。那时我还没有搬到这里。我梦到了我可以贴着河面飞行,可以越过山岭,我可以站在树梢上,在风中摇曳。只要脚尖轻轻一踮,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飞翔。可是这样的梦,已经很久没做了。有一次,我几乎已经做到这个梦了。我从一个堤坝上往下跳,我希望我能飞起来。我伸开手臂,像鸟儿展开翅膀,一直到碰触到水面了,我也没能飞起来,我一头栽到了水里。我已经不会飞了。我每天都做梦,大多平淡无奇,醒来就忘了。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再也没飞过,我的脚步永远沉重地走在大地上。有人说,梦到自己会飞,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未知的未来。渴望飞起来,也许是我喜欢这只白鹭的缘由。它的确飞得好。我如果能变成一只鸟儿,就应该是它飞翔的样子。
白鹭有时也停在河对岸那幢房屋的阳台上。停在青杨树上的白鹭,显得志存高远。停在阳台上的白鹭,显得孤独彷徨。
我搬来这里之后,就没看到这幢房屋亮起过灯光。我特意去看过几次。屋门口的台阶已经塌陷了,砖石的缝隙里长出蓬勃的野草。一棵巨大的合欢树,完全遮盖了那家的门窗。从这些植物的形态上来看,这里至少已经荒废了十年。这幢房子与我隔河相望,有一面大窗户对着我的阳台。窗口竖放着一张巨幅的照片,有窗户的三分之二大。这是一对年轻人的结婚照。两人相互依偎着,深情地望着窗外的景象。另一面窗户上,至今仍然贴着一张红色的“囍”。这幢荒废了十多年的房屋,曾经是他们结婚的新房。
他们为什么一去不返?为什么要把珍贵的结婚照留在这里?为什么照片的正面要对着窗外?起先的时候,照片一定不是这样摆放的。因为不可能在新房里,把结婚照的背面对着自己。
站在阳台上,我眺望着这个寂静的小村。每一幢楼里,都曾经有过一段人生,所有的人生都独一无二。在我们欢笑时,有人正在流泪。在我们欢聚时,有人正在离别。谁也走不进谁的梦,谁也长不出能飞的翅膀。白鹭从青杨树上飞起来,兜了一个大圈,轻轻地落在这幢废弃已久的房屋的阳台上。白鹭让这幢房屋多了一分生机,同时又添了一分说不出的忧伤。
小村的晚上黑得很,十点多,四周安安静静,小河里偶尔有几声蛙鸣,窗外没有一丝亮光。我正在看一本闲书,突然听到一声沙哑恐惧的鸣叫。随后又是一声。是白鹭。我冲出家门。声音是从河边的一丛迎春花底下发出的。
我一直以为,白鹭晚上会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每天晚上它离开的时候,都会飞到极高处,然后消失在天边的地平线上。我从来没想到它就住在我的屋前。迎春花长在院门的右前方,在枫杨树的底下,离河水很近。除了迎春花刚开的那段时间,谁也不会在意这里。
我打开手电筒,迎春花底下什么也没有。可是我的确听到了白鹭可怕的鸣叫。送货的老朱也跑过来:“是野猫。野猫捉到白鹭了。”
他也听到了。
我们在河滩上搜寻着。没有野猫,没有白鹭,没有血迹,也没有飘落的羽毛。
下雨了。老朱说:“回去吧。这么长时间没找到,白鹭应该没死,逃掉了。”
雨下了一夜。我一直在听雨里的各种声音。没有白鹭的动静,也没有猫的动静。天亮了,我站在阳台上朝河对面看过去。湿漉漉的青杨树上是空的,对面房屋的阳台上也是空的。雨还在下,我沿着小河走来走去,什么也没有。雨里穿梭忙碌着各种各样的鸟儿,它们有的在吟唱,有的在召唤,有的在絮絮叨叨地拉着家常,所有这些声音里,没有一个是沙哑的。
我搬来这里已经八个月了,每天都看到这只白鹭,每天早晨都向它问候。我偶尔也曾想过,总有一天,它会消失,它会不辞而别。我可以想象它是换了一种生活。我从来没想到,它会在我的面前,被猎杀。
我在阳台上坐了一上午。雨慢慢停了,白鹭一直没来。我回到书桌前,可是没办法工作,我总在想这只白鹭。我太累了,头昏昏沉沉,我想睡一觉,我靠在沙发上。书房的窗外,突然掠过,一个小小的白影。
本文节选自
《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
作者:申赋渔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出版年: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