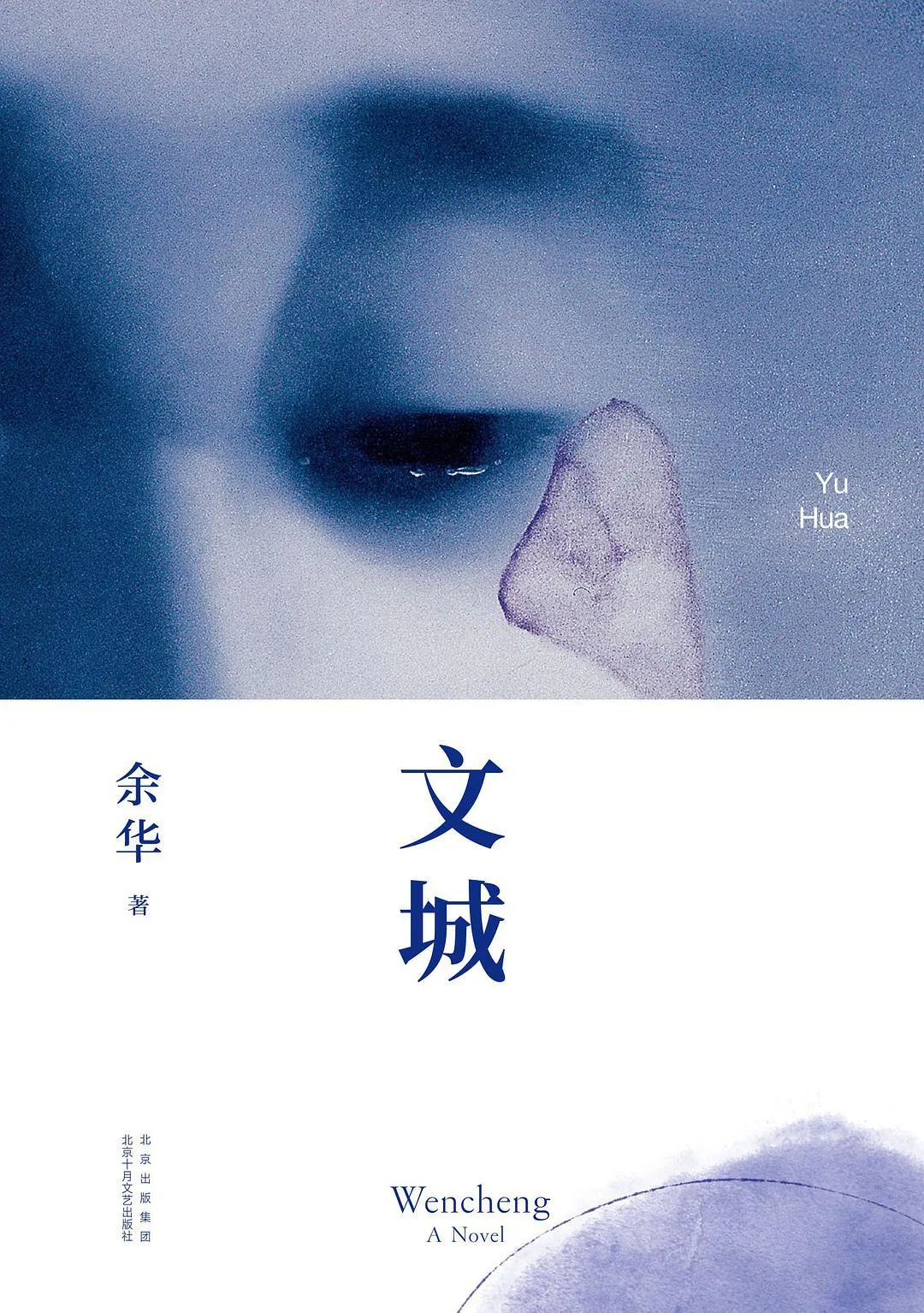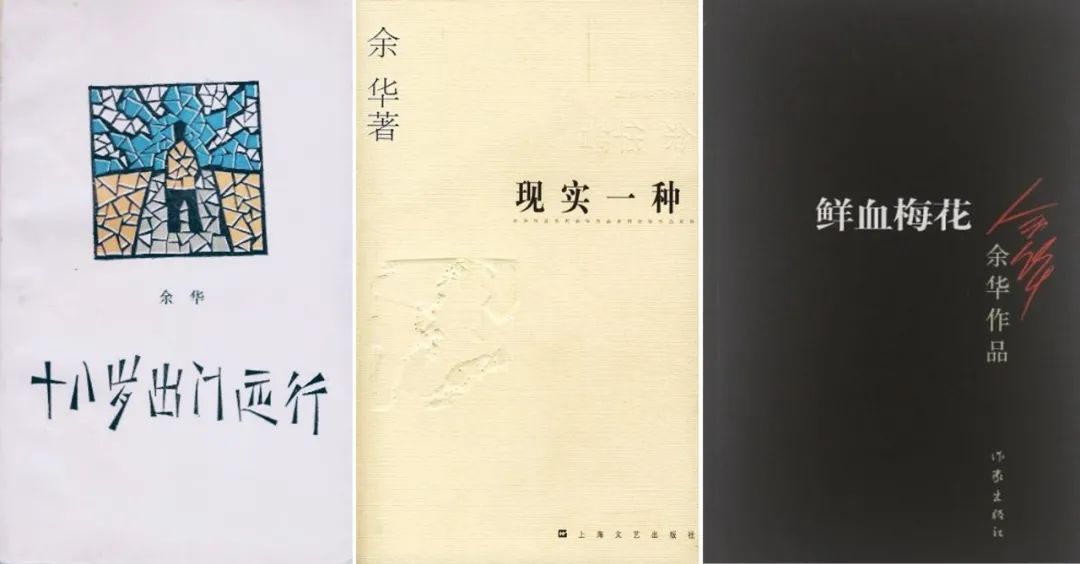余华时隔八年写出的《文城》是“纯文学爽文”吗?
“尽管我对作为小说的《文城》评价有很大保留,但我依然要承认,《文城》背后的余华有些打动我——与此相比,《第七天》背后的那个余华就会让我感到不适,他功成名就,却偏要来不可靠地代言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愤怒和残酷。”
好故事不等于好小说:评余华《文城》
文 | 李壮
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在我个人看来,余华的新长篇《文城》,是个好故事,不是个好小说。
接下来,让我来具体解释一下这句很短却又很绕的话。
01
“小说”和“故事”
这句话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在今天,“故事”和“小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离,至少它们不再像过往那样严丝合缝、二者同一。类似的情况在文学领域早已出现过,例如“诗”和“歌”的分离。《诗经》和宋词都是用来唱的,但汉语新诗在多数时候就不必考虑唱的问题,因为这一功能项已经由专门的歌词承担了。二者的合法性各自独立,标准也是不同的。有些歌词或许很有诗的意味,然而直接以诗歌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依然不妥。反过来说,许多优秀的新诗作品唱起来会很别扭甚至很难听,我们也不能因为它不能唱而认为它不是好诗。
“故事”和“小说”也是这样。在中国的文学语境中,“小说”有其特指,在多数时候,它指的就是建立在现代性和五四传统之上的“纯文学小说”。由于这一特定的来源传统,小说同启蒙的任务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并逐渐产生了一套针对小说的价值想象和技艺准则。“小说”可以讲故事,也可以不讲故事。反过来,故事能够以“纯文学小说”的方式呈现,但也同样拥有其他形态:比如网络小说、非虚构文学、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段子。
这些“其他形态”,也正是我在本文中对“故事”的特指:它们是广义“故事”中溢出了传统小说边界的那部分,多属于消费主义时代兴起的新的叙事形式,其“物种起源”与传统小说大不一样,其需求、预期效果和叙事目标,自然也不相同。
今天,“小说”与“故事”是一张纸上的两个圆,它们有巨大的重叠面积,但彼此又都有溢出。必然,二者都发展出了自己的要求和标准,这二者同样既重叠又溢出。
时隔八年,余华推出全新长篇小说《文城》
于是回到余华的《文城》。以纯文学小说的标准来看,《文城》的人物形象扁平、情节设计单薄、逻辑动力不足……一字以蔽之,就是“假”。当然,考虑到《文城》的语言总体还算漂亮、“文城 补”部分的结构设计确有心思、许多细节处理也显示出了余华应有的水平,我认为《文城》并不是一部“差小说”、最多算一部“不够好的小说”。如果有人认为这本书差到不能看,我想多半是因为它出自“纯文学顶流”余华之手、因而读者在潜意识里提高了评判标准——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就像我们不能因为这本书是余华写的就只能夸不能骂一样。
有趣的是,如果我以更广义的“故事”标准来衡量,我会发现余华给我讲了一个好故事。因为,当我以(有特指的)“故事”概念区别于纯文学小说的时候,我的关注重心已经开始向功能性或使用价值转移——转移到了阅读的流畅感、享受感、满足感,也就是读者的主观阅读体验。
我发现,读完《文城》,我的感觉是爽的。它的叙述流畅清晰,情节也能吸引人一直往下读。甚至除了“爽”,我的心中还生出了一阵感动。一些同我交流过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爽”或“感动”或二者兼有的感觉。我想或许,余华确实写了一个好故事:从最直观的效果上讲,它大概让很多读者满足了、舒服了。扁平?单薄?“假”?这些并不重要,对于“故事”来说,读者的反应是真的,它自己也就“真”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倒让《文城》显得有意思起来了。
02
“童话镇”
那么,先来说说“假”的部分。
阅读《文城》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时常萦绕着歌曲《童话镇》的旋律:
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
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
却又在爱里曲折
……
现在,一个男人沿着这条七彩的河向我们走来了。这个男人叫林祥福。这个镇叫溪镇,或者也可以叫文城。
《文城》确实很有童话感,因为若是以现实的标准,许多情节会显得怪异。例如,主人公林祥福的初始形象是很传统的,他可以因为媒婆的一点怀疑、一个眼神,就放弃中意女子。但很快,他就不走流程娶了来历不明的女主人公小美,甚至在小美卷钱逃跑又怀孕返回后,依然不加追问就娶了第二次……一直发展到变卖祖产、流浪寻妻。
再如土匪绑票一处,土匪原本绑走的是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陈永良夫妇竟让自己的长子跑去替回了林百家,理由是“儿子有两个,女儿只有一个”。用亲生儿子的命去换朋友女儿(最多算是干女儿)的命,这同样缺少现实逻辑的可信度。
某些大情节的设计也让我感到困惑:林祥福准确地找到了溪镇,并且定居下来、发家成为了风云人物。那么,明明就生活在这里的小美阿强,为什么从未被怀疑到?虽说他们在林祥福定居溪镇那年已经死去,但在熟人社会里面,谁家的来历和人员能够从所有居民的记忆及话语中一夜蒸发?这一切始终没有穿帮,似乎也禁不起推敲。即便不去做具体的推敲,我也依然觉得,《文城》的情节看似繁复却过于单薄;看似流畅精彩,却多有莫名其妙和生硬刻意之处。
当然可以替余华开脱。例如,许多人提到了“寓言”这个概念,认为这些不合理之处多是寓言化叙事的特定风格追求。这无法说服我。同样的“不合理”或“莫名其妙”,如果出现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或《鲜血梅花》中毫无问题,但出现在《文城》中就会显得古怪——因为《文城》并不是一场“预先张扬的寓言”,它的扎实真切之处和它的不合理之处构成了内在的不统一。
当然也可以从人物形象来开脱。林祥福典当祖产、千里寻妻,是因他情深义重。陈家以亲生儿子换朋友女儿,纯属于菩萨心肠。至于土匪“和尚”放还林百家、后来又善待陈耀武、乃至同陈永良结成了盟友兄弟,则真心是盗亦有道。这在逻辑上的确说得通。然而问题又来了:我们随即发现,《文城》变成了一部人物扁平的小说。人物要么“好”,好到极端、好到一根筋、好到没道理(小美和阿强的形象比较复杂,但他们的故事主要出现在主体故事结束后的“文城 补”部分里);要么“坏”,比如土匪张一斧,坏到活劈良民、吃人心肝、一眼就知道会“恶有恶报”。
可以说,《文城》主体故事里的人物,几乎是不成长、不变化的,他们只是单纯的活着或者死去,忠实而呆滞地服从于情节需求——这种情况,与他们大起大落、高度极端、充满刺激性和冲击力的“精彩经历”是完全不匹配的。这样“非黑即白”并且“天长地久”的设定,只有在童话里才会有吧!作为小说,《文城》在很多地方是失真或失衡的。它在情节内容、人物塑造、叙事方式等方面,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说服力、也没有提供太多新的东西。
03
“爽”和“甜”
情节逻辑不现实、人物形象不立体,在“小说”的评判标准里是很严重的问题,它们会直接导致小说文本假、空、立不住。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就会发现,不顾逻辑细节,换来了故事情节的通畅狂奔;人物形象不立体,换来了人物特定方面的格外凸显。在客观上,这些恰恰构成了更宽泛意义上的“故事”的成功要素。于是,小说文本固然“假”,故事效果却非常“真”。
在此意义上,我愿意将《文城》同网络小说或者流行电视剧比较来谈。在这类坐标系中,“像童话”就不再是贬义词,情节和人物的“简单化”“类型化”也不再是问题,因为广义的“故事”,其重要目标就是“造梦”——而且,是造熟悉易懂、能够迅速获得辨识的梦。《文城》牺牲了复杂性和真实感,但造出了读者们喜闻乐见的“梦”。这个梦跌宕起伏,这个梦情深义重。这个梦让读者乐于做完,并且做完了觉得很爽。
于是在我看来,《文城》近乎某种“纯文学爽文”。它更精致、更深沉,但内在机理与“爽文”“爽剧”颇有相通。恰好几日前,“北青艺评”公号刊发了唐山的《<赘婿>的垮掉:爽文之后是爽剧爽完之后是空洞》一文,其中总结了“爽剧”的几条基本特征:
首先,情节变化快:从被虐到复仇,不能超两集。
其次,人物极简,情节极繁:只提供类型人物,黑白分明,全靠情节曲折取胜。
其三,人设符合观众的自我心理预期:男女颜值高,无异性交往史,有钱有权。
其四,充满爽点:如智力碾压、完虐对手、调戏强者、有权任性等。
其五,情节游戏化:以直线逻辑为主。
《赘婿》剧照
我发现《文城》高度符合。就拿主人公林祥福来说吧!他在地主少爷、流浪汉、富商大户、孤胆英雄之间无缝切换身份并高速衍生情节,符合第一条。他爱憎分明、一“好”到底,符合第二条。他有钱有才有影响力还痴情盖世,符合第三条。林祥福虽然没过多显示智力碾压、权力碾压,但反复表现出对这世界的道德碾压,是道德价值层面的绝对强者(近乎“民间圣人”),符合第四条。林祥福的故事单线行进,几无旁支,类似“打怪升级”然后“功德圆满”,符合第五条。一条不落,全部吻合,读者读完故事觉得爽快,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此外,我们还能够从《文城》里看到“甜宠文”的影子。这在女主人公小美的身上尤其明显。小说里,小美玩的是“仙人跳”,这事儿实在不光彩。结果呢?原配丈夫和受害丈夫全都对她不怪不怨、宠爱有加,小美也对两个人真情实意、情深意浓。其他人物也显示出对她的宝贵善意:林祥福家的下人没有替少爷不平,提起她时依然是一口一个“少奶奶”;童养媳时代的婆婆,即便一时赌气赶她出过家门,弥留之际还是一直叫着小美的名字,要把家传给她。至于最后的结局,小美惨死、林祥福惨死,并且两人至死没有相见、比邻而死却又彼此不知,则是在“死生亦大矣”的终极抒情上打了一个擦肩而过的时间差——非常典型的“虐恋”设置。
于是,“土味霸道总裁”林祥福,沿着七彩的童话之河,一路寻找着人见人爱的甜蜜宠妻小美,一路顺风顺水、却又求而不得。这个故事是喜剧性的,叫“风里雨里,总裁找你”;同时也是悲剧性的,叫“冰里雪里,来生还你”。无论如何,它都充满了戏剧张力,并且融合了大量高度符合当下读者(我指的是普通读者而非专业读者)所最期待、最习惯的叙事模式及其元素,“诱人”并且“感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故事模式很符合当下受众的习惯和期待,却未必是完全的新鲜事物。例如,丁帆教授在《如诗如歌 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里,就专门分析了小说的传奇性及浪漫叙事风格问题,并且将话题上溯至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传统。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在古典或西方的知识框架内拼死挖掘论证《文城》的艺术价值,我的意思是,《文城》作为“故事”而成功的一面,并非余华(或任何网络文学作家或编剧)的独家发明,也未必只关乎当下一时的消费流行。这一话题,显然比《文城》自身的好坏得失意义更大。
04
“老狮子”
同样比“《文城》好坏”意义更大的,还有其他一些“衍生话题”。
在《文城》里,有一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林祥福的“嫖娼——阳痿”故事。林祥福在溪镇扎根落定之后,终于开始慢慢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他此生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小美了。在这一刻,他恢复为一个正常的、完整的、自由的男人。他勃起了。于是他去寻找那个当年曾被他误认为是小美的暗娼女子,进了她的家门、来到了她的床边……然后,他发现自己“不行”了。而在后面的故事中,林祥福与这位女子建立了某种奇特的,止于触摸、陪坐甚至沉默的依恋关系。故事的最后,这位女子甚至成为了林祥福遗书的托付人。
“阳痿”问题在男艺术家那里是非常敏感而重大的。有一种说法是,达利当年之所以画出那么多弯曲的钟表,背后正是对阳痿的强烈恐惧。这一话题看上去很低俗,但其实质却是低俗行为的永久性缺席(或者说,它就是对这一“缺席”可能性的完全暴露);它以下半身的形式把问题深刻地转移到上半身,在性行为的语境里,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精神化的生命处境——这不是简单的生理功能受损,而是强烈隐喻着整体生命能量的衰退、或者说生命能量的形态转化。
我想起了余华本人。我当然、并且绝对不是说,余华先生的某些功能可能受损。我想讨论的只是,当一个以残酷、冷峻、锋利驰名的作家老去了,当他的生命激情变得柔和而稳定,当他的荷尔蒙和才华不再以当初那种极其暴烈的方式喷射到文字之中,他的作品,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当然可以有很学术的说法。比如“晚期风格”,来自萨义德,前些年貌似很火。比如“先锋的内化”,这不仅仅发生在余华身上,也发生在余华当年的“先锋文学”战友们身上。但我在此想说的是一些更加具体和真切的词。例如柔软。例如温情。例如和解。例如善意。
1993年2月,余华在北京团结湖公交站 (肖全摄)
尽管我对作为小说的《文城》评价有很大保留,但我依然要承认,《文城》背后的余华似乎有些打动我——与此相比,《第七天》背后的那个余华就会让我感到不适,他功成名就,却偏要来不可靠地代言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愤怒和残酷。《文城》背后的余华,让我想起“老狮子”这个形象。血和杀戮淡了远了,它们仍在,但不再使他感到迷恋。他现在看到的是东非草原上的金合欢树,是升起又落下的太阳。并且,他愿意把这画面笨拙地分享给我们。
因此,我对《文城》的直观印象,就是它构成了《活着》的某种“背面”:当然,就艺术品质而言二者几不可比,但如果说《活着》是关于残酷的生存,《文城》则确实试图去讲述温暖的死去。并且当林祥福时隔十七年再次来到那条引领他来到溪镇的河流、再次踏上当年的同一条船,我也真的忆起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那个少年——在残酷成人世界的入口和尽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杨庆祥教授在《余华<文城>: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一文中谈到过余华的转变:“余华将这种转变的缘由归因于一个梦:在梦中有人要枪毙他,他在梦里挣扎,最后发现并没有人来救他的,他感到了巨大的恐惧……这个时候他从梦中惊醒,意识到没有救赎的时刻是多么让人绝望。文学如果仅仅给人提供这个绝望,是有所欠缺的。从那以后他决定要在文学里面提供温暖的东西。温暖是什么?其实就是希望——也就是布洛赫所谓的‘希望哲学’。”杨庆祥随后着重分析了《文城》里的“信”和“义”。温暖和希望是重要的,也是这部不使我满意的小说中少数令我满足的地方——尽管它或许跟狭义的文学无关。但关于文学的谈论为什么一定要是狭义的呢?
同时,我也想起孟繁华教授几年前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情义缺失”的说法,他觉得文学里如果只有恨、只有残酷和背叛,显然是不够的。《文城》里面的情义是足够的,即便这情义显得有点笨拙甚至有点违和,尽管这情义或许是仅仅是策略、或者仅仅来自年龄所带来的必然的坦然与和解。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思考文学本身,去思考当下汉语小说写作普遍存在的某些症候性问题。
因此,在“是个好故事,不是个好小说”这个观点之后,我还要再加上一句:
它本身简单得可商榷,但外围延展得有话题。
-END-
作者简介
李壮,青年评论家、青年诗人。1989年12月出生于山东青岛,现居北京,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有文学评论及诗歌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上海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曾获《诗刊》陈子昂诗歌奖年度青年理论家奖、“新时代诗论奖”、丁玲文学奖、长征文艺奖等。出版诗集《午夜站台》、评论集《亡魂的深情》。
凤凰网读书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联系。
为您推荐
算法反馈精品有声
热门文章
精彩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