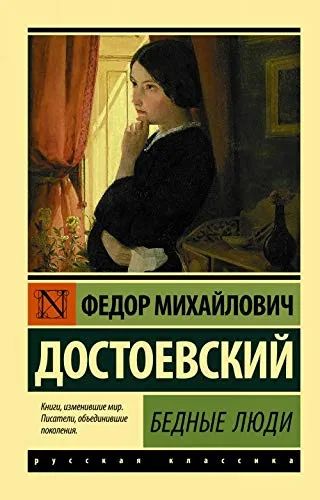撕开遮蔽贫富阶级的幕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坛初亮相


独家抢先看
“有天晚上,我走过他们家门前,那个时候很少那么安静,我微微听见抽泣的声音,原来是有人在哭,哭得那样安静,那样可怜,那样伤心,这些穷人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终夜挥之不去,我无法入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描写穷人,那些可怕的沉默的最底层的穷人,带着他的悲悯、感伤与爱。1845年冬天陀式的初创作品《穷人》,一经发表便惊艳了俄罗斯文坛。在星河璀璨的俄国文学界,陀式艰辛复杂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的创作道路和文学深度。
本文摘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作者约瑟夫·弗兰克耗费数十年,以小说式的文风撰写了陀式五卷本的恢弘传记,也描绘了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画卷。
“我陶醉于其中,整整两天了”
俄罗斯文学中,任何人亮相文坛的掌故都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生动,也没有人引起了他这样广泛、惊人的骚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说法是人尽皆知的,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自己的天真和幼稚,并使其带有感伤色彩。
“[1845年]冬,我突然开始创作《穷人》,我的第一篇小说;之前我什么都没写过。写完小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提交给谁。”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应该拿小说怎么办,有证据表明,格里戈罗维奇当时在怂恿他投稿给《祖国纪事》。
小说完成后发生的事是可以确定的。格里戈罗维奇深深被作品感动,他把作品拿给涅克拉索夫,这两位年轻的文学家都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落了泪。激动之中,他们凌晨四点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时彼得堡正值白夜,日光像白天一样。
第二天,涅克拉索夫将小说拿给别林斯基看,后者同样对这篇作品怀有热情和好感。当别林斯基沉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中的时候,安年科夫来访。他对别林斯基当时的激动留下了书面证实。
“你在看手稿?……我陶醉于其中,整整两天了。这是新手之作,一位新的天才……他的小说揭示了俄罗斯生活和性格中的秘密,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过。想想吧,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篇社会小说…… 它反映的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它关心的是一些善良的人,那些认为爱全世界是至高的愉悦和每个人的责任。他们无法理解生活的车轮是如何用它的规则和秩序悄然无声地碾过他们的身躯,就这么简单,但这是多么动人的故事啊,多么感人的一种作品啊! 我忘了告诉你,这位艺术家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
别林斯基 Vissarion Belinsky (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
别林斯基喜欢激动极端的表达,只有从同俄国风行的对浪漫主义的模仿的斗争和建立俄国文学中的社会现实主义方面,他的反应才是合乎情理的。当时,俄国城镇底层人民的生活已经出现在各种形式的生理学速写中,然而这些速写的重点集中于外在描写和照相式的准确上,而非创造性洞察力和内在的身份认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位将这样的材料应用于具体主题,而非仅仅写作生理学特写的自然派作家。“我常到别林斯基家做客,”他向米哈伊尔在1845年秋写道。“他对我很有好感,他视我为公众前的证明,佐证了他自己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成功创作出别林斯基期待已久的作品。《穷人》在同时代的人中激起的波澜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别林斯基带给俄国文学的新方向。
“他从最下,来观察世界”
《穷人》的形式是两个人的书信,一位是低级九等文官马卡尔·杰符什金,工作在圣彼得堡庞大的官僚体系中的中年抄写员,另一位是十几岁的少女瓦尔瓦拉·陀勃罗谢洛娃。二人都是善良、孤独、脆弱的另类,对方的安慰给自己惨淡的人生带来了一丝温暖。然而,这天真无邪的田园诗很快被他们正在顽强抵抗的、卑鄙的力量终结了。瓦尔瓦拉绝望的境遇和眼前一个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迫使她接受了一份婚姻,这本书在杰符什金的悲戚中结束,因为瓦尔瓦拉将永远消失在他的生命中,走入新郎贝克夫(Bykov)的园地(贝克夫在俄语中意为“牛”)。
《穷人》
《穷人》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灵巧地运用书信体,把藏在人心里最隐秘、最难以启齿的想法说了出来;信中字里行间的情感远远比内容来得重要。或者说,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张力让我们走进了他们真正的心智。
乍看上去,杰符什金是多么的简单、天真,事实上却是一个不断和自己做斗争的人物。他为了取悦瓦尔瓦拉,变得拮据,为她买那些他买不起的糖和水果,他承受着侮辱,但却试图掩饰,因为这来源于贫穷;在与瓦尔瓦拉的情感纠葛中,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叛逆思想,这同那个时代他脑中自然而然接受的顺从的信条完全相悖。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两个简单的主人公的故事置于众多其他情节之中,一下让小说获得了真正的社会维度。瓦尔瓦拉插入的日记将我们带到她还是乡村女童的时代,其中还包括有肺病的学生波克罗夫斯基的肖像描写,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次出现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形象,后来发展为拉斯科尔尼柯夫。他名义上的父亲,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娶了怀着贝克夫的孩子的一个女孩为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带着一种狄更斯式的哀婉,特别是描写这位老汉护送自己受人尊敬、受过教育的孩子的灵车走向最后安息之地的场景。
“老人好像没有感觉到恶劣的天气,哭着从大车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他那破旧的礼服的前襟随风飘扬,像是一对翅膀。那些书从每个衣袋里突露出来;他两手拿着一本大书,紧紧地抓住。……那些书不断地从他的衣袋里掉到污泥里去。有人叫住他,告诉他丢了东西,他就捡起来,又赶快去追灵柩。”
另一处插入的情节是饥饿的小职员戈尔什科夫(Gorshko)一家,从外省赶来,为自己在政府服役期间的贪污罪正名。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断出现的最底层的贫穷的家庭的原型,他们的特点是可怕的、不正常的沉默,似乎在哀号中埋得太深。他们的孩子都不作声,杰符什金告诉瓦尔瓦拉:
“有天晚上,我走过他们家门前,那个时候很少那么安静,我微微听见抽泣的声音,原来是有人在哭,哭得那样安静,那样可怜,那样伤心,这些穷人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终夜挥之不去,我无法入眠。”
以上叙述都构建了一种力图在人前掩饰他们正在承受无力抗争的压迫的形象,理智、感悟力、道德升华都出现在本不该出现的地方,至少当时俄国文学的观点这样认为。到处是贫穷和侮辱,到处是豪强对弱小的剥削,彼得堡拥挤的贫民窟的瓦片房漏着雨,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穷人》向生理学特写最精华的图片描写中加入了对蒙受羞辱的人类理智的精确洞察。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果戈理的最大创新是,他从最下,而不是从上来观察世界;果戈理对他卑微的主人公的同情从没有强到可以克服内含于叙述中的屈就立场。《穷人》的立场和心理直面阶级傲慢与阶级偏见,直面莫须有的上流社会优越性。尽管别林斯基对书中包含着直言不讳的抗议之声只字不提,但他绝非漠不关心。
“没东西吃的时候,名誉算什么”
杰符什金在书中经历了显著的进化。早期的信件揭示,他全不抱怨地接受了自己的卑微地位,甚至还自觉地对自己能够完成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而沾沾自喜。尽管低谷时,他也会借酒消愁。他本不会感到屈辱和自己一无是处,这时他顺从的心中闪过一个造反的火花。 他在遍地是奢侈品商店和衣着华丽的彼得堡街头,感受到了他们与自己出身的贫民窟里那些孤寂、悲苦的穷人的差别,突然间开始幻想,为什么他和瓦尔瓦拉要忍受这种贫穷,而其他人生而富贵。
“我清楚,我清楚,我亲爱的,这么想是不对的,这不过是随便一想而已;但直言不讳地说,说真心话,为什么命运像乌鸦一样在人还未降生就宣告了某些人的幸福,而其他人就该生在孤儿院里?”
财富和个人奋斗看起来毫无关系,杰符什金的“随便一想”同革命思想也是一样。我们在后文可以发现,杰符什金惊人地说出了圣西门式的思想,最卑微的工人更值得人尊敬,因为他对社会比那些富人、那些贵族有用。这一切将杰符什金推向了那穿透人心的、贫富对比的梦境,像欧仁·苏或是苏里耶的小品文一样,撕开将两个阶级生活遮蔽起来的幕布,让人们放在一起,看个究竟。
电影《镜子》
那边,在一个烟雾弥漫的角落里,在一间潮湿的,因为穷而用来作住房的小破屋里,有一个手艺人刚从梦中醒来。比方说,他整夜梦见昨天无意中剪坏的一双靴子,好像一个人就该梦见这种没价值的东西似的!……他的孩子们尖声哭叫,他的妻子在挨饿。不光是皮鞋匠有的时候早上起床是这样……小宝贝,就在这,在同一所房子里,在楼上或者楼下,一所金碧辉煌的宅子里,住着一个大阔佬,也许夜里他也梦见了这么一双靴子……另一种剪法,可是仍然是靴子,因为就我所指的这个字的意义来说,小宝贝,我们都有点像皮靴匠,我的亲人。……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在大阔佬旁边,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得了吧,不要再想那些事了,不要光想着你自己,只为你自己一个人活着了。……你的孩子身体健康,你的妻子没有去要饭。瞧瞧你的周围吧,你就看不到有什么比你的靴子更高尚的东西值得关心吗?”
权贵富豪们对周围穷人遭遇的视而不见让杰符什金深为气愤,以至于他在恍惚中感到,他其实有一种误置了的自卑感。“走到最底层去,”他说,“然后再评价一个人毫无理由地放纵自己和忍受屈辱是不是正确。”
这一部分包含全书的中心社会主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版的法国19世纪30年代社会小说,是像狄更斯一样的认为权贵应对那些相对不幸的弟兄负起更多道德责任的劝教。 这一主题的高潮是杰符什金面对政府里的上级的场景,这位卑微的抄写员,因在抄写过程中漏掉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而遭到责骂。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情感:
“我的心在我胸腔中颤抖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害怕。我只知道我有生以来还没像这样害怕过,我坐在椅子上仿佛生了根一样,就跟没那么回事似的,好像叫的不是我。”
他那时的表现如同稻草人一样,他最后一颗扣子掉落,他试图去将其捡起,就好像一种辩白。感动于他如此明显的窘态,善心的将军自掏腰包给了他100卢布。当后者为了表达感谢而亲吻将军的手时,将军涨红了脸,屈尊和他平等地握了握手。
“ 我发誓,尽管在我们充满不幸的、最苦的日子当中,”他向瓦尔瓦拉说,“我瞧着您,瞧着您的穷困,又瞧着我自己,瞧着我的卑贱无能,我心里悲痛得要死,虽然如此,我向您发誓,这一百卢布对我来说还不算宝贵,宝贵的倒是承蒙大人亲自握我这么一根麦秆、一个醉鬼的卑贱的手。”将军不仅感受到了杰符什金经济上的窘境,更发现了他维护自尊的渴望——这使将军在施舍的同时,避免了再一次侮辱。
电影《镜子》
别林斯基为这一幕深深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别林斯基在他们首次会见时,高度赞扬了这一场景。“那掉落的扣子!亲吻将军的手的那一刻!再也没有这位不幸主人公的同情,唯有恐惧!这份感激之中,是恐惧!”握手中展示了微妙的情感,内含对卑微的杰符什金的平等的认同,作为一个象征出现了两次。
杰符什金很反感,在富人施舍给他贫困的酒友艾米里安·伊里奇前,竟然调查了他,杰符什金将其视为对艾米里安尊严的侮辱。无独有偶,当戈尔什科夫赢得诉讼后,到处说自己的尊严又回来了,但作家拉塔齐亚耶夫竟然嘲讽道,在没东西吃的时候,名誉算什么,钱比什么都重要。杰符什金觉得:“这对戈尔什科夫是种侮辱。”
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感受到精神上的平等同物质上对不幸的人救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贫穷,人的自尊需求将达到病态的程度。 事实上,《穷人》最重要的主题已经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作品中重要的张力。在《穷人》中,精神与物质的张力是暗藏的,处于一种平衡;对精神维度(或者说,是道德心理)的强调不过是为了凸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物质生活上所承受的不公正的同情。
但是进入19世纪60年代,当一种攻击性的、狭隘的唯物主义成为俄国激进派的意识形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激进派决裂,捍卫“广义”上的精神。人物质需求的满足同内在道德心理的对立,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登峰造极。
将军的帮助,虽然使得杰符什金渡过难关,但无法解决他的人性问题。随着主题从贫穷到杰符什金无法留下瓦尔瓦拉,这部小说进入尾声。将军施舍的姿态无法解决杰符什金的一切问题,很好地指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将自己的主题置于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即社会只是人复杂纠葛的一个元素而已。死在重新获得尊严与安定那一天的戈尔什科夫的命运,再一次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问题的自觉,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角度的解决方案。
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将主题视界拓展的动机在后文还有体现。书前半部分,杰符什金只反对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公,在结尾处,出现了对上帝智慧本身的一种胆小的质疑。当瓦尔瓦拉同意了求婚,并将自己的命运归因于上帝“神圣、深不可测的力量”时,杰符什金回答 :
“当然,一切都得依从上帝的旨意,所以定是如此,这一定也是上帝的意思;天庭的统治者,当然是法力无边的,命运也是如此,都一个样……瓦林卡啊,这一切怎么这么快,……我……我将一个人了。”
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形而上学走向,从社会公正问题的限制中走出,或者这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重视眼泪”
《穷人》作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控诉,是一个高度自觉的复杂的作品。在整个18世纪,书信体小说已经成为表达美德与理智的形式,比如理查德森的克拉丽莎·哈罗和卢梭的茱莉,抑或诗意和值得赞美的高贵的灵魂,比如歌德的维特,这些是高尚情感和思想的表达。
书信体因此已经成为夸张的浪漫主义感伤的表达形式,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它们的主人公是榜样式的人物。事实上,其中的社会性在于主人公道德和精神上的高尚同他们所生活的堕落的贵族特权世界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同样的目的,用同样的形式来描写下层人民。
然而,由于这种感伤主义的书信体小说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用来描写受过良好教育和具备高尚情感的人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做是艺术上的巨大冒险。 用这样感伤主义的形式来描写一位老抄写员同不受尊敬的女佣人之间最终破产的爱情故事,违背了当时已经接受的叙述原则,但我们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做法非常自觉。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新地使用了书信体的形式,正如维诺格拉多夫所说,一反当时对彼得堡小公务员肖像描写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可上溯至19世纪30年代,将人物仅仅作为对滑稽故事讽刺描写的材料,而直到1842年,人们才意识到如此流行的文学风尚对小公务员是多么不公平。
果戈理 Gogol,俄国批判主义作家,代表作《死魂灵》
果戈理的《外套》继承了这一传统,保持了他讽刺、诙谐、俱乐部里谈趣闻轶事的笔调。果戈理甚至也向这一讽刺故事插入了一丝感伤主义的同情,但这种同情依然是从外部、从高处发出的。因此,这个段落与全书对阿拉基·阿卡基耶维奇轻蔑的对待方式只能形成一种附加的道德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同,在全文的书信体感伤主义形式中,仅用了这一处诙谐用笔来描写贫困潦倒的小公务员,打破了讽刺形式,同时同自己的“慈善”主题融为一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将基本上视其为果戈理的继承者,当今的批评家则关注于他对果戈理的人物和主题的“仿拟”创造,即他将诙谐和诡异的笔调转换为感伤主义的悲喜剧的形式。这些观点无法自圆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转了《外套》中嘲讽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一些形式特征。这种反转并不颠覆果戈理的重要地位,反而加强了他明显的“人道”主题。果戈理的叙述技巧在于他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种诙谐距离,防止读者产生情感认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其道而行之,舍弃讽刺特征,而代之以感伤主义的书信体形式,重构了杰符什金的人性和理智。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准确的术语去指代这一形式上的、以强化主题为目的的仿拟。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的关系远不是一种对抗,而更像一位充满同情心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力将一部作品的形式重构,使其与内容更为和谐。《穷人》和《外套》都包含着果戈理风格的“笑声背后的眼泪”,但是它们的比例是不同的,笑声是果戈理的最高要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重视眼泪。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