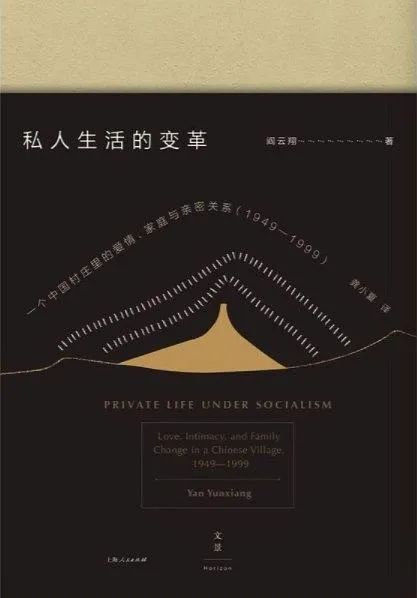中国彩礼变迁背后,是父权的衰落
“彩礼”是中国传统婚姻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表层意思是男方家庭为了促成婚约,所给到女方的资产数目。但在上世纪数十年的彩礼习俗变革中,其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和家庭观念也在逐步变化。
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文化人类学家阎云翔以1949年至1999年50年间的东北下岬村为研究对象,记录并分析了该村落在爱情、婚姻、家庭结构、生产方式等多个方面的变化。在有关“彩礼”的部分中,作者展示了中国农村的彩礼从最开始的金钱,逐渐发展为复杂的钱和物的混合体,进而重新简化为金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家庭模式和个体的生活观念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彩礼与遗产预支
在人类学研究里, “彩礼”通常指的是从新郎家向新娘家转移的资产,它的作用在于敲定两家之间的婚姻契约,而使妇女从一家转手到另一家。 而之后,这彩礼也经常被女方家长用来给自己的儿子娶亲。相形之下,嫁妆则通常被看作是女儿从娘家支取的自己的家产份额。 在欧洲与亚洲那些高度等级化的社会里,嫁妆是提高女家地位或新娘在婆家地位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嫁妆中有一部分往往就是出自男方付给的彩礼。Jack Goody把这种复杂的做法称为“间接嫁妆”。在下岬一带,由于嫁妆在婚姻财产转移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所以我的调查基本集中在彩礼上。
我问村里人彩礼包括什么,他们无一例外地马上回答: 钱和物 。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彩礼中的钱都是由男方家直接交给女方家,这也就是学者们常常提起的 “新娘礼金” 。
而彩礼中的物,大约包括这么几类:(1)家具;(2)床上用品;(3)自行车、电视机等大件,这都由男方家庭负责买齐,作为公公婆婆给新婚夫妇的礼物。这也许可以被称为 “直接赞助” 。
彩礼支配的变化从收取礼物一方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钱还是物,都可以被看作男方父母对儿子儿媳的婚姻赞助。表6显示了过去50年来彩礼的变化。
表6 新郎家提供的结婚资金(元)
第一项:礼钱。这笔钱本来的用意,是给女方父母为女儿准备嫁妆的。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女方父母经常用这笔钱来给儿子娶媳妇。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彩礼只以金钱的形式支付。也就是说,在60年代中期以前,女方父母对彩礼有完全的支配权。 所以,高额彩礼的受益者基本上是女方的父母。
第二项:“买东西钱”,这是6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这是男方家给女方家为新娘买衣服、鞋袜之类小东西的。不过,男方家并不会将这笔钱给到新娘父母手里,而是用来买了东西送到女方家交给新娘本人。在成婚那天,新娘会带上这批东西,连同她的嫁妆一起到新郎家去。这些东西是她的私人物品。 这一项目的出现很具重要性,因为那是专给新娘的。
60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三类项目,就是所谓“装烟钱”。与“买东西钱”不一样的是,这笔钱是直接给新娘的,以酬谢她在婚礼上为长辈装烟。我认为, 这是彩礼制度的第一个根本性变化。 尽管这笔钱并不多,在60年代通常是20—50元,但这是第一次出现了由新郎家直接给到新娘自己手里的钱。正如表6显示的那样,到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笔装烟钱的数目增加了不少,同时增加的还有“买东西钱”。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里,男方的家庭不再控制这笔“买东西钱”,而是将钱交给未婚夫妇,让他们自己去买东西。 这一变化反映了新郎新娘在整个婚姻交换中的重要性大为上升。
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彩礼中涉及金钱的部分都被归入一个新的项目:干折。所谓干折,就是将彩礼折成现金。现金的总额会列在彩礼单上。更重要的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笔彩礼干折在订婚仪式上直接给到新娘本人手里。 这就使得干折与过去男方以各种名义给女方父母以现金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根据下岬人回忆,干折是1985年开始流行的,起因是当时传说1985年后盖房子就不会再分到宅基地了。那些准备结婚的人担心失去申请宅基地的机会,所以许多人就让他们的未婚妻在要彩礼时全部要现金。这笔钱之后就用来买盖房子的建筑材料。干折的数额也随之增加,之后更是连年递增。
男方父母给新婚夫妇的彩礼这期间也逐渐从实物变成了现金。前面提到过,这类彩礼本来包括三种:家具、床上用品和自行车、电视机等大件。表6显示,在50年代的婚姻契约中不存在这些彩礼,而到60年代才开始一点点出现。 但在70年代,新婚夫妇对这类礼物的要求大大增加。 先是家具成了结婚的必备品,再就是出现了所谓 “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 很快又加上了相对高档的床上用品。虽然这些东西都直接写在彩礼单上,但它们不是给新娘的礼物,而是给新婚夫妇小家庭的用品。
80年代出现了更大的变化。 老的“四大件”依旧出现在彩礼单上,而新的大件又不断地被加了进去。 这些新大件包括 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摩托车。 原先对好家具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下流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到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新的干折,将彩礼提到了空前的高额。根据这种新的办法,所有购买东西的花销也都折成了现金,而这笔现金都给了新娘,这被称为“大干折”。 男女两家都以这种方式认可了新娘是新的小家庭的代表; 原本由男方父母直接给新婚夫妇的礼物就这样逐步变成了折现的金钱。到90年代末期,大干折还包括盖房子或买房子的钱,有时甚至包括重要的生产资料,例如承包的土地或拖拉机。
总的来说, 在过去50年里,新郎父母提供给新婚夫妻的彩礼已从简单的金钱发展为包含6个金钱与实物项目的复杂彩礼;而在最近这些年里,这又重新变成了只有金钱一项的大干折。 表7显示了这一变化。
表7 彩礼的变化
每一个新项目的出现都体现了婚姻契约中的新关系,从而也体现了婚姻交换程序的逐步变化。 另外,尽管政府一直严厉批评买卖婚姻,但婚姻的平均开支却从50年代的大约200元上升到了1999年的2.85万元。不过,高额彩礼却并不等于国家意识形态中说的买卖婚姻。因为女方父母不一定能够从男方家的彩礼中得到什么利益。事实上,彩礼金额的上升主要是给小夫妻的东西有所增加才造成的,而且干折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婚姻契约中金钱转手的性质。如今新娘以及躲在新娘背后的新郎对男方家提供的彩礼有了完全的支配权。
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后期,订了婚的姑娘基本上不直接参与购买订婚礼品,而是通过在婚礼之前监督礼物的准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她们有许多办法来判断男方家是否按照答应的条件来准备,比如在婚礼前请人去检查礼物准备的情况,或者是向对方提出具体的礼物要求等等。
自80年代后期开始,干折这种新办法使得新娘对婚姻契约中的财产部分有了几乎完全的支配权。 结果,新娘通常变得更加“贪婪”,对彩礼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991年7月,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彩礼谈判。其中最难对付的竟是姑娘本人。她坚持要5500元的干折,而男方家最初提出的是4000元。最后,双方以5000元敲定,另外再给姑娘500元的装烟斟酒钱。在订婚仪式完毕之后,她得到了3000元,而婚礼之前她还会拿到余下的2500元。
年轻姑娘索要高额彩礼的真正目的是为将来的小家庭积聚更多财富。 1989年的一件事,使我注意到了新郎在彩礼上涨中起到的作用。有个年轻人鼓励他的意中人向自己的父母索要高额彩礼。据说,他告诉姑娘一定得要4000元的干折,否则她就不干。他说,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从他妈那里要到钱。而另一方面,他对家里说,除了这个姑娘他谁都不娶。结果,这姑娘果然得到了所要的一切,而且他们结婚几个月后就分家单过了。村里有人说,小伙子在订婚之前已经打算好了分家。有人还告诉我,这件事情并不算太特别,因为近年来许多小伙子嘴上不说,暗地里都这么做。 这里面包含的重要信息在于, 如今村里许多年轻人恐怕在开始谈恋爱之时就已经在计划其未来的小家庭生活了。
1991年还出了一件令许多人吃惊的事。有个新娘竟然要求将男方家里的粮食加工厂作为彩礼的一部分。这家的新郎还有个没结婚的兄弟。最后,工厂被分成两半,两个儿子各一半。在整个90年代,彩礼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在过去所没有的项目,比如土地、奶牛、拖拉机等。 这些都是生产资料,它们进入彩礼单意味着年轻夫妇正在为他们自己的小家庭积聚生产资本。
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
在早期的婚姻财产契约里,新郎的家庭将彩礼交给新娘的家庭,目的是为了保证新娘的嫁妆最终能够成为新婚夫妇的财产。但是,这对夫妇在大家庭没有因为分家而自然解体之前并不具备独立性。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妇女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都对她们的嫁妆有控制权。但是, 因为彩礼这部分是通过新娘的父母来给到新娘手上的,所以新娘父母就对彩礼中多大部分能够以嫁妆的方式给新娘有了决定权。 当新娘家里穷时,父母通常就将这笔钱挪作他用,这样,这种中国式的间接嫁妆也有了流行于非洲的彩礼制度的色彩了。
90年代,下岬村的结婚礼物是以干折的方式从新郎家直接给到新娘手上。新娘则在新郎的合作下,从婚姻契约开始谈判起就完全控制了彩礼。而通过分家单过,新娘就能利用这笔财富在结婚后马上建立自己的小家。 前后两种彩礼的根本区别在于,前一种方式无论是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都没有以建立新的小家庭为目的,新郎新娘的个人利益完全被父母的权利与大家庭的需求所压倒。而在后一种方式里, 新郎新娘小夫妻的利益推动了他们去索要更高的彩礼和嫁妆,新娘与新郎都在婚姻契约谈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结果,彩礼不再像原来那样是双方父母用来保证新娘出嫁或者建立亲戚关系的手段;借用Goody的概念,彩礼干折变成了新郎要求分割家庭财产的一种办法。换句话说, 彩礼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礼节性的礼物交换或者支付手段,而是财富从上一代往下一代转移的新途径。
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
在下岬村,分家的时间自80年代初期便不断提前。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期,为社会所接受的时间是在次子结婚之后长子才提出分家要求,而这一般要求长子在婚后与父母同住3年至5年时间。至少,一对青年夫妇也要等到生育后才会另立门户(即至少有1年以上的从父居时间)。
我在1991年的调查中发现,自80年代后期开始,近1/3的新婚夫妇不等生育便与男方父母分家;40%以上的青年夫妇则在生育之后立即另立门户,不再等到丈夫的弟弟结婚。这种趋势在1994年到1997年之间变得更加明显:80%以上的新婚夫妇在丈夫的弟弟结婚之前分家;其中又有40%以上的夫妇分家时尚未生育。在1991年,分家最早者是婚后7天。在1994年,两对新婚夫妇在婚礼之后即直接搬入自己独立的新房子,根本没有遵守从父居的习俗。这一趋势发展到1997年春季,便导致一对青年干脆在自己的新居举行婚礼,而这新居却是新郎父母出资修建的。
在分家与婚姻财产转移的过程中,财产本身固然要紧,但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却更加重要。 在许多情况下,提早分家实际上对无论是老的家庭还是新的小家庭在经济上都非常不利。年轻夫妇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通常比留在大家庭内部会遇到更多的麻烦。然而,通过一系列单过的方式来提早分家却越来越普遍,因为分家能够解决由谁来控制家庭经济的问题,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倒在其次。1994年,有个刚刚分家的年轻妇女对我解释说,大家庭里固然有许多东西,但却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丈夫的父母和兄弟。 在她自己的小家庭里,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自己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所以她觉得很愉快。
谈到控制权,分家可以说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 分家不仅重新分配了家庭财产,而且重新界定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 同样,彩礼嫁妆一直是被父母用来作为控制成年子女、在家庭内部延续自身权力的手段。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代际之间不断的讨价还价,父母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对家庭财产的控制。 这一切又反映了父权的衰落与男女青年权力的上升。
是什么使得年轻人在为家庭财产同父母讨价还价时那么有力量、有办法呢?须知,对家庭财产的控制是体现父权的最重要的一点。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变化,包括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国家政策的影响、市场经济改革等等都是相关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直接导致父母失去对家庭财产的控制。从微观角度看,我发现积累财富的新方式以及人们财产权利观念的变化恐怕是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研究台湾农村的分家现象时,Sung提出要区分继承的财产与挣得的财产。继承的财产,比如土地和房屋,是通过男性继承人一代代传下去的,这样家族中的男性就得以完成传宗接代的职责。同一家系中的男子都平等地享有这类继承权。与此相比,挣得的财产则是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份。至于父亲在分家时的权力,Sung认为:“当父亲的财产如果是继承来的,就比是在儿子的帮助下挣来的情况下对儿子更有控制权。他作为父亲的地位就会因为他所兼有的家族财产掌管人的地位而得到加强。” 而如果家庭财产是阖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父亲的地位就会大大被削弱。
用上述这种财产是继承还是挣来的标准来考察下岬家庭财产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下岬年轻人之所以能够要求早分家以及高额彩礼和陪嫁,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对家庭经济的贡献。1949年以后激进的社会变革完全改变了传统财产积累的方式。土地改革运动使得村里人的经济地位基本平等,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更进一步剥夺了农民家庭中可能继承下去的财产,因为土地、大牲口等重要生产资料都集体化了。 从那以后,家庭财产主要是由家庭成员通过个人劳动所积聚的。 虽然在集体化时期家庭还是分配的基本单位,但是同时,个人对家庭经济的贡献通过工分制度和其他集体化的制度而显示得明明白白。
50年代中期集体化运动
在集体化的会计制度中,每个个人的劳动所得记成工分。在秋收后再转变为现金。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挣了多少工分都是公开的,并且会在年终贴在大队部的墙上。这样一来,每个人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就一清二楚了。这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因为他们的父亲再也不能像在传统的农民家庭里那样,否认家庭其他成员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另外,年轻人比上一代人更容易适应新的集体化耕作方式,也能更快掌握新技术,当工分公布出来时,许多年轻人比他们的父亲挣的工分更多,年复一年,他们就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结果,他们很清楚自己对家庭经济有着什么样的贡献,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对家庭有多重要。这样,他们在家里也很自然就不再那么听话了。正如村里一位老人说的那样: “年轻人一旦能够自己挣饭吃,坏脾气就来了。”
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家庭财富主要是通过个人贡献而不是继承来积累的,人们就日益倾向于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家庭财产。 特别是在过去20年中,村里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在家庭财产中的份额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意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在彩礼与嫁妆方面发生的变化。我多次问年轻人,为什么他们在索要彩礼和嫁妆时那么坚决,那么不管不顾,他们一概回答说,他们努力干活,给自己家做了大量贡献,他们要的不过是这么些年来自己的劳动所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 年轻人并不认为他们通过彩礼与嫁妆或者分家得来的那部分财产是他们拿了家庭财产中的一份,他们觉得那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财产。 这种像是从家里拿走自己存款的意识正是集体化时代留下来的。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对家庭财产的要求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家长权力,颂扬现代化,使得长辈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两代人在就家庭财产讨价还价时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处于平等地位。结果,年轻人强调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少谈甚至不谈他们的责任与义务。这种不平衡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年轻人忽视了赡养老人的义务。 在家庭生活这另一重要领域里,父权同样也衰落了。
本文节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