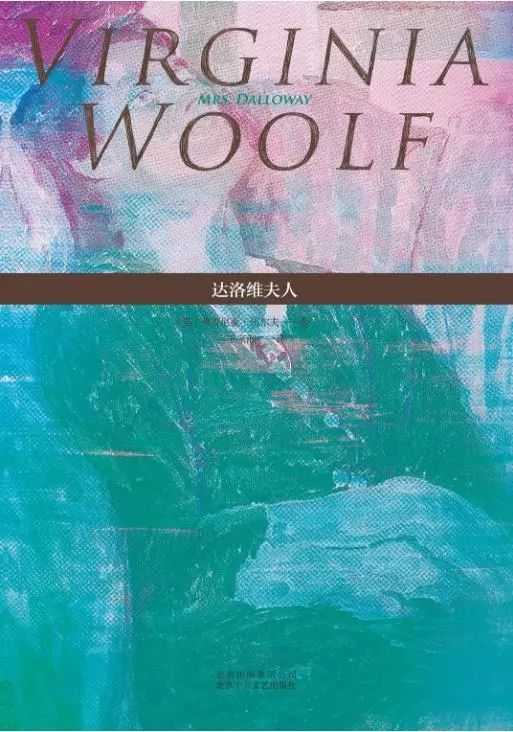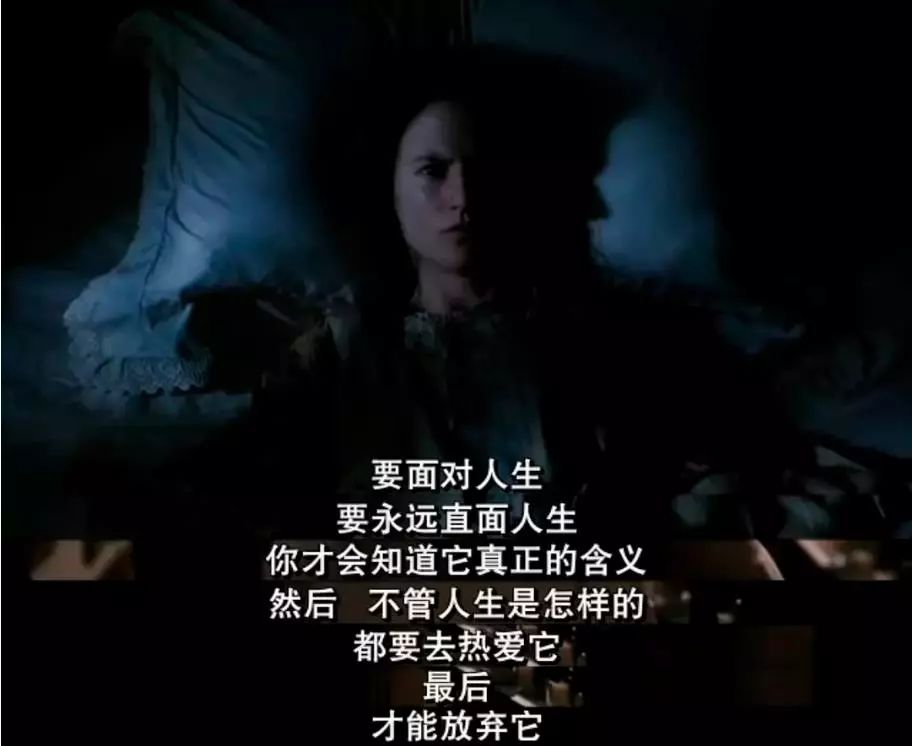伍尔夫:一个被净化的文学女神


独家抢先看
1
“诗人会死,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幸福。”——《时时刻刻》
电影《时时刻刻》,尼可·基德曼饰演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依然流行。在世时,她是英国最潮流的作家、演说家,去世后,她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洞察、对父权社会和传统写作的批判仍然深入人心。或许伍尔夫自己都没想到,她的书漂洋过海,化身遥远东方女权主义者们的文艺圣经,“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成为她最有名的句子。
伍尔夫幻化成一个永不妥协的符号,如同一位高尚激昂的斗士,指引着异国女性的斗争。但她被神化的过程,也是被误解的过程,后人呈现她的敏感和痛苦,她作为精英女作家的优雅和从容,却抹去她刻薄恶毒、尖锐粗粝的一面,当伍尔夫被语录化、偶像化,我们离真实的她也渐行渐远,而这些虚假的崇拜,才是真正应该被打破的东西。
1882年,伍尔夫出身于英国伦敦的文艺世家,年纪轻轻就接受了优渥的教育,但早早失去母亲(1895年5月)和父亲(1904年2月),使她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期间,她两次精神崩溃,并试图跳窗自杀,死亡和疾病让她的内心时常处于不安之中,对世界充满了消极的情绪。
伍尔夫旧照
但“诗家不幸文章幸”,精神危机早早炼就出一颗敏感的灵魂,也让伍尔夫对文学和处世都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这不是一个优雅灵动的伍尔夫,而是傲慢率性、说话刻薄、对维多利亚时代不屑一顾的伍尔夫。
得益于出身,伍尔夫不必沾染工厂的粉尘,也无须下地劳作,她在青春时就接触到英国最优越的知识分子,大谈艺术和审美的边界。阶层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伍尔夫,令她傲慢,也令她更加大胆。她敢于乔装打扮成阿比西尼亚的门达克斯王子,愚弄大英帝国的国家机器,也敢于身着奇装异服,大胆地谈论性与爱。他和朋友们聚集起的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成为那个年代最大胆的知识团体,也最受文化界的争议。
罗沙蒙德·莱曼(左)、约翰·莱曼(中)和林顿·斯特来彻,他们都是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成员,从1905年左右直到二战期间,这个团体都一直存在。它的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成员包括:雷顿·斯特拉奇、维吉尼亚·伍尔夫、李奥纳德·伍夫、E·M·福斯特、维塔·萨克维尔、罗杰·弗来、凡妮莎·贝尔、克里夫·贝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
这个团体打破清规戒律,蔑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条文,他们不谈国家大事,伸张自我欲望和纯粹审美,伍尔夫是其中最耀眼的一员,她针针见血的评论、贵族式的高冷,还有异于淑女的新潮做派,让她在伦敦文学界声名鹊起。
在那个女性露出光滑脚踝都会引起争议的年代,伍尔夫敢于书写同性之爱。《达洛维夫人》里,克拉丽莎思忖道:“关于爱情这个问题,同女人的相爱,又是怎么回事呢?就说萨利·赛顿吧,自己过去和萨利·赛顿的关系,难道不是爱情吗?”《到灯塔去》中,莉丽和拉姆齐夫人则发展出超越友谊的关系。伍尔夫热衷于写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却对异性之爱含糊其辞,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多次拒绝了异性的求婚,即便后来与深爱她的评论家伦纳德结婚,伍尔夫也极力避免着性关系。
《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一书指出:“由于早年遭受到达克沃斯兄弟的性侵犯,她的潜意识里深深植入了对男性的畏惧与反感,即戈登所说的强化了的‘自我保护的童真意识’。据说因为她所表现出的性冷淡,朋友们称她是‘冰冷的鱼’(cold fish)。她对异性亲密关系的心理拒斥使她对婚姻态度犹豫,并导致婚后性生活的失败。”
种种前卫造就了偶像一般的伍尔夫,也是后人最津津乐道的她,但早在青年时期,伍尔夫就表现出自己阴暗的一面。在她的早期笔记《卡莱尔的房子和其他素描》(Carlyles House and Other Sketches)中,伍尔夫不仅直面自己的精神危机,而且“痛苦地审视自己的偏执,审视自己所属阶级的偏执”,这个女人高傲又势利,浪漫又俗气,她把她对犹太人的歧视,对劳动阶层的偏见都写了出来,但与此同时,她批评地最恶毒的其实是她自己,还有她所处的阶层。
日记里的伍尔夫依然才华横溢,但也“明明白白地令人生厌”,所以在她去世后,这些内容被小心翼翼地淡化,服膺于讨人喜欢的伍尔夫神话中。
2
“达洛维夫人说要自己去买花。”——《达洛维夫人》
年轻的伍尔夫生逢其时。
彼时,西方处于文学革命的开端。庞德在湿漉漉的地下铁站徘徊,《尤利西斯》成为禁书,籍籍无名的海明威还在绞尽脑汁出名,哈代和高尔斯华绥的写法则成为被挑战的对象。伍尔夫捕捉到浪潮的变化,尽管一开始并不喜欢《尤利西斯》的写法,但她很快意识到叙事革命的必要。
她认为:现代的人性和过去相比有微妙的变化,现实主义已不能准确描摹时代人心的巨变,在1922年的论文《狭窄的艺术之桥》中,伍尔夫大胆设想:“未来的小说可能是一种诗化、戏剧化、非个人化、综合化的艺术形式。”而在《论现代小说》一文,她把作家的任务从书写时代转向内心世界,要记录“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从而描绘出“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定、解说的内在精神”。
现代主义者认为,传统叙述虽然宏大,但因为作者的全知叙述和对人物内心的忽略,导致了小说细部的粗糙同质,而一个人的一天尽管只有24小时,她的所作所为、内心思量,已经足够延展成一部小说的体量,伍尔夫就是这种叙述的实践者,她的《到灯塔去》《墙上的斑点》和《达洛维夫人》等,如今都成为意识流的经典。
伍尔夫刻画人物的心灵,绝不主张废话连篇。她早早继承了父亲干脆利落的文风,在写小说时,她的笔调总是清冷而疏离,令人后背发凉,又禁不住默默点头。伍尔夫的干脆在随笔和评论里也可见一斑,她讥讽作家贝内特啰里啰嗦,调侃E·M·福斯特说话温吞,在《普通读者》里,她批评《简·爱》这类故事“总是当家庭教师,总是堕入情网”,“夏洛蒂·勃朗特没有塑造人物的力度和宽阔的视野”。
在小说《达洛维夫人》里,伍尔夫写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头:“Mrs. Dalloway said she would buy the flowers herself.”(达洛维夫人说要自己去买花。)在此,一个明白爱情与欢喜仅仅关于自己的女性横空而出,她渴望挣脱囚笼,却又患得患失,贪恋自由的乐趣,又纠结于日常琐碎。
高度的自我塑造了她,却也淹没了她。她是又不是伍尔夫,她被称作达洛维夫人。前缀是个Mrs。她曾在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出航》中短暂出现,如今她要自己举办宴席。她要在意识流中暴露自己的懦弱、自私、怀疑、患得患失,但毫无疑问,她会让读者心生共鸣、溢出同情。
《达洛维夫人》的创作年份是1923~1925年,那时候,“布鲁姆斯伯里的王后”不安于乡下的佣人与助理。她像是一只五彩斑斓的囚鸟,歇斯底里,惴惴不安。她明白丈夫伦纳德的好心,可她意识到自我正随着伦敦渐行渐远。
电影《时时刻刻》就记录了这一过程。电影有一幕值得我们留心——伍尔夫避开周遭的人,躺在地上,面对一只将死之鸟,那只令伍尔夫久久凝视的鸟,它的出现、它的死亡,是导演在暗示伍尔夫的命运。
也许,这也是他对小说《达洛维夫人》的一种致敬。将死之鸟是达洛维夫人的象征,也是停留在伍尔夫脑海里的“惊惧”的象征。伍尔夫躲避他人,凝视着这只鸟儿,她仿佛预见了自己的命运。她的眼中有同情,也有恐惧,在那一刻,她的心境正如同《达洛维夫人》所描绘的:
“她命中注定要被这个可恶的折磨人者摇来晃去。可究竟是为什么呢?她像一只小鸟,躲在一片树叶形成的薄薄空间里,当这片树叶摇动时她对着阳光眨眼睛,而当一根干枝断裂时她又大吃一惊。她得不到任何保护;她被巨大的树木和大片的云朵所环绕,四周是一个冷漠的世界,她得不到任何保护;她受着折磨;但她为什么就该受苦呢?为什么?”
电影《时时刻刻》剧照
电影的最后,伍尔夫平静地走入水中,波光粼粼,一切如常。她选择死亡作为挣脱折磨的方式,而在庸碌的人间世中,依然有源源不断的“达洛维夫人”,如同站在即将断裂的树枝上的飞鸟。
伍尔夫受不了乡间宁静的生活,她要回到震撼的大都市去,在每天都充满光怪陆离的伦敦,伍尔夫坚持描绘现代人内心的惶惑无定,当身处巴黎的“迷惘一代”渲染着享乐与疲惫,伍尔夫已经开始大胆描绘人们心底的暗流,与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划清界限。
从1925年到1940年,伍尔夫相继写出了《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海浪》《岁月》《幕间》等杰作,她的写作迈向高峰期,她的精神却每况愈下。
3
“我要纵身向你扑去,我永不认输,也永不屈服,哦,死亡!”——《海浪》
电影《时时刻刻》剧照
伦纳德只能延缓她死亡的步伐。
1941年3月平静的一天,伍尔夫再次精神崩溃。在预感到自己这一次不会好转后,她给伦纳德和姐姐凡妮莎写下短信,独自投入冰冷的欧塞河。
《时时刻刻》中,一个情景令人印象深刻——烤蛋糕的家庭主妇坐在马桶上不住哭泣,丈夫敲门询问状况,家庭主妇捂着嘴,连说无事。而这时她已经动了自杀的念头。当生命的意义无可挽回地消退,自我逐渐成为负担,死亡成为她的选择。
伍尔夫的自杀源于对崩坏世界的恐惧。她的好友克莱夫·贝尔说:伍尔夫“面临着精神错乱的前景,清醒时也只能面对战争威胁下千疮百孔的世界,我不觉得她的选择不明智”。
在去世前,她留下了自己的遗作《幕间》,将诗歌、现实、喜剧、戏剧、叙述、心理学,都融为一体。伍尔夫把故事设在英格兰中部的村庄,讲述了一九三九年六月区区一天里发生的故事。她表面上在写乡村生活,实则是在书写二战时人们内心的恐惧。那些血污的网球鞋、监狱的铁窗、吞食青蛙的蛇还有报纸上士兵强奸妇女的新闻,无不指向战争的恐怖。《幕间》象征着两幕暴力戏剧之间的宁静,暗指英国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法西斯的狂攻,已经山呼欲来风满楼。
伍尔夫在《幕间》里也留下了死亡的隐示:小说中波因茨宅一个干粗活的女仆到清凉的睡莲池旁休息,伍尔夫看似闲笔地提及,十年前曾有一位贵妇在这处池塘投水溺亡。那是一片浓绿的水,其间有无数鱼儿“遨游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闪着亮光”。
在伍尔夫投水自尽后,布卢姆茨伯里派成员在河边发现了她的手杖和脚印,整个团体陷入深深的沮丧中。根据剑桥大学的档案,这个知识分子团体对伍尔夫的行为并不意外,但仍充满感伤的情绪,正处于世界大战的阴影,他们对未来失去希望。
伍尔夫死后,她所在的家园从一个光荣的国度,逐渐变为敦睦迟缓,英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仍在,但已无法返回黄金时代的辉煌。但伍尔夫那些源自内心的文字依旧不过时,她直刺人心的文字、永不妥协的主张,裹挟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浸染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作家因文字而不朽,她的能量在漫长时间中闪耀。
然而,伍尔夫被反复提及的过程,也是她的形象被固化的过程。那个尖刻、暴躁、带刺的伍尔夫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符合父权审美的知性、睿智、温柔的伍尔夫。就像《时时刻刻》里塑造的那个“敏感的,痛苦的女小说家形象”,它把伍尔夫满嘴脏话、言语恶毒的一面抹去了,它呈现的是男人会同情的痛苦,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伍尔夫。
所以作家多丽丝·莱欣说:“后人似乎不得不使弗吉尼亚变得温柔、可敬、平和、优雅,于是便看不到那粗鲁、苛刻、声音刺耳的部分,而这些也许是创作的源泉。弗吉尼亚最终以文质彬彬的女文人告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扮演伍尔夫的会是一个年轻漂亮时髦的姑娘,不苟言笑,永久的蹙眉显示,证明她有许多艰深的思想,正在深思。”
伍尔夫面的的困境,在今天依然存在,伍尔夫要挑战的世界,仍是我们所面对的铜墙铁壁。在一个和解成为正统话语的年代,追忆永不妥协有其意义,若和解只是对现实的粉饰,何妨大胆说不,追寻内心的主张。
我们不比世界重要,但世界也不比我重要,牢记《时时刻刻》所说的:“亲爱的雷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只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的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
作者简介:周郎顾曲,闲散青年。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