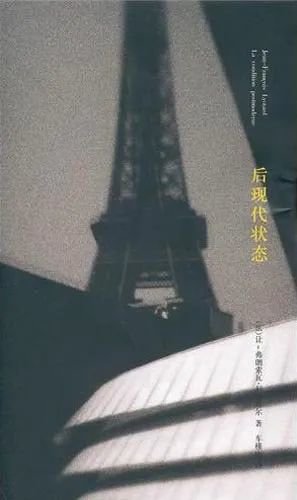韩炳哲的“社会病理”式分析,有何问题?|专访余明锋


独家抢先看
今年,“元宇宙”可能是技术和产业领域最热的词汇。不仅互联网巨头(如Meta)开始野心勃勃地围绕元宇宙进行商业布局,多所国内外的大学、科研机构也设立了相关专业和研究所。
不过,尽管各种对元宇宙的定义似乎言之凿凿,却似乎还没有人能够清晰地说出它到底是什么。在人们尚未厘清一种技术的基本轮廓时,却已经开始利用这种技术的隐喻来展开对未来的想象,这本身似乎就是最大的隐喻:我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技术之中,而技术,则界定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绝大多数的想象。
尽管技术已经如空气一般介入到我们每一刻的日常生活中,但绝大多数人对我们与它的关系都是习焉不察的。在新著《还原与无限》中,同济大学青年哲学学者余明锋认为,当下社会依旧存在一个对技术的误读,即技术依然主要是人类的工具,甚至在学者中,这种误读都难以破除。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慕尼黑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译有《敌基督者》《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等,发表论文多篇。
元宇宙只是我们身处的“技术时代”的一个缩影。而事实上,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将一切还原为数字计算的思维方式,成为社会运作的主要原则。从这一线索看去,不少哲学家都有相关的论述或研究。比如尼采就曾在100多年前预言我们今天的处境。福山,乃至近几年颇为畅销、流行的韩炳哲,也都对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展开过论证。
余明锋如何看待这些哲学家们的研究?他如何在这样一个脉络下书写他的“技术时代三部曲”?在最近的采访中,他与我们分享了技术哲学相关的最新思考,也谈及了韩炳哲式的社会病理学分析可能的危险之处。
采写丨刘亚光
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被余明锋认为是一个“技术时代”中的社会。《还原与无限》是余明锋写作的“技术时代”三部曲的开篇,区别于“技术工具论”式的误解,余明锋将一种“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的存在界定为19世纪之后现代世界全面展开的动力。在此,技术深深嵌入资本和政治的系统之中,裹挟着每一个人。技术甚至成为一种将一切还原为数字计算的思维方式,成为社会运作的主要原则。2020年《人物》杂志引发公众热议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可以看作是一个反映这个“资本-技术-政治”系统如何运作的最佳实例。
尼采曾在自己的《漫游者及其影子》中提出过一种“机器批判”,他指出,现代技术尽管在精巧程度上远超古人,但却可能在文化影响上带来人的“降低”,生产出更多的“末人”。尼采的预言可以说领先了时代一百多年。如果说尼采生活的19世纪西欧,电报、打字机、火车、照相机的发明带给人们的是拥抱新时代的欣喜,那么我们当下生存的时代中,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克隆仿生等诸多高新技术带给人类的除了进步的憧憬,更有挥之不去的人被技术系统吞没的焦虑。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反思以摆脱这种焦虑的哲学,当今也遭遇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被边缘化的危机。
在余明锋看来,这是技术时代的哲学必然遭遇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技术时代要求哲学对无处不在的技术进行反思。另一方面,“资本-技术-政治”系统主导下的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是无限的效率增长,已经与哲学的“沉思”背道而驰。学院派哲学家宏大的理论构建越来越远离现实,失去市场。人类生存境遇和整体知识样态的转变,也呼吁更多新的哲学形态的出现。
在哲学回应技术时代似显乏力的背景下,韩炳哲似乎成为一个“异类”。这名韩裔德国哲学家用短小精悍的“小册子”谈论现代人的抑郁、爱欲与互联网中的只言片语,用一个个精妙的隐喻做出先知式的判断:当今社会已经从福柯的“规训社会”转向“功绩社会”,从“他者剥削”转向“自我剥削”。一时间,韩炳哲似乎成为那个转型成功的哲学家,引领包括东亚社会在内的全球阅读热潮。
余明锋认为,韩炳哲这种从人们最切身的生活经验出发进行的“社会病理学”分析,确实迎合了技术时代人们对哲学的需求,也值得当今的哲学学者学习。但紧接着的问题便是:止于一种生活现象的诊断,是否就是当今时代哲学反思的极限?他认为,“韩炳哲热”面临的争议也在于此。如果不最终从现象回到与那些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对话,或许“社会病理学”分析也会失去其生命力。
《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作者: 余明锋,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 2022年8月
“技术时代”:
一种常被忽略的根本生存境遇
新京报:《还原与无限》的定位是一部哲学导论,不过相较于现在很多以哲学史或者以多个哲学基本问题为框架的哲学导论,你主要选取了“技术”作为一个基点展开内容。为什么你觉得技术是一个对于当下的人们接近哲学来说如此重要的话题?
余明锋:首先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导论”主要是针对于我自己的写作计划来说的,因为这本书是我的“技术时代”三部曲写作计划的第一本,后面还有《感知论:技术时代的认识论》和《拯救现象:技术时代的存在论》两本书,这本书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出问题,打开一种切近现实的哲思路径。当然,对于读者来说,它也有一种导论的意义,也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熟知而非真知的生存处境进行一种切己的反思。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导论”是对哲思的开启,而不是对历史上的哲学理论的普及性介绍。
至于技术问题,首先要说,《还原与无限》意在讨论一个以资本-科学-技术三位一体为本质的“技术时代”,而非单单讨论技术。其次,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视角,是因为它构成了我们当代人最基本的一种生存境遇,但是我们又对之习以为常了,仿佛世界就只能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的,而这就构成了哲学反思的恰当入手点。
新京报:近些年在中国兴起了一股阅读韩炳哲的热潮,他的理论也被大量地应用于分析文化、社会现象。有学者认为,他的写作经常是从现象出发去批判性地发展某个既有的理论,这里面可能就存在一些望文生义或是牵强附会的问题。你怎么看这种评价?我们常常说要让哲学“说人话”,但或许哲学问题与日常语言之间确实有难以通过“翻译”跨越的距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难题?
余明锋:我觉得大家对韩炳哲写作特点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他的确更多是从现象而非哲学史上的命题出发去进行思考。不得不说,我们当下的中国非常缺少这样的思想家,即便我们有很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能像他这样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提出有现实关怀的真问题的人太少了。这是我们需要向韩炳哲学习的。
要理解韩炳哲这样一种哲思方式,我们还得谈谈当下哲学的基本形态。粗略地说,尼采之后,哲学基本上放弃了体系建构。之所以如此,根本上是因为哲学的反思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个人类知识体系的语境中。今天的知识体系,和过去人类的知识体系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差异其实也和我谈的技术时代相关。那么差别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科学的目的,已经不再向着哲学所提的那些基本问题而去。科学更多以资本为驱动,以技术为导向,最终落实为技术的实现和资本的回报,以及社会效率的增加,而非朝向永恒问题的追问。可以说,现在排在科学考量第一位的不是“沉思”,而是“实践”,而且这个实践越来越具体、知识门类越来越细分。当下的知识形态让今天的哲学难以用旧有的方式建构黑格尔式的体系。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反思进路。
《黑镜》第三季剧照。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书中提到的对笛卡尔的再认识。过去我们会认为写作《第一哲学沉思录》的他主要强调“沉思”,而你会认为他其实有很强的“实践”面向。从古希腊时期的“技艺”传统,到你提的现代社会资本-技术-政治三位一体,其中存在一个技术理解的“古今之变”,这也深刻影响了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技术越来越脱离人本身的劳动,另一方面,技术由科学引导转而引导科学,可否谈谈这种技术地位的颠倒的根本转折点是什么?笛卡尔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吗?
余明锋:首先,技术时代我其实把它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上,整个现代世界都可谓技术时代,现代早期的知识规划为之奠定了思想基础。狭义来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资本-科学-技术结成三位一体的形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开始超越东方,将这套秩序扩张至全球。
其次,我谈笛卡尔,是为了挖掘技术时代的思想根基。有朋友可能会问,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真能决定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吗?我想社会现实的具体发生永远不是在哲学家的头脑中进行的,甚至哲学对社会的干预是微乎其微的,社会变化有非常具体的原因: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运作、具体技术的演变,等等。在这个层面,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不过,我们依旧不能忽视在一个长程的时段上思想发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笛卡尔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我们后来者不言自明的思考方式。比如用主客二分的方式看待自然、数理实验的自然观,尤其是一种将世界还原为数学计算的还原论。比如有关颜色的问题,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持有还原论的态度,从这种视角来看,颜色就是波长嘛。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看见的并不是波长,只是从科学的视角将之分析为波长,这当中是有区别的。
韩炳哲的“社会病理”式分析,
缺少语境比较
新京报:既然技术时代的哲学已经不同于过往,那么今天的哲学有什么比较理想的展开方式?
余明锋:我认为,尼采之后的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是“社会病理学”。相较于过去的体系性哲学,这种哲学往往针对着那些与我们的日常经验高度相关的问题,比如尼采的“末人”诊断、海德格尔讲的“常人”、福柯谈的规训,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我个人觉得,韩炳哲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病理学家”。如今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他都有一个相当大的阅读市场,这是有原因的。他的作品通常不会跟你绕思想上的圈子,而是直接谈你的生活出了哪些问题:现代人的疲倦、倦怠社会及背后的原因、现代人为何丧失爱欲,这些都非常打动人。
近年出版的韩炳哲作品。
新京报:的确,韩炳哲善于使用隐喻来表述哲学论点,同时也习惯提出新的概念。不少学者都指出了他的一些新的说法本身合理性存疑,比如你说,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这个转变是否存在是存疑的,可否展开谈谈?
余明锋:总体上来看,韩炳哲的诊断虽然有很准的一方面。他基本上以我们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原型,尤其是西欧社会,所以对于我们国家一线城市的读者来说,是会觉得很有共鸣的。不过这里面的问题是,他可能夸大了一些“新现象”的影响,对于这个社会依然存在的一些19世纪以来的问题谈得比较少,重视不够。比如,我们现在有没有出现一种走向“功绩社会”的迹象?当然有,但如果说我们已经全面从规训社会进入功绩社会,这个诊断就有些夸大其词了,我们显然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规训的普遍存在。
其次我特别想谈的就是,我们不能停留于韩炳哲,这个是什么意思?现在可能很多哲学学者都面临一个“困境”——包括我在内。我们一方面希望让哲学变得更有活力,更加直面现实,甚至部分地走向公众;另一方面,我们要当心哲学的鸡汤化。大家的精神困惑所关系到的当然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我认为哲学学者还是需要守住一份清醒:哲学终究是不能完全化约为社会病理学的。社会病理学是当代哲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哲学能提出真正有现实关怀的问题,但哲学不能仅仅在各式社会病理中打转。
我认为,这也是韩炳哲的一个缺陷。就是说,他的社会病理学诊断很有洞察,可他在深入思想史传统、重提哲学的永恒问题方面做得并不够。这可能部分和他的这种小册子写作的风格相关。同样,我认为略有讽刺的是,他的这种写作本身就很符合他所诊断的社会病理:在一个加速时代,每个人的时间都所剩无几,大家对韩炳哲的小册子趋之若鹜,但对那些更重要的大部头是提不起兴趣的。我想,这样的小册子可以继续写下去,应该也会一直对大众读者有所启发,因为它始终和大众的感知同频。但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重提哲学问题,对人类的永恒之问作深入探究,那就简化了哲学。
《精英的傲慢》,作者: [美]迈克尔·桑德尔,译者: 曾纪茂,版本: 漫游者|中信出版社 2021年9月(点击可阅读桑德尔专访《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
新京报:在提到韩炳哲的绩效社会批判时,你指出他的批判遮蔽了绩效在历史语境中曾经具有的正当性维度,即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福利分配的正义原则存在的。这让我想起最近受到关注的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其中也讨论了所谓“优绩主义”的问题。但正如你在书里所讲,如果机会均等没有保障,那么绩效并不可能是正义的。人们对桑德尔对优绩主义的批评同样类似:真正的问题并非优绩本身,而是机会不平等。你怎么看优绩主义的问题?当下对其的批评存在这种错位吗?
余明锋:有关绩效的问题,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相关。我们不妨举例来谈。比如,大学教师,每年都遇到学院绩效考核的问题,总有老师可能因为考核不合格被降档甚至解聘。这搞得人心惶惶,扭曲了很多东西。但我们能取消考评吗?如果取消这种考评,那又会怎样呢?我们的各种评审会出现没有客观标准的问题,恐怕既没有效率,也不会变得更加公正。
其实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学科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就开始系统讨论所谓绩效社会的问题。绩效这种根据才能、功绩来分配的原则总体上是比较符合一种分配正义的,它也为无可避免的不平等现象做了合理化论证。当然,也正因为绩效成为二战后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韩炳哲的批判才会如此打动人。
但真正值得去反思的可能并非单纯绩效本身,而是绩效的基本前提。首先是机会的均等,机会不均等的前提下聊绩效就有点耍流氓。比如,高考按分数来,但因为学区不一样,孩子受的教育水平天差地别,那么表面上的公平就恰恰掩盖了不公平。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退出机制的保障,因为绩效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优胜劣汰,这时候就得保障一个所谓的“被淘汰者”,让他有最基本的福利,让他能够重新开始。即便对这个绩效社会本身来说,如此也才可能长久。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是非常现实且重要的问题。
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韩炳哲的绩效社会批判非常明显的是以西欧社会为蓝本的,所谓机会均等和退出机制的问题,其实恰恰这些社会确实已经做得比较好,这时候再去谈绩效社会批判,就格外恰当。当然,中国当下这么多人对绩效社会批判产生共鸣,说明我们也部分进入了这种问题的语境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语境的比较里去理解韩炳哲。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 》剧照。
“精英”式的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新京报:在书中讨论尼采的章节,你也提到了尼采的机器批判很大程度上预警了我们这个年代的很多现实,比如智能手机的进步不仅没有让人变得更自由和聪慧,反倒让人“堕落”。不过,这样一种技术批判的论调常常难以回避一种质疑:这是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如果每个人其实都能比较清醒地认清技术的问题,只是自主选择“陷于技术”,那么他们是否只是“我们以为”的不自由?
余明锋:这其实是一个所谓现代社会的自由承诺问题。现代社会给予了我们每个人一种自由的愿景,但它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各种各样的系统让人陷入更大的不自由。这个诊断我觉得基本上是准确的。至于说这种批判有没有精英主义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区分所谓的“伪精英”和真正的精英主义。伪精英大概只是一种身份标榜,而真正的精英主义代表了我们所追求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不能说我们有批判的姿态,就完全否定所有的精英主义追求。如果我们的生活陷入了一种被奴役而不自知的状态,那我们不是应该有一种切实的反思吗?如果说这是精英主义,那就是一种必要的精英主义。
不过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如果要细谈这种“自由承诺的落空”,仅有哲学肯定是不够的,哲学只能提供一个反思性的目光。真正完整的社会病理学诊断,一定缺少不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比如,如果要探讨所谓加速社会的问题,那么一个年轻人一天具体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这是需要更多社会实证分析的。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人,从第一代的阿多诺,到后来的哈贝马斯,同时就是兼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加速社会批判的哈特穆特·罗萨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四代传人,他的研究同时也是社会学的。
余明锋翻译的尼采及相关研究著作。
新京报:你提到尼采对超人和“末人”的划分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看待“痛苦”态度的差别。这其实和韩炳哲讲的“透明社会”批判也有类似之处。现代社会不论从技术发展还是在制度安排上,都致力于消灭痛苦和“断点”,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毫无阻力:智能手机的屏幕制作的让我们能快速滑动,我们点一下外卖平台就希望能立即送达......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痛苦的意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吃苦是福”这种论调的翻版。
余明锋:首先,这是尼采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的一个最为着重的批判点。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后,一直在致力于减少痛苦——虽然事实上未必减少了痛苦,它可能带来了更多更大的精神痛苦——但至少我们的价值观始终都是以减少痛苦为指向的。这时候我们强调,要理解痛苦的价值,初听上去可能确实会有种“感谢苦难”的毒鸡汤味道。但这是一种误解,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我绝不是说要无差别地肯定所有的痛苦,不是没事做给自己“找虐”;而是首先要反对用“人生就是痛苦减少,快乐增加”的这样一种还原主义苦乐观去思考人生。经济学里有所谓“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它的哲学基础其实是英国的功利主义,强调苦乐计算。但问题在于,它将人生完全化约为简单的苦乐计算了,这无疑是对人生现象的过度简化。况且所谓人生的苦乐,本身也很难算得清楚。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谈论本身基于一种知性的抽象。
此外,我想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追求一定包含着自我超越和克己的维度。比如我要写一本书,那就必定要忍受和克服很多痛苦,要放弃很多东西。我们要肯定的是这样一种痛苦。这种包含着自我超越之苦的生命理解,内在包含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性”。韩炳哲所谓当代社会对“肯定性”的过度强调,其实也可以从黑格尔出发来理解,虽然他没有怎么提黑格尔。黑格尔是最强调“否定性”的思想家。当我们不是着眼于生命意义的追求,去肯定自我超越所内在包含的痛苦,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对生命中的一切否定性进行消除,而这恐怕是对生命本身的巨大误解。
人类的世界不只是智能的世界,
还有精神的世界
新京报:利奥塔尔在《后现代状态》中把当下时代的技术问题归结为一个“算法”的问题,它不穷究生命的本质,而恰恰要绕过本质问题,把一切还原为数学。近期多家媒体都报道了AI作画小程序风靡的现象,这里的问题是,AI作画与人类作画有别,前者是还原论式的创作,后者才是真正的艺术,这是否其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技术足够发达,是否二者的距离可以弥补,“二者有别”只是一种人类的执念?
余明锋: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几年会持续反问自己的问题。一种有趣的观点认为,人类应该愉快地接受AI取代人类的事实,觉得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变相进化,人类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尤其是一些“超人类主义者”,会把尼采的超人学说和现代技术进步主义联系到一起,论证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但我们尤其需要纠正的是,尼采其实恰恰不这么看。各种人类机能增强技术,包括基因改造,表面上看是在超越人自身,在趋向超人,但其实它只不过是信奉着尼采所说的一种“末人”的价值。这个我在书中有详细辨析。“超人类主义”超越的并非“人本主义”,而仅仅是用技术手段,替代了传统人本主义实现其目标的文化手段。
《后现代状态》,作者: (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译者: 车槿山,版本:守望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AI作画最近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但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语法和思维上的误解:AI并没有在“作”画。它只是在计算,它的运作逻辑是“绕过事情的本质”,把事情的本质当作黑箱来处理。AI不需要理解艺术,只需要通过计算去符合人类对艺术的某种模式化理解就可以了。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人类也抛弃了对事情本质的理解,或者放弃了这种追求,而反过来用AI 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自己,我们就会越来越觉得我们只是有肉身的计算机,以及,其实我们对于爱、美、艺术的理解,也不过是可以全然还原为智能计算的。
这会是非常危险的误解。人类的世界不只是一个智能的世界,而是一个包含智能在内的精神的世界。它与AI的世界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果说AI也有一个世界的话。我在想,人类未来最大隐患之一,就是从单纯的苦乐计算和单纯的智能运作来理解自己,把机器作为模板理解自己,于是人就被看作不够完美的肉身机器了。
《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一季剧照。
新京报:你写作“技术时代三部曲”,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试图提出一种“非还原论”的世界观,在你对“还原论”的批评之上,可否谈谈这种观念何以可能?
余明锋:简而言之,非还原论的构想是从“感知”入手重新唤起我们对于最基本的世界现象的好奇,它针对的也是我刚刚提到的两点隐患:人类不断地用苦乐计算和纯粹智能的思维来看待自身。这一点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媒体上的“元宇宙”热中也有体现,人类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构想,居然是将我们可以感知到的世界完全用0-1的代码去模拟。这当中的简化不可不察。在人类基本的感知里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概念化和隐喻化的构造,这种构造并且有历史性和文化性,本身是有流动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可塑性的,它不能单纯地被数字化。以我前面举的颜色为例,颜色可以被化约为波长,但对波长作怎样的切割和命名,就和我们的语言与文化的选择有关系。
比如在爱斯基摩人那里,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关注我们所关注的大多数颜色,但会特别关注各种不同的“白”,据说他们的语言里就有关于“白”的十几种词汇。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有着对于“白”的极为丰富的感知,相应地就发展出与之相关的丰富词汇。我们的感知中是有概念和隐喻的。这个隐喻的部分,实际上被传统的哲学大大忽略了,这是我在《感知论》要着重谈的问题。总之,当世界被简化为一个可计算的机械体系时,人也就生活在一个机械性系统之中,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感受不到什么人性的温度。只有当我们通过感知打开丰富的世界层次之后,我们才能重新恢复世界的温度,使得世界对于人性是有庇护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走走;校对:刘军。封面图片为《黑镜》第三季剧照。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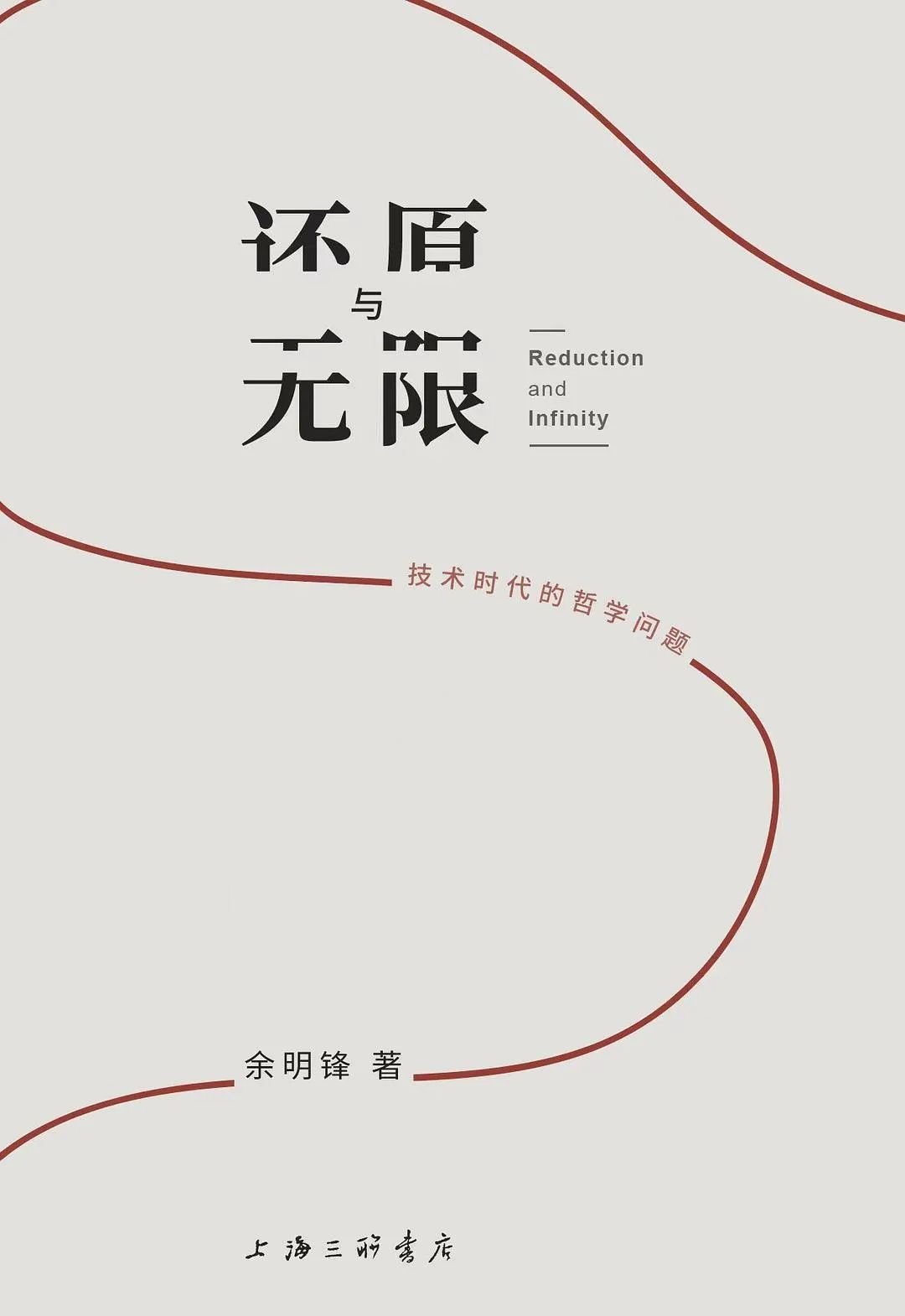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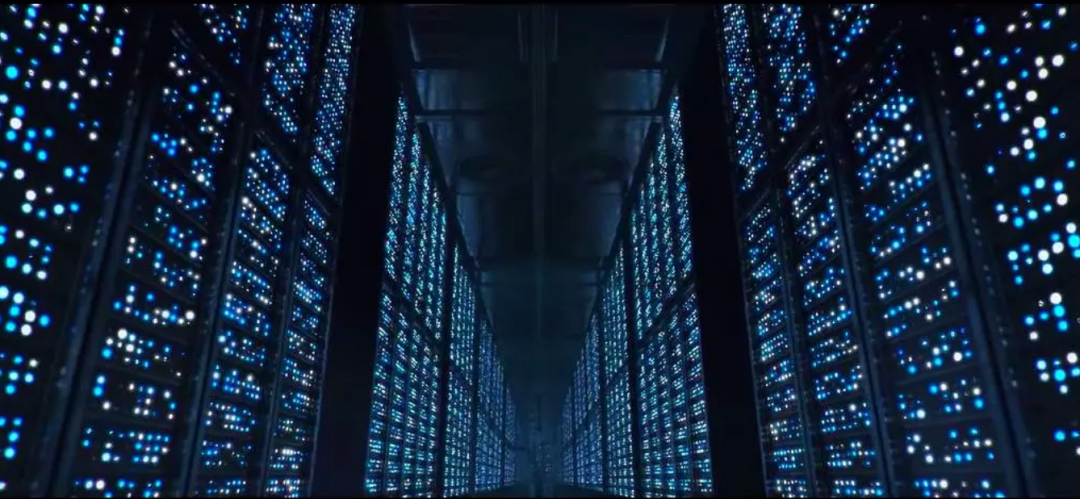

![《精英的傲慢》,作者: [美]迈克尔·桑德尔,译者: 曾纪茂,版本: 漫游者|中信出版社 2021年9月(点击可阅读桑德尔专访《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https://x0.ifengimg.com/res/2022/5F0CC5943647272AAF6027EDA88066D90215052A_size134_w1080_h158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