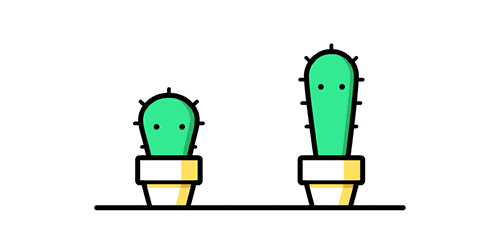从这一天开始,数着指头候着过年
“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对中国人来说,年隆重又漫长,似乎从刚刚进入冬天开始,人们就着手为过年做着各种准备。制作美食、除旧、添新,处处彰显着人们对这一节日的重视。尽管当下年味儿日渐冷淡,但“过年”依然承载着我们诸多寄望与愿景。
作家邹汉明出生的塔鱼浜,是位于浙江桐乡西北的一个小村庄,它因拆迁而变成一片废墟,自此,与年味儿和童年相关的一切都成为他往后余生的旧时光。邹汉明用文字还原将近半个世纪前,江南小村庄的冬日生活图景,这些生动的“备年”画面,不断勾起我们对于正在消逝的年味鲜活的记忆。在他笔下,冬至的糯米团子、腊月的赤豆糯米饭以及年前除尘和剃头的活动,都被注入了延绵的生命力。
本文摘自《塔鱼浜自然史》一书,经出版社授权转发。
腊月廿三
蒸糯米饭、送灶神
十二月廿三一到,农历年关的序幕就慢慢地拉开了。孩子们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数着小指头,一天屈一指,候着过年的。年节的气氛,也一点一点地浓郁起来。这些,从塔鱼浜那一条条蓝色的炊烟上,从一只只跑过门前的小狗摇晃的尾巴梢头,都可以觉出来。
廿三烧糯米饭,是塔鱼浜约定俗成的规矩。村里的水田,糯米并不多种,但每年总要种一小爿田。除了一些大节日做糯米馍馍、裹粽子、打年糕之外,糯米的用处,就是廿三这一天的晚上,一定要烧一铁镬子的糯米饭。
糯米饭平日是不会烧的,因为糯米别有味道,容易吃撑肚子,不易消化。再者,糯米也毕竟不多吧。但糯米比粳米还是要来得便宜。糯米看上比粳米瓷实、光滑,米粒大一点,看起来比平常吃的晚稻米虚胖一点。一般的人家,都用一个小米囤囤积着那么一点点。
廿三的糯米饭,一定要加入一大碗赤豆。紫红的赤豆,铁一般坚硬,清水里浸一下,再与糯米一起倒入铁镬子同烧,这样做出的赤豆糯米饭,镬盖一掀,立时焕发出一股沉实的暗紫色。热气腾腾中,涨开的赤豆依旧粒粒可数,而原本瓷白的糯米,这会儿全染成了赤豆的颜色。赤豆与糯米,融合成一体了。
赤豆糯米饭
第一碗糯米饭,一定要盛给灶家菩萨吃。这是我母亲的任务。灶山上,积累了一年的长脚灰尘,早已掸去,且已点燃了两枝红蜡烛。这头一碗香喷喷好颜色的糯米饭,就在她双手恭敬的递送下,摆上了高高的灶山。
廿三日是灶家菩萨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的日子。中国的老百姓,素喜临时抱佛脚,你看平时的灶间,总黑漆古脑,邋里邋遢的,这一日却马虎不得,因为菩萨就要起程了,他老人家这一去,关系到整整一年的运道,谁都需要仰仗他的美言,一年四季才会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啊。这可是怠慢不得的大事体。主妇们殷勤致意,实在也是在塞菩萨的嘴。这灶君王,一定是一个和气宽容的大菩萨,也乐意成全人世的美意,否则,以他菩萨的大觉悟,岂不明白升斗小民的伎俩。
廿三祀灶君,算得例俗。
推前一段时间,我家乡廿三这一日,考究的人家,会制作一种叫做廿三棚的东西。方法是:去竹林里断一根不大不小的青竹来,截去竹梢,在截去的这头劈开同等大小的三根竹片,当然这根竹片,万万不能与青竹断开,扳开劈开的一头,小心地嵌一只蓝花碗上去,扎紧。蓝花的供碗里盛满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并覆以冬青、柏子等装饰物。孩子们是很喜欢举着这只廿三棚到处走走的——这一定是一种别家没有的小小荣耀吧。
电影《饮食男女》
20世纪70年代,江南的风俗已经大不如往昔。我所亲历的农历廿三祀灶君,已经简化到只点两根蜡烛,再盛上满满一碗糯米饭,摆上灶山,仪式也就宣告结束了——这实在有些草率了吧。
灶家菩萨用过饭,接着,就轮到孩子们享用了。我们的好胃口,已经像两扇大门一样,打开许久了。
暗紫色的赤豆糯米饭上撒一调羹的棉白糖,一边吃,一边看着雪白的糖悠悠闲闲地融化到米饭里,一股世俗生活的甜味顷刻间游走在孩子们正在发育的身体里。这个,差不多就是年节的味道了吧。
腊月廿四
二十四,扫尘日
过年之前,前前后后的屋子里总要打扫一番。
这一天母亲是主角。事体她吩咐,我和弟弟完成打扫任务。屋里的梁条上倒挂下来的长脚灰尘,竹竿绑上一把笤帚,可以轻松掸掉。因屋漏而地上出现的水洼,去稻地外挖一块泥巴来填平。有意思的是,新泥是黄褐色,与屋里的黑泥颜色不般配。于是,像一件衣服的补丁似的,修补的痕迹竟然是这样的明显。这水坑新补的泥巴,风干以后,通常仍会与老泥脱离,脚底一拖,或笤帚一扫,松松垮垮的,全是泥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廊柱上,多余的洋钉要拔去。这些洋钉,都是我父亲钉上去的,原本可以很方便地挂他的蓑衣、箬帽、担绳……但实在太多了,把一个好端端的廊柱,钉得像岳飞传里金兀朮的狼牙棒。
门角落须得整理一下,锄头、铁耙要挂墙壁上,套鞋、掘子、土挞,要分开放,梯子要回到原来的所在。
最难处理的是一双钉鞋,扔又不是,留又不是。还是留着吧。这是盲太太传下来的“传家宝”吧。没见父亲穿过,灰头土脸的,积满了尘土。要是在现在,可以入收博物馆了。
年节边
小队分红、备办年货
做了一年的活,记了一年的工分,农历十二月廿几了,小队该分红了。
小队长毛老虎提起铜锣的拎头绳,拿了敲锣的棒槌,站到木桥堍,一个转身,面北背南,眼光正好罩临整个塔鱼浜。他手里的铜锣终于在这一年的尽头,咣咣咣咣,敲出了最欢快的乐章。不用分说,今天是分红的日脚。各户的当家人都到齐了,汇聚到毛发林家的厢屋,全体围着一只油光光的八仙桌,分红点数钞票。我父亲,这一年,分到人民币七十六块,其中多数是角票。他一张一张地数着。每数几张,手指肚抹一滴唾沫,继续数,继续眉开眼笑,笑到口水都流下蛛丝似的一长条来。分到了铜钿,无论多少,可以备办过年的年货了。塔鱼浜的每个当家人都很高兴。主妇们,男孩女孩们,同样高高兴兴。高兴极了。
电影《过年》
晚上,敲门的声音好听地响起。高稻地的牛屄新山来了。一忽儿,大块头炳奎也来了。原来都是还钱来了。我父亲是老好人,只要说几句好话,就乐意借钱给非亲非故的人家。他不像我婶婶美娥,除了几个至亲,铜钿银子一律不外借,抠门得很紧。
有一年,不,不只一年,小队会计、我的大叔拆烂污阿二的算盘珠噼噼啪啪一推算,我们家成了倒挂户,倒欠公家二十六元。父亲垂头丧气,只是一口一口一个劲儿地抽他的雄狮牌香烟,他一句话都没说。他这一生,心里原本就没有这一粒算盘珠。这个亏他吃大了。
拜利市、画六神牌
每年拜利市(江南市肆中向有“利市”之称。所谓拜利市,是我家乡年脚边敬神的一种祭神仪式)供奉的六神牌,连同供六神牌位所用的那个木架子,是我得着父亲或母亲的吩咐,急匆匆跑去半里许的外婆家借来的。我这一番来去,额头汗出津津,胸口怦怦直跳,厢屋里立定了,还要吐一口大气,可见得我这一回的奔跑是用尽了全力。因为终于做成了一桩神圣的事体,看着厢屋即将开始的拜利市仪式,满心里都是欢喜。
五颜六色的六神牌,塔鱼浜实在也没几家有吧。好像翔厚镇上也不见得有店铺卖这个四旧。对了,那时要破除迷信,板刷刷出的红赤赤的标语,墙面上正写着呢。但破除迷信是翔厚大队的正经事体,三里路外的塔鱼浜根本就没把它当一回事。我们祭我们的祖宗,拜一年一次、多一次也不拜的利市,顶多把大门关紧一些,不让你看见,就算我们的迷信早就破除了——也就可以了吧。对,这就是塔鱼浜思维。
有一年,村里有人悄悄地在传说:东边的阿二也在他那座新造的屋子里拜利市呢。阿二家供奉的那副六神牌,才好看啊。阿二就是大队支部书记邹根富,他的举动一向有榜样的作用。那一年,我在翔厚小学已经学唱到“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的革命歌曲。“榜样”这个褒义词,我熟悉,也会用了。
农历年底了,寒冷的天气让整个塔鱼浜村的大门都关得紧邦邦的,泥路上泛着阵阵灰白色,也不知是尘土还是冰霜,还是天上的哪一颗星夜里碎裂在了地面上。总之,除了那一分灰白,路上什么都见不到。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天一黑,屋外面少有人在。那几个晚上,只要满村坊跑跑,透过大门的缝隙,都能够看到八仙桌上两簇摇曳的火苗——那是一家子正在拜利市的标志。跑到高稻地上,果然,我看到了根富家也在热火朝天地祭拜呢。这一下,我们大家都放宽心思了。连我家贴隔壁的四类分子严子松,也不再像原先那样小心谨慎。
电影《过年》
当年底拜利市的仪式越来越公开化的时候,这庄敬的仪式上必要用到的六神牌,就越来越难于借到。因为大家都需要啊。好多人家,就等着隔壁邻居家仪式完成,赶紧借来一用。终于,我弟弟汉良眨巴眨巴着布满红丝的大眼睛,充满期待地对我说:“阿哥,我们画一副六神牌吧!”
于是,我们借了一副模本,用养蚕时剩下的白纸,尺寸裁得与模本一样大小,先用图画铅笔,勾画出六神的轮廓。那六神,从右至左,依次是:观音、门神、圣帝;寿星、土地、灶司、蚕花天子、马鸣王;五路财神、地母、田公;蚕花五圣、顺风大吉;文昌(赵元台)、招财、利市;家堂(路头五圣):关帝、太君娘娘。一个个像模像样起来,鲜活起来,等到我们用图画课上的蜡笔一上色,简直与借来的模本一模一样,父亲见了,难得地夸了一句:“两只小棺材,倒画得蛮像的。”
其实这一副六神牌,大多是我弟弟画的,我沾了他的光。后来的好几年里,我们各自上大学,寒假回到塔鱼浜,每次拜利市,供奉在架子上的六神,我仔细一看,仍是我和弟弟同画的那副蜡笔画。
烧年猪头
年节边,江南农村的风俗,过年必备一个大猪头。
猪是自家所养,算定到年节边,正好养大,这猪就叫做年猪。年猪的头是不外卖的,自家备着,年廿八或廿九拜利市用。
猪头煺毛后中间半劈开,呈一柄蒲扇状,腌在一只大陶钵里。腌法:用石块压实。等血水流出,滗干,如是者再而三。腌一些时日,取出,挂廊檐下晒,直晒得肉质紫红,滴沥出油水,摸上去硬邦邦,逸出一股清香,这才收好。
烧猪头一般用花篮灶最大的那眼灶。用硬柴烧,火势持久,猛烈。小半天工夫,镬子里飘出猪肉的香味,与猪头放在一起同煮的,还有蹄髈。灶肚里,可以煨番薯。年底的这些天,整个塔鱼浜就飘散着这股勾人食欲的肉香和番薯香。
烧年猪头是很开心的事。开心不仅仅是可以煨番薯。那些天,天寒地冻的,坐在灶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置身在暖洋洋的空调间,适意非常。猪头烧熟,又经硬柴火一焖,肉质糜酥到无须刀切,只须一双筷即可以打开巨大无比的猪头。不过,且慢,烧熟的猪头还要派一个用场,在祭祀的仪式完成后方可以拆骨食用。
年三十前两三天的晚上,塔鱼浜家家户户开始拜利市。天色向晚,父亲取出上年收折好的六神牌,置于八仙桌北端朝南的方位,东西两边各摆上小酒盅并配有筷子,南端朝北的方位燃起两根大红蜡烛。八仙桌上,除了鸡鸭鱼肉,赫然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年猪头。猪头肉上插一把刀,特别醒目。看这个样子,大概是请神仙们自己动手歆享吧。
利市拜好,碗筷收进,父亲就在八仙桌上动手拆猪头。我和汉良围坐两旁,嗅着猪头肉的香味,吸着口水,一边分享着父亲不时扔过来的猪头肉屑和一块块还粘着精肉的骨头,有说有笑,连呼好吃好吃好吃。
电影《过年》
咸猪头的两只耳朵肉嚼着喇噗喇噗的,用牙齿一咬,自己的耳朵也会哔剥哔剥响。女孩喜欢吃猪耳,男孩嫌肉味不过瘾。不过,猪耳朵是酒醉徒最喜欢的下酒物,父亲不会给我们多吃,只尝鲜,杀一下我们嘴巴里的馋虫也就此打住。猪头上最好吃的是猪翘,也就是猪鼻,吴语谓鼻冲,猪翘肉香中带有韧劲,味道特别好。猪翘一片一片切得薄薄,拆肉的时候,我们能吃到几片,也不过过过瘾而已。其次,大概是猪舌头了,至今仍是酒醉徒吃酒下饭的妙物。
猪头的骨头大而且多。我记得,拆出的骨头上的肉被我们小心剔出后,骨头就此收好,放门角落。过了年,读者一定知道了,我们会跟一个绰号叫“喊天鬼”的小货商换芝麻糖吃。
那时候,过年的年猪头,市场上实在难以买到,因为一般的养猪人家,肉猪脱手,猪头就自家备着过年。只有养两只猪的人家,才有可能卖出一个猪头。有几年,我们家不养猪,过年时就买不到一个香喷喷的年猪头。没有了年猪头的年,那还像过年吗?总觉得缺少了一点年味。有时,看到村上有养两三只年猪的,父亲早早地就去打招呼了,要求他们留一个年猪头卖给我家。但这样也不能保证,轮到对方的亲戚也要年猪头,我们家又要轮空。我记得有一年父亲买了一个咸猪头,是商家腌好的,到了拜利市的当晚,一拆肉,尽管有肉香,肉质却偏咸,全没有自家腌制的那种纯正的年猪头味道。
腊月廿九
剃头打三光,不长蚤子不长疮
彭家村小桥头的剃头师傅金介里,年前,无论如何要来一次塔鱼浜,整个村坊的男人,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也都在等着他来收拾端正呢。
我是看着金介里由一副剃头担子换成一只小箱子的。金介里也由脸色红润、步子轻快、手脚利索渐渐地走到了面白蜡生、一阵西北风来就能把他吹倒的那个样子。
他从我家东边的戤壁路口蹭出一个头,提着他的小皮箱走来了。孩子们早早地将一只阔长的条凳搬到稻地上。江北灶上的水,也开始烧滚,直到铁镬子的缝隙里直挺挺地喷出一条紧邦邦的水蒸汽来。
小皮箱里,金介里先取出鐾剃刀的帆布带,随手挂在门框边上的洋钉上。接着,箱子里取出折叠得甚是方正的一块剃头布,噼啪一抖,双手一甩,宽宽大大地就围住了一个人的胸口,上端的两条布带利索地围脖子打个结。一边打,一边还不忘轻轻地拍一拍他的后脑勺,好像跟被剃头人有了一份誓约似的。随后,他不紧不慢地取来轧剪、木梳、剃刀、黄颜色的透明肥皂、掸头发的刷子,一把与我们家里全然不一样的小剪刀……一切按部就班。他娴熟的剃头手艺就在塔鱼浜人的眼皮底下施展开来。
崭崭齐齐收拾干净,簇簇新新过大年。理发,终究是头等的大事,要是头不剃,想含含糊糊混过年关,那不成的。全村人的眼睛雪亮雪亮。那就要被套上一个讥讽,叫做“毛猪头过年”。总之,要被大家笑话的。
电影《过年》
金介里最擅长剃西装头。所谓西装头,头发三七分梳,显得洋派。全村唯独我盲太太,每次金介里来,都要让他刮一个大光头。看到头发一簇簇落地,一个圆滚滚、肉鼓鼓的和尚脑袋就出来了。每到这个时刻,孩子们总觉得盲太太就是电影里的那个大坏蛋。盲太太为什么要剃光头呢,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那么他该不是要省五分剃头钱吧。金介里的剃头价格,光头比西装头便宜五分。再者,光头的剃头间隔总比西装头时间上也要来得长一些。这样,盲太太就可以省下不止五分钱了。至于光头,那个年代,除了牢监里刚外放的之外,我看整个塔鱼浜也就他一个吧。
新剃头,照例要打三下,一边打,一边还念念有词:剃头打三光,不长蚤子不长疮。孩子们快快活活地追打新剃的头,连盲太太的头也打。他人高马大的,实很难打到他的大光头。但我们跳起来,打了他就跑,总之,仍旧打不到三下,且稍不留神,反被他捉到,反打。有吵闹激烈的,欺盲太太眼瞎,搬来一只拔秧的凳子,悄悄儿踅到他背后,站凳子上打他的后脑勺,如此得手了一回,高兴得像得了旺财,赶紧跳下来,早跑得没了踪影。
盲太太像个陀螺似的,转南转北,转东转西,手忙脚乱,嘴里是呵呵呵呵的笑。
金介里如果十二月廿九不来,年三十上午他一定来。要是年三十上午再不来,那一定发生什么意外了。我离开塔鱼浜前的两三年里,眼看着年三十已到,那一天终于没有等着他来剃头。整个塔鱼浜都在埋怨他。
“格卖屄(塔鱼浜土白。此语,实无淫荡的意味。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思。有时甚至表示说话者与被说者之间有很亲切的意味,不直呼其名,多半呼一声“格卖屄”替代,也算得上江南乡村民风粗野的一个方面吧),到十八亩田横头了,也不见他来!”
“格金介里,不要来了,来了,大家都不叫他剃。”
“金介里啊,听说,乌镇看病去了……”
“怪不得老早看见他,面白蜡生的(吴方言,脸色惨白的意思)……”
小桥头的某间平屋里,金介里的耳朵根子,想来一阵热一阵冷的。
年节一过,消息传到,金介里故世了。
年月三十
烧年夜饭、领压岁钱
年三十的上午反倒是安静,因为该备办的年货,已经办好。一埭老屋,前前后后打扫干净。连七石缸里的水,也早早地担满。花纸糊上东西两堵墙。花纸是京剧《李慧娘》《穆桂英挂帅》以及祖国大好河山的十六副组照,后者每幅配以七个字的标题。我记得其中一句是“镜泊湖上运牧忙”。每家的厢屋,朝南的位置最尊。这朝南的墙上,贴的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两幅画像。花纸的墨香我一路闻了又闻,鼻孔里吸满了墨香味。真的,每一个乡下孩子,花纸买到手,卷成长长的纸筒,忍不住就把鼻子凑上去吸,一则模仿戏剧舞台上丑角的那个长鼻子,二则,乘机闻一闻它的墨香。那两张领袖的肖像,塔鱼浜每户人家,不约而同都请到了,且都张贴在了朝南的墙上。
细看两位领袖的领子和领口,纹理清晰,可以觉出画师一丝不苟的心思。两件同样的微露的衬衫领口,有着同样一道雪雪白、崭崭齐齐的纹线,紧贴并稍微突出于外面中山装的领口。而两位衣服上的纽扣,一位稍显模糊,一位则极其清晰,纽扣的四个穿针线的小孔也画得特别清晰。那些年,两张红光满面的面孔,一直占据大半堵朝南的墙壁。或许离得太近,其实很长时间,小屁孩们是不敢抬头细看的。
母亲塞给我一个铜勺,要我想办法擦干净。黄澄澄的铜勺经过一年的使用,积满了灶间的灰尘,变得乌漆墨黑。只有铜勺的反面,舀饭米水时与铁镬子轻轻一擦的那个巴掌大的地方,还是簇新的。就这一小块黄澄澄的铜,崭新到晃眼,其他地方,其实都暗沉沉的。想要把整个铜勺擦得亮晃晃、黄灿灿,可也真不容易的。为了完成大年三十母亲交待的任务,我特意去外墙角落捡来几块瓦片,水里一浸,对着铜勺唰唰唰唰连着擦了小半天。我用这个笨拙的办法,把一个黑乎乎的铜勺重新回到它黄澄澄、光灿灿的黄金时代。当铜勺再一次摆上灶头时,连一向很少表扬的父亲,拿下一天到晚嘴里含着的香烟屁股,难得地张嘴赞了我一句。
我父亲和母亲的生活算不得和谐,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太大。父亲软弱,母亲却强悍。父亲是塔鱼浜最本分最老实的一类人,母亲虽然出生在塔鱼浜,却从小跟着石门开糕饼店的祖父母生活。她是作为六二六三的知青下放到塔鱼浜的,阴差阳错,两个人结合了。但是,两个人始终说不到一块儿。于是,一年四季,他们吵架不断。而每次吵架,总是母亲占上风。吵架的原因,说到底,其实都是因为穷。父亲早上去翔厚吃早茶,顺便买菜割肉,提篮里带进家门来的,常常是一条项圈肉。项圈肉便宜,可是,猪的身上,就这个部位的肉,最不好吃,看着肉乎乎,一段骨头都没有,烧熟了,汤汁起一层膏,看着油亮光光,吃到嘴里,实在没觉得有什么好吃。父亲一买再买,母亲也就一吵再吵。
电影《过年》
年三十的上午,母亲骂父亲,多半是因为父亲贪这小便宜,买来的年货不称母亲的心意。母亲在厨房里,喉咙直响,父亲在外头,气呼呼地说一句,也就没了言语。有时候,两个人就像两个超级大国一样冷战,所不同的,母亲翻白眼,父亲却笑嘻嘻,并不当一回事体。至于那顿年夜饭,两个人仍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母亲做菜,父亲找来祭祖的盅子与筷子,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年节的时间一到,两个人居然合拍了。
年三十的中饭一直比较简单,匆匆忙忙吃一碗饭,就完事了。奇怪,中饭吃好,父亲和母亲吵架的事情,像全然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一天绷得再紧的神经,此刻也放松下来。接下来的夜里,我们再听不到难听的吵架声。非但我家,塔鱼浜所有人家,大抵都这么一个样子。
家家其乐融融,处处一团和气,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和谐社会终于出现了。现在,就是塔鱼浜最凶狠的母夜叉,也一变而成了说话细细柔柔的小猫咪。年节的气氛,跟着暮色,跟着过一份人家的民间柔情,安静地降临下来了。
门早早地一关,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始祭祖。这个庄敬的仪式一开始,我母亲照例隙开大门的一条缝,闻听着呼呼折入的西北风,低低地呼唤我早夭的姐姐,一声“……来吃”,也很含着她的深情。这个仪式,与七月半完全相同,这里就不赘述了。所区别的,除夕的祭祖,菜肴来得特别丰盛,除夕讲究全鸡、全鸭、东坡肉、蹄髈、红烧鲤鱼、蛋夹子、油豆腐嵌肉……满满塞塞摆了一桌子。年节的肉,除了东坡肉为鲜肉,大多数人家用的是咸肉。所用的肋条,切得如装卸铁耙的枕那么大,满满的一大碗,白烧,一股肉香。为了省时,咸肉通常与老笋干同烧。这一碗东坡肉,大抵要“吃”到正月半,新年罢,才彻底消灭。我新年里去亲戚家做客人,这碗肉端到桌子上,也只拿眼睛瞟瞟,隔空闻一闻它的肉香味,并不动筷子。主家也会很客气地将大肉搛到客人的饭碗里,但客人大抵仍悄悄地搛回肉碗。这样客客气气地互相推让一番,也算各自尽到了礼数。汉良小我三岁,爱吃肉,看到这块肥美大肉,眼睛眨巴眨巴,早流着口水想吃掉它了。我眼睛一瞪,他没敢动筷子。
除夕的吃法有许多讲究,我现在只记得吃猪眼和猪的尾巴这两种。这猪眼,须得悄悄地一个人吃,不可让他人看到。每当吃此物时,大人在一旁,必是眼不旁斜,见了也只当没看见。据说如此吃法,可免胆怯。换言之,就是从此一个人走夜路,什么都不害怕了。中国人向来有吃什么补什么的恶俗,吃猪眼难道就补人眼了?这猪眼的魂大概就是这样钻入我们的小眼睛里去的。于是,夜里看到什么,就什么都不怕了。至于这猪尾巴,好像吃的时候无须避目。吃了猪尾巴的好处,说夜里不会咯啦咯啦咬牙齿。我夏天的夜里,常听到汉良咬牙切齿的声音,所以这猪尾巴,通常就让给他吃。
除夕用的是雄鸡。杀鸡退鸡毛前,孩子们总是眼明手快地将鸡屁股上最亮眼的几根鸡毛硬生生拔下来。鸡毛的用场,一是做毽子,反正做毽子垫底的铜板,无论康熙、嘉庆,家里都有;二是祭祖时,仍旧要将这几根鸡毛插回鸡屁股。当然,孩子们也只能插到鸡的屁眼里。鸡毛一上身,鸡就不一样了,雄鸡的威势一下子就出来了。雄鸡,塔鱼浜土话“骚呱嗒”。前一个字,描绘的正是雄鸡追雌鸡,趴对方身上的骚状,后一个拟声词,描述的是它啼声的嘹亮——雄鸡是一只忠实可靠的报晓时钟。
三十年来,有一道菜我离开塔鱼浜后一直不曾吃到,也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我母亲不知从哪里吃到一道叫鸡黄肉的菜,她居然无师自通地开始做了起来:切用夹精夹油的鲜肉若干;取鸡蛋若干,挑碎,与面粉同拌,撒入少量味精、盐;备一只小油锅;一切端整有序,她将鲜肉放入鸡蛋与面粉同拌的碗里拌匀,筷子搛入油锅,滚满蜡黄面粉的鲜肉,一入油锅,吱吱有声,肉不规则的周边冒出咝咝的气泡,一股肉香扑鼻而来。好多年里,一碗鸡黄肉,是年夜里我们最喜欢吃的小菜。且这道菜,母亲是在祭好祖,开始吃年夜饭的时候特制的,端到八仙桌上,还百热沸烫,十分好吃。但,那些年,肉实在舍不得多买,母亲为了省料,有几次用吃剩的大肥肉做,味道就没有原先的那么鲜嫩了。
年夜饭要满满地烧一大镬子。吃剩的米饭就用饭篮盛起,挂好,以示年年有剩余。这个活一般由我来做。年夜饭还要趁早吃,因为饭后有好多事正等着完成。隔壁的严子松与严阿大,每年都比我们早一些时间吃饭。吃完年夜饭,严子松开大门,再推开他家大门外的矮闼门,呼一声他们家的花狸猫。这猫极乖巧,见到门开,咪呜一声,但见一团黑影,闪电般跳入严家的门内。严子松矮门一掩,再大门一关,就没事可做了。他唯一的乐趣大概就靠在床头听广播机。严子松没有生育,还是远近闻名的四类分子。严家虽然从彭家浜领养了哑巴子新田。其时哑巴与顺娥结婚多年,也已另立门户,哑巴子一家似乎跟严子松严阿大夫妇已经划清界线,连逢年过节这样的大事,也不再来往——真不知道老严家那些年是怎么想的。
电影《过年》
一年最后一顿年夜饭隆重地吃罢,接下来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等着当家人来发压岁钿。每人都有份,母亲也有份。印象中的压岁钿,不多,从几毛到几块,与时俱进。父亲这时已经兑好新币,满脸堆笑,似乎连脸上的灰尘都在笑。他数钱的手抖动着,一张一张数好,确认无误,再一一分派过来。领到钱,我们兄弟俩笑嘻嘻的,觉得过年真好。
我有好几个舅舅,都在塔鱼浜。他们在前埭,走路七八分钟即可到我家。年夜饭后,舅舅们也会一个一个来坐一会儿,给我和汉良发一点压岁钿。因此上,过一个新年,我的压岁钿也还不少。至于压岁钿的用处,年初一去翔厚买几张花纸,或买一串小鞭炮。最让我动心的,当然是去乌镇或石门的新华书店买小人书。买来的小人书,连睡觉的时候都会放在枕头边,入睡前闻闻它的油墨香,心里就舒坦了。半夜里醒来,说来好笑,我也还会摸到鼻子边嗅一嗅。这铜钿银子用得踏实,用得还斯文。
乡下的孩子,嘴巴都比较臭。这嘴臭,倒不是一年四季不刷牙所致,而是会变着戏法骂人。我或许是其中出名的一个。因此,到了年夜里,我家乡有用老毛草纸擦小孩嘴巴的恶俗。所谓老毛草纸,就是擦屁眼的卫生纸。那时父亲买的都是便宜货,尤其这老毛草纸,黑乎乎的,硬得不得了,纸上的稻草一根一根简直可以抽出来。这种很粗陋的草纸,曾经擦得我们的小屁眼火辣辣地生疼。现在,一年将尽,父母们是很希望用它来擦一擦我们的嘴巴的。他们说用老毛草纸擦过的嘴,骂人的话就不算数了。那意思就是,小屁孩的嘴巴,就只当它是一个屁眼吧。于是,新年里讲出不吉利的话,全当它是放屁,无甚紧要了。据说有的父母等孩子们入睡后,还真的用这草纸轻轻一擦,真是可笑至极。
年初一的早上,忌口不少。最忌讳口出一个“早”字。比如,天亮了,或者被连成一片的炮仗声惊醒,父母叫起床,准备放炮仗迎灶君菩萨回家,迷迷糊糊中脱口一声:“早呵哩!”坏了。“早”与“蚤”同音,喊了这一声“早”,他们说一年里会生好多“蚤虱”。于是就要用这老毛草纸擦嘴。后来,孩子们嫌草纸糙乎乎的大不舒服,就央求大人们由着自己来擦。最终,简化到自己抬起手来,象征性地用手掌一抹了事。这也是与时俱进吧。
少不得打牌。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两个,四个人一桌,正好坐满八仙桌的四个方向,打百分,赢钱,下的赌注还不小呢,反正铜钿银子都在自家人手里,输也不心疼。这个时候的气氛是融洽的,一家人难得地坐到一起玩乐,大概一年也就这一次吧。打百分,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半夜,我们跟着父亲到稻地上放炮仗,隆重地接灶君菩萨回家。我们猜想他老人家刚刚天庭汇报工作归来。附近村庄的炮仗声几乎在同一时间噼噼啪啪响起,几秒钟里织成了一张无边的大网,笼罩了新年与旧年分野的此刻。这才是年节的声音,年节的气氛,千百年以降,原来仍是这样的猛烈、浓烈和激烈。此后,零零落落的炮仗声一直响到天亮。
年三十夜里的零食不可不记。一般的零食也就是葵花籽、南瓜籽、长生果、野核桃和大核桃。紫红的荸荠既可做小菜又可当零食吃(生熟两宜)。我父亲爱吃柿饼,每年他都买。此物甜津津,不宜多吃,吃多了,胃吃不消。唯有母亲自家做的芝麻番薯干,炒熟之后,吃上去咯咙咯咙,似乎大有嚼头的样子。这芝麻番薯片,是秋天做的——先将番薯烧熟,用铲刀拓糊,拌入芝麻,少许的糖精(那时糖是紧俏商品,稀缺),做成一张张薄饼,摊竹匾里晒干,再剪成菱形或片条,收藏好。年三十,取出这番薯片,放铁镬子里爆炒,炒时,怕贴锅而焦黑,撒入粗盐同炒,因此口感上又带一点咸味,也算本村的一大风味绝品。野核桃塔鱼浜土语“野葡萄”,大家都爱吃,常常是最先吃完。除夕的南瓜籽大多是夏秋之际剖南瓜时备下,半年下来,竟也积累了这么多,只可惜我始终没有学会啃南瓜籽的本事,我听到塔鱼浜的女孩咬南瓜籽的“的的”声,看到她们吐出的瓜壳竟然只只完整,真是大开眼界,满心佩服。而我,要么将瓜籽咬碎,要么咬半天还吃不到籽粒,南瓜籽的两面被唾液浸湿,最终呸的一声,一吐作罢。
毕竟是江南的深乡下,塔鱼浜过年,没有一家会贴春联挂红灯笼的。
年初一的早上,落下门闩,大门吱呀一声,分向左右两旁,一道狭长的、鲜亮的、万古常新的光灌进门来。揉揉眼,但见附近的稻地上,铺满了碎碎红红的纸屑,空气中还有硫磺的味道,那是昨夜四个炮仗与一串百响留下的,是除岁的灰烬,也是清早有关年节的最美好的记忆,或许还是新年留给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第一天的脚迹。
本文节选自
《塔鱼浜自然史》
作者: 邹汉明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品方:大方
出版年: 2021-07
编辑 | 朱皮特
主编 | 魏冰心
新版微信修改了公号推送规则,不再以时间排序,而是根据每位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在这种规则下,读书君和各位的见面会变得有点“扑朔迷离”。
数据大潮中,如果你还在追求个性,期待阅读真正有品味有内涵的内容,希望你能将读书君列入你的“星标”,以免我们在人海茫茫中擦身而过。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