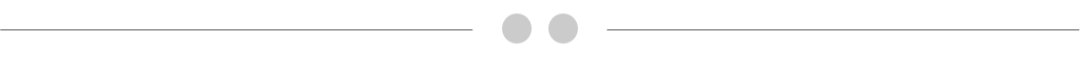如何用维特根斯坦解释“自由”?


独家抢先看
文 | 李厚辰
之前有篇文章在尝试提出对今日我们“自由”困惑来源。约略而谈,就是我们对自由太依赖“想”,而“看”得太少。这里的想,分为对我们自己自由的“内学”,和对他人非自由的“外学”。
所谓自由的“内学”,我们关注自由的“意志”,即想法的自由,因此我们相信知识让人自由;相信类似瑜伽、冥想等修习方式通过对注意力和意念的练习让人自由;
也相信通过心理学的路径改变想法,调整情绪,领会潜意识,以摆脱内心的束缚获得自由;或者直接一头扎入道家,跳出人的世界,在一个更巨大的视野与天地中,消解那些让我们不自由的困境。
这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个体面对如此巨大的世界,难免感觉世间无栖身之所,因此只能反求诸己,在自己的内心来寻找这个自由的充分条件。
所谓反自由的“外学”,就是说建立在各种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中的他人,在这种理论解释中,都是被环境决定而没有自由意志的。
例如被利润控制而必然贪婪的企业家,例如被傲慢和偏见控制,而必然轻视我们的外国人,例如因为愚昧而必然盲从群体的“乌合之众”,以及因“地理”、 “基因”、 “演化论”而形成某种“必然”的某类人。
这是我们熟悉的公式。对于这些大多时候“有害”的他者,我们并不认为他们会产生任何改变。
这样的图景进一步加剧了外部世界的恐怖无望,让我们想退回“内在自由”的疆域,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在外部世界的选择,面对这些可怕而又不可能改变的“敌人”,我们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导致文章难以理解的,大概是对于问题的解决框架并未完整呈现,就是所谓的“看”需要如何理解。我们是在“外部”走投无路,才被逼到“内求”自由的,而内求自由从来都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尝试。我们的自由在世界中,而不在心里。
因此这里的症结在于“外学”的部分,如何少想而多看,我们的自由就在其中。
01.
看一位企业家的利润抉择
在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中,一个企业家的“利润分配”在于他自己的贪婪程度,一个企业家的所有操作和动机,“究其根本”都是满足他个人的私欲。甚至企业如果能够投身公益慈善,也都是为了营销和商誉,或者为了避税。这些当然不是臆想,这样的情况存在。
因此一个企业家是否“自由”,似乎就要看他是不是能抵御住贪婪的“私欲”,选择慷慨地分配更多利润给予雇员,如果仅仅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中,我们当然不相信人的“自由”,选择慷慨而不是自私,这也太难了吧。
但一个企业家面对利润,真的是在做“私欲”与“慷慨”的选择吗?
一个企业家做大净利润,有很多种不同的理由。实际上这个世界上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家总是少数,大多数做企业的人都面临很大的不安全感,企业的净利润就像是一个企业家的储蓄,面临市场的波动和变化,净利润很多时候并非简单满足短期“私欲”的工具,而是投入次年再生产,或填补现金流储备的一笔钱。
不仅如此,一个企业家拼命提高净利润率就是一种贪婪的剥削吗?对一个行业的企业而言,净利润率也是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指标,如果一个企业的规模类似,净利润率却远低于同业竞争者,这也一般被看作企业竞争力不足的表现。
进而在资本市场,净利润率与一个企业的估值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资本市场与估值也经常被看作企业股东牟利的工具,这当然是事实。但其实资本市场的另一个很大的作用是企业融资的渠道。
更不必说,其实很多时候企业做大净利润,就是为了扩大规模进行再投资,这部分钱也会逐渐流入设备或人力的投入。
请注意,在上面的所有可能性列举中,我一点都不否认企业家的贪婪或逐利,也不提及他们突然善心大发或变得慷慨。只是说,“利润”这个东西,在私欲之外,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我甚至并不反对有人说,究其根本,企业家就是逐利的。
只是在一种过于简单的视野中,比如现在企业有40万净利润,企业家面临两个选择,是要自己买辆汽车,还是分给员工。这里的“逐利”是一种零和博弈。
而在企业40万净利润,企业主为了逐利或野心进行再投资的时候,这40万在次年却可能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被雇员占有。在这里,企业家的私欲与员工的利益,就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
更不必说上面提到的更多其他考量,则更不可能被放置在简单的“利益分配”的视野下考虑。这也是企业家的真实考量,企业家是否会考虑多拿钱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当然会的。但有时企业家也在放弃近期利益而野望更大的远期利益,有时也在考虑企业安全与同行业对比的问题等。
而这恰恰就是企业家真正的“自由”所在,是要现在拿所有净利润去炒房,是投入再生产,还是为自己改善生活,这里所有各不相同的选择,还包括其具体的路径和方式,以及产生的外部性,将带来一个不能用简单“剥削”和“贪婪”理解的世界。
马克思意义上贪婪地剥削着的企业家;韦伯意义上敬守天职,进取财富的企业家;熊彼特意义上以创造性突破困境的企业家,这在一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
在截然不同的背景、行业和情况里,在不同的语境中,企业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自己的事业,做着各种不同的决定,并不断拓宽他可以做的决定。
对利润和私利的追逐不过是这件事的一个模糊动因,却不是对企业家生涯的完整动机和要素。对“经营事项”“利润”“人力资本”看到越多的可能,企业家就有越大的自由。
02.
想与看
接下来,我们要来探索探索什么叫“看”了。
关于“父母打孩子”这件事,你能想到什么?父母不称职?这是人类唯一不用任何职称和筛选就上岗的职业?孩子早年心理创伤的长期持续性影响?原生家庭理论?
父母可以打孩子吗?会造成永久不可逆的坏影响吗?理论界争论不休。
在高铁上看到一个熊孩子呢?如果这时父母教训一下孩子,只要不是太过分,我想周围的人都能接受。
当然我们依然可以讨论,孩子的顽劣是日常教育失当造成的结果,打不是唯一要做的。但在那个特定的当下,其必要性确实显著。
这就是“看”的效用,看让情况显得清楚。看也不会改变人的“想法”,一个秉持父母不应该打孩子的“观念”的人,当然也会在某些情况下看出来,打可能是最快速有效的惩治手段,但这并不是不自洽,这个人同样可以继续坚持“父母不应该打孩子”。
这就是应然和实然世界的区别。应然世界中的关系是由一些典型的、定性的事件与语言概念、理论构成。
而实然的世界却是靠“看”的,我们很了解身边的人,知道他们的复杂,不是因为我们曾经坐下来,用一些理论仔细分析了对方,而是因为“看”,从某些时候,看到对方的可爱,别的地方看到软弱,有的时候看出对方的坚强,有的时候看出执拗。
看出这些并不困难,不依靠复杂的理论和分析,却依靠熟悉和明确的背景语境。
存在于网络世界中的人的“可爱”总是符号化的,要么是特定的样貌,要么是一种特定的符号化的行为,生活世界中的“可爱”却要微妙的多,你在熟悉的人身上看出来的可爱,换个人来看可能丝毫没有感觉。在维特根斯坦的语境中,这就是一个“面相”。
“面相”是触目可及的,没什么知识与理论的门槛,不怪老话说“见面三分情”。澳大利亚在2014年的电视节目《与敌人相处(living with the enemy)》中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
他们将价值观完全相左的两个人安排在一起生活,来看他们是否可以相处,其中包括动物保护组织人员和以狩猎为兴趣的人,反移民当地人和非裔难民移民,反穆斯林白人和穆斯林等组合。
在节目中,他们都能够近距离地发现很多通过理论和概念无法注意的细节。这就是他们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了未曾预料的“面相”。
这些面相未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立场,动物保护组织的人依然认为保护动物迫切和必要,但也发现狩猎并非一个“恶习”,狩猎爱好者也明白动物保护不是个“有钱人的虚伪关怀”。
想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基于有限的信息,辅以知识和理论,给予定性和理解,并将这种理解成为一种模式,并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看则是一种在情境中的视点,并不基于理论,而更依赖对一种特定生活状态的同理,而形成的一种理解。
这是一种不断构成的“面相”,每一个“面相”就是一种新的理解,我们不断发现,原来我们以为被单一环境要素决定的行为,或是简单因为“失德”或“放纵”而进行的行为,或是只有一种糟糕“本质”的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中能够展现出的丰富可能性。
在一种比较简单的总结下,想不断充实和构成应然的世界,而看则不断拓宽我们对实然世界丰富性的认识。
我们常说,“世界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不过我们在脑子里这样“想”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世界应该是复杂的,人应该是复杂的,世界与人不该这样简单吧?这还是个应然的问题。
唯当我们看到了实然的丰富面相,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人或事的好坏,多种可能,世界与人的复杂才落实下来。
而我们的自由,就在这样的复杂之中。
03.
自由在世界之中
海德格尔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即“此在在世存在”。这句话应对的则是海德格尔对于“西方哲学遗忘了存在,只记得存在者”。存在者就更接近一种成形的,被“想”把握,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
而人在世存在,永远在存在的途中,则没有寓居于“观念”之中。自由也不是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在世界之中的问题。
当我们谈论道家的自由,谈论人可以想象那不可观察之大,与不可想象之细微,从而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和片面,因而摆脱困苦,获得自由之时。我们在谈论一个“大世界”,却不在世界中,这是个由“语言”构成的大世界。
举个更近的例子,一想到“高维文明”的神奇,作为“三维文明”的我们,就感觉到渺小和浅薄,这好像在说宇宙。但实际这也仅仅是由“高维”和“三维”的概念构成的,我们没有经验过这个概念。
举道家和宇宙观的例子,是要回到我们的“自由内学”,不管是以上两种,还是有练习方式的冥想瑜伽,至少在我看来,其与自由的关系都是一种语言构成,一个建基于概念上的自由,而不是真正可经验的自由。
就像之前文章中提到中考分流的困境,有人反驳说:难道职高就不能给予人希望吗?随着对职高不断的投入与发展,社会变得更加尊重蓝领工人,职高也是一条颇有希望的道路。
这里面因“投入”和“发展”,因“变得尊重”而有“希望”,也可以套入到任何句式,依然是仅仅存在于语言与应然中的。
自由一定是个实然之物。就从这简单的一点,我们就该明白,不管是讨论人是否有“绝对的自由”,还是讨论存在主义意义上“自由”的本源特点,这都是些搞错了重点的玄思。
自由不依靠“内学”,而依靠“外学”。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反自由的外学”其实也堵死了我们自己的自由之路。
将他人于世界中理解为仅仅能够被环境“决定”,其实不是对他人的浅薄理解,而是对“在世存在之人”的浅薄理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自己,因而被逼从内在建立自由。
当我们通过对他人的“观看”以看出更多面相,开始理解他人生活的丰富,这里丰富起来的也不仅仅是他人,而是“在世存在之人”的生活境况,我们自由也在这个丰富之中呈现。
同理心的关键不在态度,不在程序,不在知识,而在见识。因而论语说: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恐怕其中也可以蕴含这样的启发吧,知人的见识,是对世界丰富性的经验和熟练,而这种经验和熟练,才是自由的基础。
他人如何可以不受环境的决定,那么我们也就可能效仿之。
尾声.
网络是个应然世界
但很可惜,网络世界是个应然世界,即便是网络世界中的人物报道、访谈,也决不像面对面的人际交往,能够展现出人的丰富面相。可以说互联网,这种以书写文字和社会理解为主的媒介,是一个属于“想”的媒介。
互联网会是我们的自由的阻碍与牢笼。互联网在人类世界中的出现,到现在为止是一条单行道。在这个媒介中,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太少太少,虽然每天我们都在大规模使用我们的眼睛,但那不是真的看,或者说即便你在看一条视频,看一部纪录片,那几乎也就是在看概念,看观念,看理论。
互联网不承载我们的眼睛。这篇文章再次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互联网,不过这可以今后再继续展开了。“不要想,而要看。”记得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教诲,我们都会从中得到更多自由。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