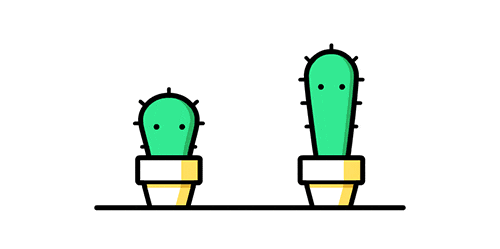在没有大鱼大肉的时代,我们乡下人是这样解馋的
我问过姥姥,姥爷为啥那么喜欢吃辣椒?我姥姥说了一句哲学家永远说不出来的乡下话:“辣椒是穷人的馋啊。”
——画家 冯杰
01
苦瓜和尚和苦瓜的脸庞
苦瓜开小黄花,黄扣子大小,为时不长,丈量完二十四小时后就悄然退场。散出一种独到的幽香,哪怕只有一朵,风来,一个院子里都会填满这种叫幽香的单词。
大画家石涛的号是“苦瓜和尚”,他编过一本《苦瓜和尚画语录》,我一边看书一边吃苦瓜,文字苦,却感觉石涛的绘画风格并不“苦”,而是“涨”。笔墨抒情的成分更多。张大千是画史上造假石涛的高手,现在拍卖行的许多石涛画都出自大风堂之手,且一一蒙混过关。张大千让我明白,世上最妙的造仿不是苦苦摹画,不是像不像,而是意创。是替石涛创作,让石涛一直死而复生。这例子是画坛三十六计之一,我叫它借尸还魂。
苦瓜的苦风格其他蔬菜无法模仿。
一个在四川泸州工作了一辈子的表舅,晚年返回中原,定居郑州。他告诉我:少不入川,老不进关。他年轻时进川,是个美丽的错误。但能做一手好苦瓜菜,我认为是最大的收获。我在他家第一次吃过炒苦瓜后,上了苦瘾,回来就在院子里自己种,以至家里晒衣服的栏杆上都爬满了苦瓜须。
说苦瓜脸是形容一种愁相。天使有愁容,植物也有愁容。
苦一向是自己的事。《传灯录》里有一句禅语:“苦瓜哪堪待客。”
苦瓜像我们这类小人物浓缩的生活,苦,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皮到瓤的苦。静下心来想想,苦中恍然还能有一种回味。这才是支撑生活的骨头。像大家平时过的日子,尽管苦,若等到下一盘苦瓜端上来,照样要吃。
02
韭菜的剪法
“韭”这个字形很有意思,长长短短,横竖都是发的韭叶子,难怪《说文》里这样解释:“在一之上。一,地也。”如果倒着看,压上一个盖子,就该是不发芽的韭黄。
韭菜以春天最好,夏天就苍茫了。人到中年才恍然,出名要早。古人的“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讲的都是及时,说的“时间和速度”,在讲物理。《政和本草》里说治消渴饮酒无度时,可以吃韭,“韭苗日吃三五两,或炒或作羹,无入盐,但吃得十斤即佳。过清明勿食”。这哪里是治病,说的是过生活。
先人命名一种植物总怀有一种愿望,“韭”乃“久”谐音,《说文》说:“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诗经》里最早出现“万寿无疆”这个字眼,就是与“祭韭”有关。只要有韭根埋下,不必年年播种,它是一种内含毅力的植物。母亲从老家挖来些许韭根,就种在盆里、地上,有时等到做饭下锅时,才忽然想起来剪。
我们乡下剪韭的一个方法实在高妙,不用镰刀、菜刀,认为那样剪出的韭菜会带有“铁腥气”,用碎碗瓷片来割,这样割的韭菜原色。
那么多人与韭有缘,苏轼的“青蒿黄韭试春盘”,他调制了三种颜色,上菜。陆游的“雨足韭头白”,是一种诡奇意象,白头的韭啊。郑板桥的“春韭满园随意剪”,他向往闲适。韭菜能在文学史上发芽,都与吃有关。其中要数杜甫的那一把韭菜最鲜。
杜甫《赠卫八处士》是杜诗精品。“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我每每读时,叹世间苍茫。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杜甫有,我也有。韭菜肯定也有。
雨夜留客剪韭,是古时诗人的一种习惯,朴素不失雅致。相当于现在诗人找个理由要四个小菜、一捆啤酒喝到天亮。
所谓“剪春韭”,不是室外活动,而是回归室内的一种烹韭方式,如果你以为是手持一盏马灯或电筒,半夜到菜地下刀剪韭,那就错了。
我告诉你古人“剪春韭”的方法,步骤如下:就是一手拿一束韭菜末端,将另一端放在清盐水里煮,然后剪掉末端,最后投入凉水里。这样烹出来的韭菜味道清脆可口。
就这么简单。并不是唐诗别解,也不是误读,我家来人时从来就是这一古风。
03
“二十五节气”和苏东坡的咳嗽
哮喘有点如怀旧,似曾相识燕归来,每到一定季节,不期而至,倒像是二十四节气里的一种,真可称为“二十五节气”。
我少年时,几年里都困于咳嗽,病期自每年秋冬之交开始,到春夏之交结束,比一个叫“立冬”的节气都要准时。咳嗽起来,喘得胸口疼,震得头痛,夜里睡觉都要趴在床上,像一个拙劣的诗人写一行诗都要点五个标点。
到医院治疗,医生最后诊定为“季节性过敏性哮喘”。开了一大堆西药,饱受苦药之累,最后也未根除,年年复发。一天,乡下的姥姥知道后“出场”了。她说偏方治大病,即使无效,也不影响身体。姥姥一说内容,我笑了。
姥姥用红梨炖川贝,熬两小碗,每天晚上让我睡前喝一碗,次日早上喝一碗。半月之后,竟好了。单方是红梨一颗,贝母十克。半月一疗程。姥姥说,川贝母最好,如无贝母,单熬红梨也有效。
后来读书,我看到更气派的单方,与明末的傅山有关。在古代,哮喘到极致就是痨病,谈痨色变。傅山是名医,又是书家,他给一位痨病鬼开了一个药方,药材竟是满满一船梨,让患者坐在船头,自山西吃到河南。果然,船还未到下游,痨病在中游就好了。
这方子让我惊得吐舌头,比姥姥的厉害。多亏我未遇到傅山,姥姥只给我十五颗红梨。
一天看《苏东坡传》,知道苏东坡晚年也困于咳嗽,哮喘。可惜双方生不逢时,都在时空里错过了,要不我可以送给他我姥姥的十五颗红梨。
面对心平气和的风景,如果你控制不住自己咳嗽,要一种聪明简单的治疗气喘的方式,我希望尝一下我姥姥的红梨。不行你再去看西医,只当这是一个轻松的古典乡村游戏。
先执一颗红梨。
04
柿子的别名就叫涩
天下画柿子的人多多,如果不以名分才气论,只按画柿子个子的大小往下排,“柿子座次”一定是这种排法:计有吴昌硕、齐白石、虚谷、赵之谦、潘天寿、冯杰。
我手下走过了那么多颗柿子,认为,柿子画得最好的一幅却是南宋牧谿和尚的。六个柿子端坐在那里,拙笨、简朴,却透出大智、慧心。像六个红脸罗汉,在打坐。
打我识字始,知道柿子就是涩。我对“涩”的感悟一向深恶痛绝,因为小时候偷的柿子大都青涩,苦不堪言,像文言文,像鸡肋。因为涩,小时候跟着姥爷在乡村“漤柿子”,这是一道乡土手工制法,用烧开的热水将瓮缸里的涩柿子加工致熟。这样,青柿清脆,不涩。
“涩”在中文里的意思永远是:青涩,艰涩,苦涩,稚嫩,晦涩,滞涩。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可划入出身不好接受再教育的词列。后来,一个懂日语的人告诉说,“涩”在日文中显得别开生面,可引申为“好的”“雅的”品位。
涩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涩有一种青春朝气,原色的,野性的,更接近原创。只要当下有涩,未来肯定就有成熟。涩一点愈好,起码比世故、媚俗要强。
而媚俗就是“软柿子”,从“骨感”上言,拿不起来。
05
辣椒是穷人的馋
传统画家在画《清白图》时,画完白菜,余兴未尽,就在一边添上几支辣椒。若几尾红鱼,般配。辣椒属平民日子里的道具。
那时我们家贫朴,辣椒的辣就像生活中的味精,是点睛之笔,让人忘记日子里的苦与艰难。走在乡村,冬天屋檐垂落的一串红椒分明让人鼓起向上的勇气。
从形状上看,柿子椒算是素椒,“狗尿椒”是最辣的,“朝天椒”是辣中的极品,一般用于观赏,极少有人敢吃。用途多可作为乡下人打赌的道具。
辣椒下来的季节,姥爷用盐水泡满满一缸青椒,吃饭时就随手捞出几支,算是最好的菜。看到姥爷的这种吃法,我也捞一支青椒效仿,却不得不叫喊苦辣。那种辣,绕梁三日。有时没有青椒,姥爷会将干椒在掌中搓碎,放进碗里,显得更暴烈。
乡下的日子就是这样过去的。简单,厚重。
我问过姥姥,姥爷为啥那么喜欢吃辣椒?我姥姥说了一句哲学家永远说不出来的乡下话:“辣椒是穷人的馋啊。”
在没有大鱼大肉的时代,我们乡下人就是靠这种方法解馋的。简单,有效。它是穷人的权利,且还不用去央求他人。真不知道,没有辣椒的日子该怎么过?
06
红薯的人道主义
请耐着性子,先来细读以下一段文字: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七零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州原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这是一九六三年郭沫若为纪念红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而作。那一年我还没出生,可见红薯比我大得多。等到我此时去写这篇红薯文章时,已经四十三岁了,也该是红薯传到中国四百一十三年了。薯到中年啊。
红薯来到中国的经历极为精彩,简直如一出传奇小说,我就听到过三种民间版本:
一说是有一陈姓华侨,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从菲律宾将薯藤挟入小篮子内,航海七日,地下党怀揣情报一样,秘密潜回福建,开始种植,以后在中国四处传播。
第二个说法:一个人在吕宋岛(也是菲律宾),取薯蔓缠入缆绳中,涂上青泥,避过检查,得以渡海,传到中国。使用瞒天过海之计。
以上两个都与菲律宾有关。
第三种版本更是情节跌宕起伏,近似我们北中原民间艺人说的“评书”:话说红薯原产自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交叉的脚指头,就是红薯的形状),严禁外出中国,违者治以死罪。一个叫林怀兰的中医,遍游交州,因其医治一关将有效,就被推荐去医治国王之女。看好后,国王赏赐熟番薯,林怀兰就要求生番薯。林先生是有心计之士,咔嚓咔嚓咬了几口,就留下半截藏起来,急急告辞,这怀薯之人要归回老家。
过关时,关将盘问,林怀兰便从实告诉,要求其私自放行。关将说:“我受的是君王俸禄,将你放行这是不忠,然而我感谢先生之德,违背了又是不义。”真是一团矛盾。自己解不开,干脆跳到水里死去就解开了。评书最后要的就是这效果。这关将倒像中国易水边那些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林怀兰携薯回来后,遍种于粤,后人纪念他,还建立了薯公庙祭祀。让人感慨的是,他旁边配以那名关将。民众感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觉得这一则红薯来历写的不是“薯”,写的是“人”以及人道主义,倒是一出话剧的素材。
关于红薯这道题也许还有更多解,传到我这里,只记录以上三种答案。
红薯来到我的北中原,它不像山药和土豆,山药面庞沧桑,土豆表情丰富,一个个皱眉或舒展,喜悦或哀伤,相比之下,土豆显得丰富多彩,红薯则是另一种形象,外表心平气和,更显出一种乡村的淡定。
我看到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将薯总结为“十三胜”:
一亩收数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诸土种中,特为敻绝,二也。益人与薯蓣(就是山药)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百亩,四也。枝叶附地,随节作根,风雨不能侵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岁不能灾,六也。可充笾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饼饵,胜用饧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秽不容,其间但须壅土,勿用耘锄,无妨农功,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十三也。
他说的可都是些好词。
红薯对我们北中原人而言,更是功德无比,那是生命里的地粮。当年困难时期,是一块块小小的红薯养活了北中原人。让我感恩红薯。
红薯做生活里的主粮,梗、秧、叶子都可食用。红薯一般生吃、煮吃、蒸吃,还晒成红薯干,下在锅里,或磨成红薯面,做饸饹面、窝头。姥姥还用红薯叶蒸菜馍,叫“揣”菜馍。
乡下人在形容人比喻人时有个俗语——“红薯屁还没放尽,就想装城里人”,是调侃那些忘本之士,可见红薯有“气贯长虹”的作用。现在城里人却偏偏要装“乡下人”。
天下之雅是不同的,若天下之俗,到骨子里则都是一样。
我家曾在黄河大堤下一个叫孟岗的小镇居住了近二十年,每到冬天,都要从黄河边的乡村送来上千斤的红薯当口粮。寒冬,有时我正在夜半睡觉,会被窗外冬夜里滴落下来的“晃啷晃啷”马铃铛声惊醒,那铃声敲打着寒霜,像黑暗里碎碎的亮光。还有马匹不时打出的喷嚏声。那是从乡村拉来一大马车红薯。
我起来拿手电筒一照,马鼻上一层白霜。
红薯一下子吃不完,父亲就在院里挖了个地窖,让它们在里面过冬。母亲晴天就开始切红薯片,挂了满满一院子。余下的红薯对换成粉条。
后来别人都说红薯如何好吃,我父亲就第一个反对,他当年吃红薯“吃伤”过,他说,看到红薯就烧心、反胃、冒酸水。现在我想起,那是艰辛生活给他留下的痕迹。
父亲曾得过胃溃疡病,这可能与当年以食红薯为主粮有关。父亲服了好多年药,记得有一种叫甲氰咪胍的药,止酸。
据说所谓气质都是童年形成的,我除了没有书卷气、金石气、英雄气、名士气这类好气息之外,一生贯穿着红薯气,也许气到永远。
我第一次去西藏,因为高原反应,饮食不适,在拉萨街头正头昏脑涨,忽然,闻到一丝烤红薯香,顿时豁然开朗,就像一条细细的小绳子牵着我,便寻着那香气找去。拐了几个弯,终于见到一个烤红薯的铁皮炉子,立一个红薯脸膛般的汉子,急急称了两块。边吃边与那摊主聊,他是南阳人。
汉子说,河南的红薯是天下最好的。
说这话时背后就是布达拉宫,红白相间。他说话时一点也不胆怯。
吃了红薯,高原反应轻些,妙若仙丹。
对红薯,童年是充满珍惜的。有一次我在深圳一家宾馆吃早点,对面坐的一个外国女人让我大开眼界,她是如此食薯的:先用筷子将红薯上下左右分开,只吃中间的部分。这时露出我的井底之蛙面目,她这种方式我小时候可是不敢做的,我吃时把红薯皮剥厚扔掉,姥爷都是不允许的。
红薯贯穿到现代,已让人们熟视无睹,平常得不会都去心存感念了,红薯才一个个睁着红红的眼睛,那是在忧伤地注视着原本属于它的苍茫大地。四百年前,它曾是一方异族,融入另一片新颖丰厚的土地。四百年后,它竟成为主人,大地的主人。
附一:我母亲炸红薯糕的方法
先将红薯洗净,煮熟后与黏面揉在一起,盘成条状,压平,切成方块,再蘸上芝麻,放在油锅里,用文火炸,捞出来后晾凉即可食用,是童年时走亲戚的用品。
母亲又把这些红薯糕称作“三刀”。我问:为什么叫三刀?母亲说:就是用刀在糕上轻轻切三下。
附二:一首关于红薯的诗
红薯物语
拥有自己的气质 谦卑 质朴
它穿着红衣服
接近土地和雨 抵达“农业”这一词汇中心
感激热爱 或者遗弃抱怨
红薯用口语和方言在地下流动
那些大海的信息渗透纤细根梢
成为大地的毛细血管
用自己的手势触动
表达未知的另一个世界
每年秋霜涌来 尘埃落定
红薯一张张平静的面庞
是童年时自父亲的马车上所看到
映着干枯的寒霜 冻红或带着羞涩
红薯一颗颗无序地走下马车
挤满我家空旷的院子
有几颗红薯没有跟上来 在路上落伍掉队
像北中原乡村那些早早退学的孩子
本文节选自
《泥花散帖》
作者:冯杰
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