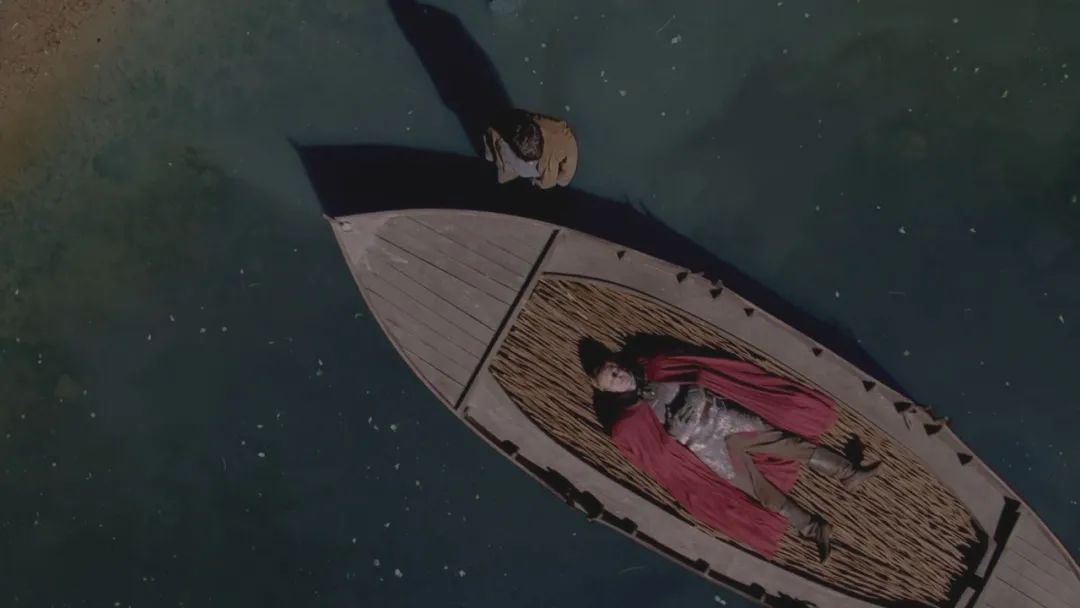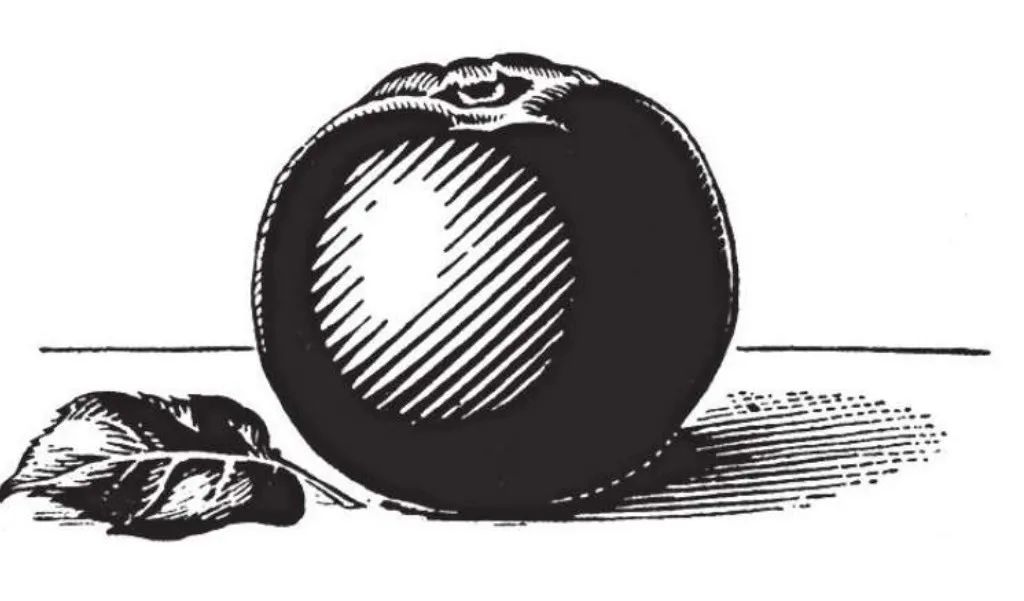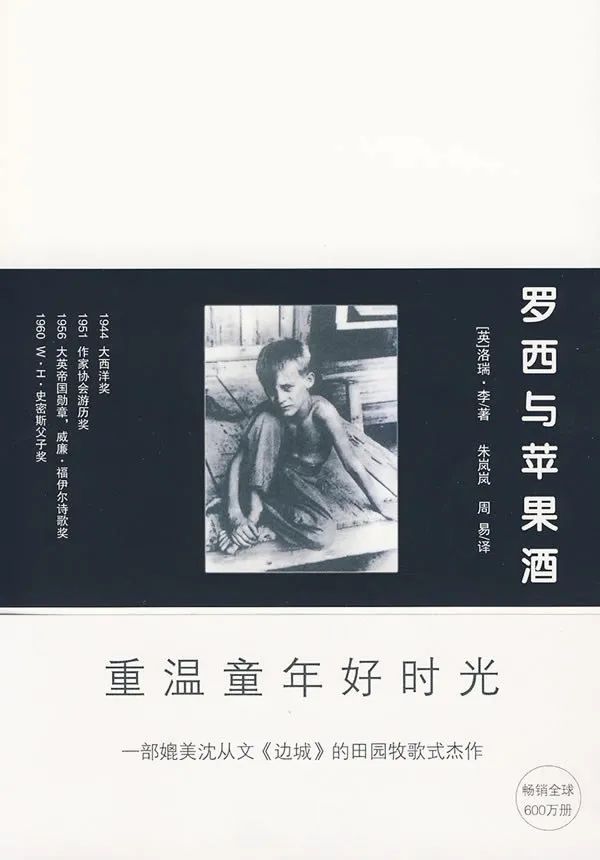牛顿选中的苹果,名叫“肯特之花”
苹果树是树木界的头一号,万事万物的开端都有它的存在。无论是伊甸园的“禁果”还是古希腊的“金苹果”,我们若要探寻文化的源头,苹果都是无法绕开的。
如今缺了一口的“苹果”以另一种路径,强势地介入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是苹果呢?
本文选自《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第17章《苹果树》。
01
那些著名的苹果、苹果树
在《所罗门之歌》中,苹果树是森林中最令人向往的树,是情人的爱巢和食品柜,而情人们的每一口呼吸都带着苹果的芳香。在希腊人看来,它是爱情与不和之树,因为在面对三位女神而她们都觉得金苹果应该属于自己时,帕里斯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认为它是爱神阿弗洛狄忒的。遭到拒绝的女神赫拉和雅典娜发动了复仇并迅速升级成一场吞噬一切的冲突,让帕里斯在灾难性的特洛伊战争中获得了特洛伊的海伦,但是失去了其他的一切。
苹果树同时滋养着爱情和仇恨,这一点你可以从果实的生长方式中看出来。一只长在树上的苹果,通常有一边胖乎乎的脸颊沐浴在夏末的阳光中,晒得红彤彤的,而另一边脸则抵在粗糙的树枝上,苍白泛绿。太阳起到催熟作用,为苹果的枝条赐福添喜。
苹果既是太阳的亲密挚友,也是《毒树》的果实,这棵树能在充满被压抑的愤怒和嫉妒的心灵中迅速生长。这种结出完美的、大小适合手掌抓握的球形果实的树木,身上有一种东西会激起深刻的情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从《白雪公主》的故事中知道了这一点。在亮晶晶的可爱的红色表皮之下,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虫眼、蠼螋和完全烂掉的果核,并不是每一口咬下去都像它许诺的那样甘甜。
一只坠落的苹果似乎代表着生机勃勃的美丽就此终结,这是圆满的时刻,也是一切都失去了前途的时刻。然而事实上,一只坠落的苹果往往意味着开始。
1665年,艾萨克·牛顿因为瘟疫暴发而抛下了自己在剑桥大学的研究,并回到林肯郡的家庭农场。在这个季节,果园里大量的苹果是常见的景致,但是在这一年,他用了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苹果为什么会落到地上?为什么不是飞到天上,或者在果园里横着到处乱飞?对于这位聪明的年轻数学家来说,那棵苹果树下平静的一小时带来了启示和变革。那是一棵智慧树,一次幸运的坠落,因为整个太阳系的运动模式忽然之间都在这个被风吹落的果子中暴露无遗了。
牛顿的苹果树长到了非常老的年纪,最终在1820年屈服于重力,轰然倒塌,但是这座果园保留了下来,成为这棵苹果树顽强生命力的纪念碑。倒下老树的一根枝条,如今也已经长成了粗壮的老树,每年秋天仍然结出许多红红的苹果。这个古老的品种名叫“肯特之花”,果实会在成熟过程中从绿色变成橙色,再变成红色。
牛顿宿舍前的苹果树
最初的那棵树遗存了一块小小的木头,现在被制成一只鼻烟壶陈列在庄园宅邸中,就像是某种神圣的遗物一样。而在附近格兰瑟姆的艾萨克·牛顿购物中心里有一个巨大的时钟,每逢整点打钟报时,一只红色的塑料苹果就会敲响大钟,吓到一头正在睡觉的狮子和毫无防备的游客。(在这家购物中心进行全面重建期间,这棵树的生存能力受到严峻考验,但是那头狮子、那个苹果和那个时钟依然还在。)
当由一只苹果和一片树叶构成的彩虹色商标成为第一批个人电脑的著名标记,将千兆字节的时代与伟大的牛顿科学革命联系起来时,苹果作为智慧树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这个标志还被解读为向阿兰·图灵的致敬,他是一位代码破译专家和计算机先驱,也是一名同性恋者,同性恋在当时的英国是非法的,他在1954年自杀与由此导致的过大压力有关。被发现时,他的尸体正躺在一个毒苹果旁边,这个苹果被咬了一口,就像白雪公主咬过的那个苹果一样。
电影《模仿游戏》剧照
这个商标也可能和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革命有关,因为当史蒂夫·乔布斯13岁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乐队成立了他们的苹果唱片公司。
披头士为企业界奉上了他们的“苹果公司”,让这只苹果成了青年文化的象征。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非常喜欢这家以一只澳洲青苹为商标的公司推出的第一张唱片,因为《嘿,祖德》是当时最长的一支单曲,七分多钟的播放时间让他们能在“呐呐呐呐呐呐呐呐”的尾声终于结束之前抓紧时间喝一杯咖啡。这张唱片B面的歌是《革命》。披头士的歌迷们做好了耳目一新的准备,成群结队地涌入开在贝克街的苹果专卖店,结果发现自己买不起在那里出售的大多数东西,由此暴露出这种商业模式的缺陷。
在青春永恒的神话国度中,每个人都以苹果为食,至少古代凯尔特人是这么认为的。这种水果在神秘的阿瓦隆岛生长得十分茂盛,根据丁尼生的想象,那里“拥有深深的草甸,幸福、美丽,到处都是果园和草坪”,受了重伤奄奄一息的亚瑟王曾被送往这座天堂岛疗伤。
电视剧《梅林传奇》剧照
在维京人看来,那些强大的男性精英众神也要依靠女神伊登可爱的苹果阻挡衰老和死亡。苹果树长期以来和青春的联系也许和它本身相对较短的寿命有关。与橡树或红豆杉不同,苹果树往往活不过30年,在它们生长缓慢的英国同胞们还没真正开始发力之前,它们自己就已经迅速生长然后倒下了。它们以快得惊人的速度衰老,变得容易感染不幸的病害,比如苹果腐烂病和黑星病。即便是一棵健康的树,也长着粗糙的棕色树皮,树枝以奇怪的角度伸展着,仿佛还没老就已经驼背了。
这种树的所有优点似乎都汇聚在完美无瑕的红玫瑰色果实上。有些苹果树的确能活到80岁、100岁或者更久,但是一旦这些老迈衰败的树停止结果并且开始掉落树枝,剩下的日子就不多了。
02
苹果的品种名,也充满了故事
在2002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五十周年庆典中,只有两棵老苹果树被林木委员会列入50棵“大英之树”的名单中,一棵是拥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牛顿的苹果树,另一棵是位于诺丁汉郡绍斯韦尔的第一棵“绿宝”苹果树。
虽然玛丽·安·布雷斯福德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用一粒种子最先培育出了这种苹果树,但英国最受喜爱的可烹饪苹果却是以屠夫布拉姆利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他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那一年买下了玛丽的村舍花园,看到了第一批绿色苹果在枝条上膨大。这种苹果真正的潜力很快被梅里韦瑟一家发现,他们拥有当地的苗圃,很快从屠夫先生的树上采集插条并建起了一座果园。
这些苹果的成功和它们的个头十分相称,它们的名字如今为人所熟知,这也证明了一棵苹果树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成为永恒。“绿宝”苹果的名声也无法保护那棵树的未来,它在几年后就倒在了地上。不过,从老树干上抽生的新根和枝条和一位更加热忱的主人,让它再一次享受了名利双收。
既然苹果树兴盛和倒下的速度都如此之快,我们也许会认为它们繁殖起来也很快。实际上,很少有苹果树是从种子长成的,因为苹果树作为杂合子,幼苗一般会和亲本大不相同。
尽管玛丽·安·布雷斯福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用种子培育的树不太可能长成一棵健康的、能结果的成年树,这是我从自己在少年时代做过的一项园艺试验中发现的。以极大的热情种下一些苹果核之后,我看着它们先长成漂亮的小树苗,然后逐渐变得发育不良,扭曲变形,与其说是树,不如说是对树的拙劣模仿。的确有一棵活到了成年,但它绝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挺拔直立、硕果累累的树。
更有经验的种植者知道,繁殖苹果树的最佳方式是从健康的树上切下接穗,也就是很小的一段树枝,然后将其嫁接在砧木上。通过不同品种的杂交,不断地培育出苹果的新品种。属于保罗·巴尼特的那棵了不起的苹果树在2013年登上了新闻,因为它上面生长着250种不同的苹果,全部都嫁接在它好客的枝条上。这顶茂盛得令人震惊的树冠缀满了鲜艳的果实以及标明每个品种名称的长三角形小彩旗,重得几乎让树干承受不住,所以每根分枝都有一根棍子支撑着。于是,在这棵繁茂的苹果树下出现了一团奇特的、有棱有角的阴影。
苹果树绝不是英国文化中永恒不变的一部分,恰恰相反,苹果树一直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莎士比亚曾经享用过一种古老的带肋纹的苹果,名为“考斯塔德苹果”,然而等理查德·考克斯在1820年彻底放下自己的酿酒生意,开始在斯劳附近的庄园里专心栽培苹果时,这种考斯塔德苹果已经基本灭绝了。
和大多数著名苹果树的命运一样,考克斯的第一棵“橙皮平”苹果树在1911年被吹倒,但与此同时,对这些美味的甜点苹果的需求已经巨大到让它有了许多繁茂生长的后代。不同苹果品种的陈列很可能像是一场家庭聚会,“斯特默·皮平”大概是“里布斯顿·皮平”苹果和一种无双苹果的杂交后代。
苹果种植不分贵贱,同时在村舍花园和大庄园里蓬勃发展。“布莱尼姆橙”这个品种虽然名字很高贵,但其实是牛津郡的一位劳工最先培育的。除了果园之外,你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见到“掷弹兵”“德文郡公爵”“兰伯恩勋爵”“伯利勋爵”“威尔士亲王”“安妮·伊丽莎白”“威廉·克伦普”“威尔克斯牧师”和“澳洲青苹”(字面意思是“史密斯老奶奶”)亲亲热热地凑在一起呢?(不过英国果园里的“澳洲青苹”也许味道很酸,因为它需要澳大利亚的阳光变甜。)
除了这些充满智慧的精心栽培,幸运的发现也一直存在,比如“贝丝·普尔”这个品种就是以一位客栈老板的女儿命名,有一天她在森林里发现了这棵树苗。苹果的历史充满艰苦奋斗和偶然事件,但也不乏某人在一棵不起眼的年幼苹果树上发现潜力的故事。苹果的品种名也充满了背后的故事,但是要当心,“亚当斯·皮尔曼”与全世界第一名园丁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以罗伯特·亚当斯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如果你认为“牛顿奇迹”和艾萨克爵士有某种关系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它最先由德比郡的国王牛顿栽培。
所以关于苹果树,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自然”的东西。就连它们成熟的轮廓也常常是人造的。人们喜欢给苹果树整枝,好像只要有一点耐心,它们就能学会一两招似的。不过,还真说对了。被技艺纯熟的双手整枝之后,这些苹果树可以呈现出最令人吃惊的形状,比如金字塔、葡萄酒杯、V形臂章或孔雀尾巴。墙式苹果树的分枝像巨大的绿色跷跷板一样从中间向外伸展,这种整枝方式的名字来自“肩膀”这个单词,因为这些过大的枝条长到肩膀的高度时最需要支撑。整枝并不纯粹是为了追求新奇的形状,还让采摘变得更容易,确保果实生长得更均匀并被阳光充分照射,以实现全部着色。
03
苹果也意味着健康、维持生命
苹果一直是一种基本的、价格可以承受的食物,无论是直接从树上摘下来生吃还是加入馅饼、泡芙、琥珀苹果派或意大利面点中烘烤。在英国,过去那些买不起炉子的人常常将苹果菜肴带到当地面包房去烹饪,这些菜肴需要做好标记,以免有人因为拿错而大动肝火。就连味道发苦的野苹果也是季节的馈赠,它们来自美丽的本土野生苹果树,可以做成果酱搭配三明治或者肉类菜肴。
我小时候在9月末放学回家时,总是能闻到果酱的气味,我的母亲正忙着煮野苹果,将黏稠的暗粉色胶状物慢慢地从自制果酱过滤袋里挤出来。这个过滤袋的前身是一个旧枕头套,紧紧地绑在一把翻过来的曲木餐椅腿上,吊在半空中。苹果富含果胶,这是素食者最喜欢的凝胶剂来源,所以野苹果果浆很容易在罐子里凝固成半透明的日落色。苹果果胶还能帮助西梅、黑莓和绿番茄定形成果酱和酸辣酱。
苹果派
催熟番茄的古老方法是将一只苹果放进一袋番茄里,这应该是很有效的,因为苹果天然地会释放一种植物激素——乙烯。然而,某些苹果品种对人类有相反的作用。一个珍稀的瑞士苹果品种的干细胞,如今已被用于刺激人类皮肤的生长和减少皱纹。研究人员还在探寻苹果预防某些癌症和血管疾病,以及抗老的功效。
每天一个苹果也许会成为21世纪的处方药。拥有光滑的脸庞和没有病痛的身体,这个梦想就是青春永恒国度的现代版本,而苹果仍然挂在那里,启发我们进入天堂的新方法。当那些人将削下来的苹果皮从肩膀上方扔到身后,想要以此得知未来配偶的姓名首字母时,谁会想到这些苹果皮后来会被发现含有抗癌化学物质三萜烯化合物呢?
健康、维持生命的苹果也许看上去很英国化,但这种结出可食用果实的树是随着罗马人进入英国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种植了甘甜的果园。苹果也是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基础,不仅仅针对纽约人(译者注:纽约的绰号是“大苹果”)。
传奇的“苹果籽约翰尼”将他的苗圃种遍东部各州,建构了强壮、健康、辛劳工作的美国典型农民的神话,对于充满母爱和苹果派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然而通过追踪苹果的基因组,我们现在知道世界上所有被驯化苹果的祖先都是新疆野苹果,这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本土物种。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的意思是“苹果之城”,而生长在周围山坡上的古代野生果园可能很快就会被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地。
苹果籽约翰尼
如今,世界苹果地图一共标记了数千个品种,这张地图还记录了消费者趋势的变化。随着人们口味的变化,商业水果作物也会随之改变。如今在英国最受欢迎的苹果是来自新西兰的“嘎啦”,味道很甜。令人兴奋的果味起泡酒最近正在流行,推动了大规模的植树计划。我们也许会想到更传统的苹果酒酿造商,推着他们漂亮的榨汁机从一个果园走到另一个果园,将夏天的最后一点汁液挤压出来,而在汗味和成熟的苹果气味都很浓重的谷仓里,摘苹果的工人领取的报酬是苹果酒,这对他们加快工作节奏毫无帮助。
相比之下,现代水果种植成为高度商业化且非常高效的机械化产业。2012年,国际竞争导致欧盟出台了保护特殊地区性产品的新律,于是作为指定产品的“赫里福德郡苹果酒”只能用当地产出的带有苦味的苹果汁酿造,例如“棕鼻子”“布尔默的诺曼人”“凿子泽西”或者“金斯顿黑”。这些品种不太可能和法国的酿酒苹果混淆,不过“布尔默的诺曼人”提醒我们,英国苹果和法国苹果拥有共同的血脉。
口味的变化和商业上的压力意味着很多古老的、名字饶有趣味的品种已经在英国消失得差不多了,不过如今人们正在努力保存传统果园。伦敦不太可能是苹果倡议的发起地,但是在1999年10月,这座城市举办了第一个“苹果日”。在令人兴奋的几个小时里,英国慈善组织“共同立场”重用了科芬园,该组织致力于恢复商品和自然界的联系,并强调地区特异性。
“苹果日”旨在通过举办这样一个令人想起老英格兰和已经快要被遗忘的民间节日活动,提高人们对果园的爱护意识。这是水果种植者的节日,是为那些喜爱乡村生活图景的人,以及吃健康食物、渴望更亲近自然的人举办的。
“苹果日”是新时代的圣乔治日,来自所有政治派系和社会阶层的人每年都在这一天欢聚一堂,享用苹果派和苹果酒。丰富的苹果品种成为地区特色和共享精神的完美象征,所以这个节日如今在全国遍地开花,但具体日期因为当地品种和采摘时间不同而略有差异:在威尔士中部的赖厄德附近是9月中旬,在苏格兰边境是10月初。就连被砍倒的苹果树木屑也加入到节日中来,用于烹制苹果风味的烧烤。
而那些对所有素食摊位以及强调自然健康、表面撒了苹果籽的“苹果奶酥”不那么感兴趣的人,会爱上用苹果木熏制的培根。如此大胆的传统创新也许会引来质疑的目光,但也会让人钦佩苹果种植商们敏锐的市场眼光,以及他们提醒现代消费者日常饮食从何而来的决心。
04
盛夏的果实,预示着日子会好起来
在孩子们的眼中,苹果已经和计算机产业密不可分了,但在这种与果树同名的电子产品的帮助下,他们能够看到克什米尔或者智利的苹果采摘工人,从而去思考超市架子上干净漂亮的六个装苹果中投入了多少劳动力。一只苹果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建立了直接联系。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前,来自这个国家的“澳洲青苹”在欧洲的很多地方并不受欢迎。
不过有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在果园里工作的人而言,抵制水果的行为到底是在帮助他们还是在损害他们的利益?从非电子产品的苹果中,仍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一棵苹果树下停留一小时,不仅播撒了农民和园丁的种子,还在培养将来的植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商业巨头。
苹果公司logo
当你在一座真正的果园里看到生长的苹果时,就不难理解这种放在冰箱里的水果了。只需要轻轻扭动一下,就能判断一个苹果什么时候可以采摘。如果它已经熟了,果梗会自动松开,让苹果从树上脱离下来,被你稳稳握在掌中;如果没有在合适的时候采摘,苹果就会像板球一样倾泻而下,并在落地时砸出瘀伤。它们常常会隐藏在长长的草丛里,静静地等待着,直到有人感受到脚下踩碎了一团棕色的黏糊糊的东西。
这些树提供了探索自然的方式,还能与我们的所有感官对话。我们可以触摸粗糙的树皮,闻到成熟果实的气味,倾听蜜蜂嗡嗡作响或者啄木鸟在枯枝上敲打的鼓点。古老的果园是某些最稀有、最漂亮的物种的天堂,虽然大冠蝾螈或者金龟子可能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一只小小的棕色旋木雀可能正在树干上慢慢地爬上爬下。在9月的某个被月光照亮的夜晚,甚至还能看到一只獾弓着浅色的背正在吃掉落的果子,或者一只狐狸伸出长长的、优雅的嘴巴,去咬较低树枝上的果实。
当然,苹果树的魅力不只出现在秋天。在凡·高眼中,重要的是苹果花,最其貌不扬的畸形树枝突然变美,意味着创造力。颜色浅淡、像羽绒一样轻盈的花瓣骤然开放,美丽得令人窒息,能够为最粗糙多瘤的老树披上光辉灿烂的云霞。稍早之前,当黎明开始降临时,你似乎能看见这些树打起哈欠,伸展躯体,摇醒一根根小枝。树上的芽一开始好像有点不确定,但它们不顾霜冻挥之不去的威胁,渐渐地点亮了每一根枝条,就像一个睡眼蒙眬的微笑绽放成一个灿烂却坚定的笑容。这种换季的骚动被呈现在c中,在明亮的碧绿天光下,蝴蝶般的花朵仿佛在和扭曲的小枝一起翩翩起舞。
《静物与苹果》,梵高
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Pissarro)一次又一次地描绘皮卡第的苹果树,无论是春天的灿烂换装、夏天的郁郁葱葱,还是冬天赤裸裸的剪影,都让他深感敬畏。春天棉衬衫般的雪白与秋天温暖而斑驳的杏黄和深黄一样有气氛。毕沙罗那以苹果为中心的世界是一首忙碌中的田园牧歌,重点是弯曲的树枝和沉重的独轮车。但在法兰西岛大区周围的田野中,这些非常独特的果树是真正的地域特征。
当英国战地画家保罗·纳什在1917年抵达法国北部时,景色完全不一样了。他在壕沟里给妻子写信,描述一座法国村庄被战火摧残之后的样子,“在鲜艳的树木和剩下的果园里,到处都是成堆的砖块、被掀翻的屋顶和只剩下一半的房子”。纳什描绘了被破坏的果园,在惊人的画面中,树冠被炸飞,树干的轮廓好像玻璃碎片,苹果树变成了黑暗、扭曲的形象,无助地伸向太阳。他笔下这些情感充沛的画作最有力地表现了“一战”造成的绝对恐惧,并且有赖于人们对苹果树真正意义深刻的共同理解。
这是一种本应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安静生长的树,让这些地方的新一代年轻人采摘、吃掉或者喝掉它们的果实,就像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一样。苹果树是生命之树,但它也是智慧树,令人辨明善恶,结出人类无法抵挡、不计后果去占有的果实。被毁的果园展示了那些幸存下来的震弹症患者无法言说的东西。在这丑陋、荒芜的废墟中,还能有什么新的开始?
尽管如此,世间仍然存在着一种重获天堂、重新开始的深刻而永恒的欲望。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出生于1914年战争刚刚爆发之后,但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时,他记得自己在“苹果树下,年少悠哉”地度过了田园诗般的童年,“心中快乐悠长”。在这里,苹果树没有受到责备,它在逝去青春的永恒光辉中闪耀。当这位诗人在1945年写下这首诗,留恋地回顾自己成为“苹果镇王子”的早年时光,他已经清楚地意识了时间的锁链。
《罗西与 苹果酒》,[英] 洛瑞· 李著,朱岚岚/周易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罗茜与苹果酒》是劳里·李(Laurie Lee)20世纪20年代在科茨沃尔德那段童年时光的回忆录,书名来自他第一次品尝苹果酒的体验:“那些山谷、那段时光的泛着金色火光的汁液,这酒的滋味来自野果园,来自红褐色的夏天,来自饱满的红苹果,还有罗茜滚烫的脸颊。”这是一段生动的个人记录,不仅有童年,还有在天堂生长的醉人的苹果。战后出生的人依然展示着对伊甸园、对重获青春与纯真的相同冲动,不管有多大胜算,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不管四周是怎样的废墟,都要重新开始。
1939年,战争再次撼动了欧洲,但在枪声和空袭警报中,人们继续静悄悄地种植果树,收获果实。艾德里安·贝尔(Adrian Bell)的《一英亩的苹果》记录了闪电战中萨福克郡的一座小农场,也证明了苹果充满抵抗力、永葆青春。随着战时配给制的实施,自家种植的水果变得对生存至关重要,而能够维持生命的苹果也拥有了特别的价值。当英国人被困在冰雪中、徘徊在未知的地狱边境,从储存箱里取出的苹果会比它们刚装进去时更红更艳。这些闪亮的果实令人想起盛夏时光,也预示着日子将会好起来。苹果树意味着起点、童年和伊甸园,但也意味着启蒙、经历和未来。如果说苹果树常常因为人类的不幸而遭到责备,那么这种树还拥有继续生长并让我们重新开始的非凡能力。
本文节选自
《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
作者:[英]菲奥娜·斯塔福德
译者:王晨/王位婷
出品方:未读·探索加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9-5
编辑 | 白羊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