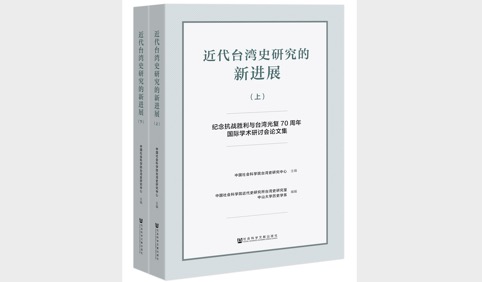失望的取经之旅:梁启超在辛亥年间的赴台游历
近来,许知远出版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传》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35年后重返话剧舞台,亲自演绎《梁启超和他的九个儿女》;作家解玺璋也再版了《梁启超传》,梁启超再度重回大众视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中,收有樊学庆的《失望的取经之旅》一文,厘清了梁启超在辛亥年间赴台考察的立宪考察之事,今日获出版社授权刊发。
撰文| 樊学庆
宣统三年,梁启超携好友汤叡(觉顿)、女儿梁思顺(令娴)赴台游历。二月二十四日(1911年3月24日)从日本出发,二月二十八日(3月28日)由基隆登陆,三月十三日(4月11日)离台返日,在台共逗留两星期。对梁启超此次赴台之行,学界研究较多。
不过,已有成果集中于台湾史研究领域,多以梁启超与台湾关系为中心,着重考查梁启超游台过程、与林献堂等台湾遗民的交往、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认识,以及梁启超对台湾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等方面之影响。对梁启超此次赴台考察的重要目的——为当日清廷预备立宪寻求参考、借鉴,并为自己归国从政做准备——学界关注较少。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转换视角,以梁启超与清廷预备立宪、政局变化关系为中心,尝试对宣统三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再做解析。
一、梁启超赴台考察的动机
对于梁启超赴台游历的动机、目的,学界主要观点认为,一是考察日本治台实际情形,二是为在国内办报和建立国民常识学会筹集款项。针对这两点内容,梁启超在赴台前后的信札中多有陈述。不过,当时梁启超赴台考察,目的并不仅在这两个方面。
赴台期间,梁启超致《国风报》编辑部第一函中说:“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咸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辨之,此兹行所以益不容己也。”读此可知,了解日本治台“成绩”确实是梁启超访台的一个重要目的。然而,梁启超随后又在信中详细开列了十条调查事项:
一、台湾隶我版图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自刘壮肃以后乃渐加至二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万矣。是果何以致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二、台湾自六年以来,已不复受中央政府之补助金,此四千余万者皆本岛之所自负担也。岛民负担能力何以能骤进至是?
三、台湾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补助数千万金,又借入公债数千万金。就财政系统言之,则台湾前此之对于其母国,纯然为一独立之债务国,今则渐脱离此债务国之地位矣,此可谓利用外债之明效大验也。吾国外债可否论,方喧于国中,吾兹行将于兹事大有所究索。
四、台湾为特种之行政组织,盖沿袭吾之行省制度,而运用之极其妙也。吾国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议,方哓哓未有所决,求之于彼,或可得师资一二。
五、吾国今后殖产兴业,要不能不以农政为始基。闻台湾农政之修,冠绝全球,且其农事习惯,多因我国,他山之石,宜莫良于斯。
六、台湾为我国领土时,币制紊乱,不可纪极,日人得之初改为银本位,未几遂为金本位。其改革之次第如何,过渡时代之状态如何,改革后之影响如何,于我国今日币制事业必有所参考。
七、日本本国人移殖于台湾者,日见[渐]繁荣。今日我国欲行内地殖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诸地,其可资取法者必多。
八、台湾之警察行政,闻与日本内地系统不同,不审亦有可以适用于我国者否?我国旧行之保甲法,闻台湾采之而著成效,欲观其办法如何。
九、台湾之阿[鸦]片专卖事业自诩为禁烟之一妙法,当有可供我研究者。
十、台湾前此举行土地调查,备极周密,租税之整理,其根本皆在于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扰?又,其所行之户口调查,系适用最新技术,日人自夸为办理极善。今者日本本国将行国势调查,即以为法,欲观其实际详情如何。
这十条调查事项中,第一、二条从宏观考察台湾经济实力增长;第三、五、六条为外债、农政、币制等具体经济政策,第四、七、八条涉及外官制、边疆殖民和警察、保甲等行政管理方面。第九条禁烟是预备立宪后清廷大力推行,关涉吏治、财政、外交等诸多方面的要政,第十条土地、户口等国势调查则是为制定改革政策提供依据的基础性工作。
可以看出,这十条调查事项都是当时清廷预备立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梁启超考查这十个方面,以及前述探究治台实情,目的都是了解日本治台政策及其影响,观“其改革之次第如何,过渡时代之状态如何,改革后之影响如何”,为清廷宪政改革寻求可资参考、取法之处,“或可得师资一二”。
实际上,梁启超赴台前后曾多次表达这一想法。光绪三十三年林献堂在日本奈良拜会梁启超,顺便邀梁访台,梁启超回应“早有此想”。“因曾闻后藤新平说台湾如何进步,极事铺张,且云非如李鸿章所谓台人强悍难治也,果如后藤所说,将来或可为我国借鉴。”宣统三年一月即将访台之际,梁启超在致林献堂信中又说:“缘既作此游,辄欲于彼都人士之施政详细察视,以为警策邦人之资。”
游台期间,为应对《神州日报》等上海报纸的攻击,梁启超发表公开信,澄清自己访台动机:“夫吾数年来,欲往台湾之本意,则固在调查其行政也。顾欲举其美者,以告我国人也。”在致编辑部函中也说:“吾兹游本欲察台湾行政之足为吾法者,而记述之以告国人。”可见,梁启超自始就将为清廷立宪寻求参考、借鉴作为自己赴台考察的重要目的。
不仅如此,就当日梁启超所处时势环境而言,其赴台考察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更“有所图”。这与其预备立宪后的政治思想、态度密切相关。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避居日本,一度深信“破坏主义”,提倡“革命排满”。光绪二十九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归来后主张大变,“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足以误国也,乃一意反而守旧”,自是“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梁启超虽身居海外,但与其师康有为一样密切关注国内形势。一面积极发表言论、筹组政党,培植立宪势力,一面隐交清廷权贵,力图在清廷上层贯彻其主张。用其好友黄遵宪的话说,即“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当逃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寸,曰辟首击尾,曰远交近攻”。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间,梁启超与端方等人联络,为其起草考察报告、奏请立宪等折“凡二十万言内外”。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更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
《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在一系列宪政改革中,梁启超首重政治建设。在《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中,梁启超向清廷提出五条“致治大原”:“上议院之组织宜参酌各国,务求完备”;“司法权宜独立,而最高之行政裁判当委诸议会”;“宜定责任内阁之制,以长保皇室之尊荣”;“地方自治范围宜加扩充,务求完备”;“将来改正宪法之规则,不可不早定”。
光绪三十二年筹组帝国宪政会时,梁拟定“尊崇皇室,扩张民权”,“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等纲领。宪政会改组为政闻社后,梁启超在宣言书中提出四条主义:“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除了政治纲领外,梁启超对宪法、责任内阁、国会、地方自治、官制等具体制度建设也极为注意,先后撰有《责任内阁与政治家》《外官制私议》《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文章详加探讨。
除政治之外,梁启超关注的另一重点是经济问题。甲午战后,战争损失和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陷入困境,庚子再创更是雪上加霜。这使梁启超对财政问题日渐关注。光绪二十六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日人松冈忠美的《论清国财政改革之急务》,指出清廷再不大革新其财政,“假使即能逃灭亡于今日,而异日亦必因财政以自灭也”。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随着各项新政推行,财政瓶颈日益凸显,梁启超对经济问题也愈益重视。
光绪三十四年底,梁启超上书摄政不久的载沣,指出“今日中国财政之困急,环球莫不为我危,苟长此不理,则虽无内忧外患,而国家且将以破产终矣。况一切新政皆待财而行,财政不整,百事束手,国家更安有进步之望耶?”宣统元年八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慨叹清廷亡国之象日现,“若其速亡之显因,则必以国民经济问题,毫无疑义,此问题能挽救与否,即决于此十年中,过此以往,永沉九渊耳。此真可为股栗者也”。
为此,宣统元年、二年间,梁启超先后撰写《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论地方税与国税之关系》《国民筹还国债问题》《再论筹还国债问题》《偿还国债意见书》《论直隶湖北安徽之地方公债》《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币制条议》《外债评议》《改盐法议》等文,着重从税收、债务、币制、盐法、财政体制等方面寻求解决财政困境之道。在此前后,梁启超还撰《财政学》一书,“可得百万言,洵为疗国之秘方”。
除研究撰著之外,梁启超多方联络清廷权贵,为宪政改革出谋划策,充当顾问。除袁世凯、端方等清廷重臣,梁启超还努力结交奕劻、善耆、载泽等亲贵,甚至准备推举载沣出任其筹组的帝国宪政会总裁。慈禧、光绪去世后,梁启超又因应清廷政局变化,积极联络得势的少壮亲贵。对主政中枢的载沣兄弟,梁启超劝导他们从全局入手抓住根本要政。梁启超上书摄政王载沣,指出“居今日而言宪政,必统筹全局,百废同时并举,庶几有济,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将并此一枝一节而不能有功而已。此则愿殿下于大部官守之外而更有所留意者也”。理财政、改官制、厉人才等为诸宪政“根本之根本”。开地方长官会议,整齐施政方针,举中央集权之渐;实行调查国势,择地试办,以次遍及;速制定地方自治制度,颁布实施,养成国民参政之习惯等三项为“一切宪政之基”。“根本不立,而枝叶能荣,未之闻也”。
宣统二年,梁启超又上书贝勒载涛,指出“古今中外之治国者,莫急于统筹全局,纲举然后目张”。改革的全局纲领之举,首在从官制入手,改革行政机关,“于整饬纲纪、澄肃吏治之道,痛下一番功夫”。次在统一财政,并“将财政机关从根本以改革”。对掌政一方,对清廷政局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亲贵,梁启超也尽力就其执掌范围建策献议。宣统元年二月,梁启超应民政部尚书善耆之请,详论作为新政基础的户口调查问题,指出“今后无论欲举何种新政,皆须经一次详密之国势调查,然后得精确之资料,以供斟酌损益之用”。又顺道论及与调查密切相关的财政改革,指出“中国财政若机关改良,办理得法,则求岁入数倍于今日,殊非难事,所最困者,非大改革行政机关,则财政之整理,终不可期;而欲改革行政机关,目前便先需一巨款,此实政府两难之道”,解决之途在于发行内债。
1910年载涛(前排左二)访问俄国
宣统二年,梁启超将积历年所得撰成的《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十万言托人上呈度支部尚书载泽。分田赋、盐课、税目、预算、公债、货币、银行、财务行政、地方财政和八旗生计等12篇,详述财政改革方法,并提议对财政系统彻底改造,“与其因循旧弊,年复一年,上下交病,何如乘预备立宪之始,为一劳永逸之计”。其撰著《财政学》一书,也是希望能有所“见用”。
除拉拢权贵,梁启超又通过徐佛苏、潘若海等人广泛联络国内其他立宪各派,筹组政党、举办报刊,宣传、贯彻其主张,指导立宪各派议员通过谘议局、资政院等机构推动清廷改革。
尽管梁启超对预备立宪寄予厚望,推动改革不遗余力,但连续的挫折令梁启超一再失望。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清廷厘定内阁官制,梁启超颇为不满,“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此后,政闻社案、诛袁、促开国会运动等事连遭不利,梁启超由此对国内局势和朝野立宪力量极为失望。
宣统元年八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感叹“国事每下愈况,中央政局既无以异于前,而其尤可痛者,在人心风俗之一落千丈,欲求两三年前之气象,渺乎不可复得。西哲言代议士为国民心理之影象。现在谘议局议员,既略写此影象与我辈以共见矣,将来忧患曷其有极?”“弟入春以来,专务养晦,国内交通殆于断绝,非敢取消极主义,良以天下事往往愈急则愈缓,愈即则愈远,且亦见当道中实无一可语之人,故毋宁任其所之之为得也。”
尤其是被梁启超等人视为“今日吾党之生死问题”的开放党禁案。其间,载泽出乎意料的反对,就使梁启超一度陷入内外交困境地。宣统二年底,开禁案最终失败,使梁启超及其同志与各派力量间形成深深隔阂。当时负责在京运动的何天柱,曾向梁启超历数反对诸人:“(都中)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造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其赞成,而阴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郑、汤、张三名士也;之数党者,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向龙寓提议此事,答言: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
连续的挫折、失败使梁启超感到,要想将自己的政见主张付诸实行,必须自己出山,亲力亲为。清廷宣布内阁官制后,梁启超就在致蒋智由信中提出:“谓国民复无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此诚可痛,然弟以为练成此能力,正我辈之责也。我辈在国民中宜多负责任者,今不自为之,何以望人。”宣统元年五月,梁启超在致梁仲策信中称:“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宣统二年二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再次重申这一态度:“弟昨日见一极要之人,述都中政界实状甚悉(所谓宪政改革云者),诚无复一线希望,然弟终不以此自沮。盖弟向来不望政府,若民间能有希望与否,则此责仍在吾辈耳。”
1911年台中栎社诗人欢迎梁启超访台的纪念照,其中多人仍留着前清发式
然而,要将自己的政见付诸实行,仅仅理论探讨是远远不够的,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深为明了。“虽按诸学理,或无剌谬,而可行与否,则全与学理无涉,而当以本国情形为断。”梁启超常年居住海外,对国内情形相当隔膜,其政策理论虽多借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经验,但日本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却未可知,尤其是梁启超从未任事,缺乏执政经验。这些都是其出山执政的巨大障碍。
而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殖民统治恰好为梁启超提供了一个急需的、可以验证自己理论的试验场。日本治台不过十余年,面貌幡然一变。日本如何将本国经验推行于台湾,迅速改变台湾面貌,其中原因为何,不仅引起梁启超极大兴趣,也增强了其对中国实行宪政的信心。“日本能行之于台湾,且当三十年前能行之于其本国”,“而谓我国万不能行,则是我国终为人役也,而岂其然哉”。正因如此,预备立宪后梁启超对日本治台经验也多有参考,甚至提出聘请曾任职台湾的日本殖民官吏为中国培养宪政人才。
开放党禁案的失败,使梁启超回国执政计划遭到重大挫折,但亦有收获。开禁案中,梁启超获得载沣兄弟的大力支持,“解禁之议,洵、涛争之不下十次”。载沣也是因宫廷、朝野压力不得而已否决开禁案,“孰谓周公无意乎”。因此,开禁案失败后,梁启超等人继续运动。在国内,梁等人一方面“以谋吉甫为上策”,准备行贿奕劻疏通宫廷;一方面借助载涛支持掌握军队。“数月来,惟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治吴禄贞……为我用”,尤其“以全力抚循禁卫军,使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辈而廓清之”。在海外,梁启超自己也为回国从政加紧准备。将梁启超拟定的赴台调查事项与预备立宪后梁启超的研究思考相对照,可以看出,这些事项大都是梁启超规划的清廷宪政改革的核心工作,也是其组阁执政后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所以,梁启超辛亥台湾之行,除了解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实情和筹募款项外,还怀有一个重要目的——为宪政取经:既为清廷立宪寻求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亦为自己“归而执政”做好准备。
二、梁启超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态度的转变
关于梁启超赴台游历过程和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认识,学界已有较详细梳理。但梁启超对日本殖民统治态度转变的前后过程,学界研讨不多,而这一问题正是梁启超辛亥赴台失望而归的关键。本节即就此问题略作论述。
梁启超访台蓄志已久,期望亦大。光绪三十三年在奈良会见林献堂后,梁启超便已计划东游。所以,宣统三年赴台之际,梁启超说:“兹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践。”后来回应《神州日报》攻击时,又再次申明“吾游台之志,以蓄之数年,凡稍与吾习者,谁不知之”。在此期间,梁启超对日本治台经验日益重视,《上摄政王书》和呈递载泽的《中国改革财政私案》中都一再提及借鉴日本治台之策。而清廷推行立宪的无能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困境,更使梁启超探究日本治台奥秘的要求倍加迫切,其详细开列的十条考察事项可谓这种心情的一个体现。尽管诸事缠身,行期一再推延,“几止者且屡”,梁启超仍下决心赴台,“毅然排万冗以行,首涂前盖数夜未交睫也”,其迫切心情于此亦可见一斑。
林献堂邀梁访台时,曾告诫梁启超行前“必请日本中央政府显要为先生绍介,盖日人深忌我们与祖国人士之接触”。梁启超虽按林的提醒开具介绍书,但对“日人深忌”一事似乎并未十分在意。基隆登陆时,日本警察刁难也未使梁启超全然改变态度。入台第二天致《国风报》编辑部信中虽道及警吏刁难事,但仍一面兴致勃勃地讲述旅途感受,“沿途水波不兴,虽深畏海行如明水先生者,亦饮啖胜常,致可喜也。前日舟略温台界而南,遥望故国,青山一发,神往久之”;一面对日本航运事业赞叹不已,“舟中设备极新,娱乐之具毕陈。日本人航海事业之发达可惊也”。
不过此时,梁启超的态度已在悄然变化。“舟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日本警察的苛刻盘查和阻挠使梁启超认识到,日本对台殖民统治与自己在日本国内感受到的全然不同。“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日本)十年而无所知,真梦也。”
接下来的种种遭遇,更使梁启超愤懑不已。“虽时日尚浅,然已起种种异感。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不虚也。”梁启超与前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有旧,又持有日本高层介绍信,因而赴台后首先拜访总督府,结果不仅三谒不得见,还倍受羞辱。“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立宪国之君主,视之蔑如矣。其官吏别有一种习气。居日本十年所不能睹也。吾至此不得不以礼往谒,乃适如昔人所谓因鬼见帝者,殊可一笑。三谒不得要领,卒辞以疾。殖民地之官吏,如是其尊大也。犹谢其派一通译官为向导,乃得遍历诸局所调查,获种种便利,此莫大之人情耳。”
出乎意料的羞辱、冷遇使梁启超深深感受到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尊卑宠辱的霄壤之别,丧权失地的痛苦、无奈。“刘壮肃公所营故城毁矣。留其四门以作纪念。今屹然于西式垩室与东式木屋之间,日过其下,刿心怵目。故抚署今为总督府,吾曾入之,归而累欷。”后来,梁启超回顾登岛前后的经历时,仍哀愤交加,“此次之行,乃不知托几多人情,忍几多垢辱,始得登岸。而到彼以后,每日又不知积几多气愤”。
三月初三日(4月1日),瀛社邀集百余人在台北故城东荟芳楼为梁启超访台大设欢迎会。会场内外日方暗探密布。据日方记载,梁启超在宴会前称“发现(台湾)在所有方面均有进步,而且政府治理良好,超出想象之外”。宴会上,又对与会诸人致辞:“诸位原是清国臣民。……(日本)领有(台湾)以后,日本政府抚爱人民,无论交通产业振兴,工业和其他种种设备,施行得当,没有遗憾。诸位如不心服,那是错误的。台湾人即是诸位,假如父母有小孩,但没有养育其小孩的能力,就给与他人,此时小孩表明不心服,那是不对的。对待养父母像对父母一样尽孝顺,应该是当然的。表示不满意是不孝顺的。诸位把日本政府也当作养父母,诚心诚意地跟随它,这是当然的。我漫游各殖民地,而且熟悉其情况。台湾是一个殖民地,从世界上殖民地的情况来看,殖民地一般受支配国的虐待,然而日本则一视同仁,对待诸位跟(日本)内地人相同,受到内地人一样的待遇。但重要的高等官还不能由台湾人出任,很可能有人为此表示不满意。那是因为台湾人的脑筋还不够的缘故。要紧的事是要造出其头脑。意大利曾把匈牙利作为保护国,匈牙利人觉得很遗憾,很用功而且达到和意大利同等的文明,终于作为自治团体亲自进行治理。假如台湾人也用功的话,达到跟日本人同等的地位,亦未可知。所以自己用功的话,重要官员很可能也由台湾人出任。因此盼望诸位尽量不发牢骚,诚心诚意,忠实行事。希望诸位作为日本臣民越发勤奋。”完全是一篇对日本殖民统治赞叹有加之辞。
然而,私下里梁启超却是又悲又愤,虽“怀抱无量数深痛隐恨”,然而迫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威胁,“而为遗老计,投鼠忌器,犹不敢尽以形诸楮墨”,只能做口是心非之语,“吾席间演说之辞,真不知如何而可。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耳”。诗词中也只能隐隐寄情,“尊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料得隔江诸父老,不缘汉节始沾衣”。面对怀念故国、相待有加的遗老们的盛情款待,梁启超忿愧满怀,“自顾何以当此”。心情已不只是“枨触万端”,而是“怀抱殊恶,不磬百一”了。
自此,原本一心要到台湾学习先进经验的梁启超,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态度幡然一变。“吾兹行乃大失望。台湾之行政设施,其美备之点诚极多,然此皆一般法治国所有事耳,不必求诸台湾也。吾所为殷然来游者,徒以台湾居民,皆我族类。性质习俗,同我内地。欲求其制度之斟酌此性习而立者,与夫其政术之所以因此性习为利导之者。吾居此浃旬,而不禁废然思返也。台湾之足称善政者,则万国之公政,无论措之何地而皆准者也。”日本大事宣扬的在台建设成绩,不过是在刘铭传已有基础上的发扬光大,并非日本独创。“刘壮肃治台六年,规模宏远,经画周备。后此日人治绩,率袭其旧而光大之耳。鸡笼至新竹间铁路二百二十余里即壮肃旧物,其他新辟容辀之道尚数百里,鸡笼、沪尾、澎湖诸炮台皆壮肃手建,台北省城亦壮肃所营。”即便日本引以为地豪地剿平“生番”,也是沿袭刘铭传之策。“日人顷方锐意犁扫生番,广张所谓隘勇线者,蹙之于丛箐中,战略与名称皆袭刘壮肃之旧也”。那些真正为台湾独有的特别措施,“若夫台湾特有之施政为日本内地及他文明国所未行者,斯则非直吾国所能学,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
这些中国不能学、梁启超不忍言的日本特有之施政,即日本在台实行的殖民剥削、压迫政策。有关梁启超对日本殖民政策的揭露、批判,学界已有较详分析,本文仅就梁启超感触最深的三个方面做一简述。
第一,以所谓“公益”为名,低价强征台民土地、房屋等财产。“台湾自有所谓土地收用规则者,与日本现行之土地收用法迥别。凡官吏认为公益事业所必要者,得任意强取人民之所有。而所谓行政诉讼、行政诉愿者,绝无其途”,其较著者为斗六厅事件。宣统元年,殖民政府以建立糖业会社为由,派数百警吏包围斗六厅农民,强迫其低价出卖世守田亩,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饿殍阗路歧”。此外诸如借讨生番之名强迫农民垦殖、借市政建设之名强拆民屋等事所在多有。梁启超指出,“其他类此者,月有所闻。台湾人之财产所有权,固无一时可以自信自安也”。
第二,实行愚民教育。殖民政府办有高级学校,台湾人民不能进入。“此间有良校,贵人育其英。岛民贱不齿,安得抗颜行”,只能接受年限短暂、质量低劣的所谓“公学校”教育。“别有号公学,不以中小名。学年六或四,入者吾隶萌。所授何读本,新编三字经。他科皆视此,自郐宁足评”。对此,殖民政府还振振有词。“莫云斯学陋,履之如登瀛。学途尽于斯,更进安所营。贵人豢我辈,本以服使令。岂闻扰牛马,乃待书在楹。汉氏厉学官,自取坏长城。秦皇百世雄,谈笑事焚坑”,学校的教育管理,“更有意想所万不及者”。对这种“更如儿戏”的殖民教育,梁启超指出其真意在愚化台湾民众,“要之,台湾识字之人本少,更十年后,则非惟无识中国字者,亦将并无识日本字者矣”。
第三,控制台湾经济命脉,残酷剥削台湾人民。台湾一切日用品无不来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屐及草履,所食之面及点心,皆然。举其小者,大者可推矣。中国货物,殆杜绝不能进口,保护关税之功用,其可畏有如此者。台湾本绝无工艺品,而中国货则税率殆埒其原价。其舍日本货外更无可用亦宜。而日本货之价,亦远贵于日本本境。以物价比例于劳庸,则台湾物价之昂,盖世界所罕见也。以故台湾人职业虽似加于昔,每日所得工钱虽似增于昔,然贮[储]蓄力乃不见其增而惟见其减。就此趋势推之,其将来岂堪设想”。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压榨使梁启超深为震惊,“直不寒而栗耳”,“此行所最生感者,则生计上之压迫是也。一受此压迫,殆永劫无摆脱之期!”
三、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访台仅两星期,便因康有为电召不得不匆匆结束行程,此后再未踏足台岛。尽管时间短暂,但梁启超仍对台湾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很大影响。对此,学界已有详细讨论。而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影响,学界所论不多,本节即就此略做分析。
台湾之行的亲身感受,使梁启超看清了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真相,也使原本对学习日本治台经验满怀期望的梁启超失望而归,“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不过,梁启超悲愤、失望的是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奴役、压榨,并没有因此对日本治台政策全盘否定,反而通过亲身考察,对日本治台政策及其影响有更真切的认识。所以,围绕为宪政取经的目标,梁启超还是有所收获的。“今固大失望也,虽然,其中又岂竟无一二可师者”,“吾国人又安可不虚心以效之耶?”“就中若改币制、办专卖、兴水利、调查土地户口、干涉卫生等,多有独到之处,应用最新之技术,万国所共称叹。”
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社会的改造和教育事业的发达,尤令梁启超钦佩不已,“台湾之治,其最可佩服者,在于整齐严肃,使其将外视本岛民之一点除去,则真官僚政治之极轨也。吾所最生感者,在其技师之多而贱。吾国欲效之,则养成各项技师,最少亦须十年。真不易哉。至此深有味乎南海之物质救国论也”。
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另一影响,在于目睹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人民的严密控制和残酷剥削后,梁启超更加积极地支持台湾人民的救亡运动。光绪三十三年,林献堂在奈良曾向梁启超请益台胞争取自由问题,梁启超授以温和运动之法,指出中国在今后30年内绝无能力助台湾争取自由,故不可轻举妄动做无谓牺牲;宜结交日本中央政界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使其不敢过分压制台人。 “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被压杀无一幸存。最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
游台返日后,梁启超继续联络林献堂等人,力图为台湾救亡运动培养领导人才。除指导林献堂等人习诗、治学外,梁启超又要求他们多学政治、法律及泰西史学诸学,并提醒林献堂牢记救国重任。“吾自游台后,深知我公一身关系于三百万台民之将来者甚大,且吾方有事于祖国,不得不广求友助,公又其重要之一人也”。“公若常以此两重大责任悬于心目,则所以自养其才器者,必有在。又岂仅以雕虫小技自安乎哉!以公之年,以公之质,固无不可任之事也。”
针对日本殖民者的愚民教育,梁启超还通过林献堂等人,试图将其筹建的国民常识学会推广至台湾,为救亡运动广育人才。宣统二年一月,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说常识》一文,指出个人自立,最重要者在“具备常识”。处于今日时代,应“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而各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傅益之”。清廷举办新政后,科举既废,教育未能普及,已有学校教育在学科编制、教科书等方面又不能系统完备,欲由此求世界常识不可得,而政治上、社会上一切制度更无足以为助。“今国中之学校,既不足以语于此,而社会各方面之教育,又适足以窒塞常识”,故必须“输进常识”。
此后,梁启超积极筹组国民常识学会,“窃谓欲救国活,无急于此”。除拟定学会《章程》外,他又拟编辑《国民常识丛书》,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史地、国际时事、自然科学等方面,“体裁或用文语或用白话,总期平易浅显,尽人能解,趣味丰富,引人入胜”,以增进国民常识。访台期间,梁启超与林献堂多次商量此事。返回日本后,梁启超又致信林献堂,“国民常识学会一事,自归来后,屡与诸同志熟商其办法,略异于前。除印送通俗之小册子外,欲精心结撰,以办讲义一种。今将改定章程及说略呈揽。弟一年来苦思力索,窃谓为祖国起衰救弊计,舍此末由。即以台湾诸昆弟论,若能得数百人入此学会,获此常识,则将来一线生机既于是焉系”,其目的即在于通过国民常识学会向台湾民众“输进世界学问,增长国民常识”,以开民智、兴民权,抵抗日本殖民压迫。
此外,台湾之行还使梁启超借了解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之真相,看清日本对华政策的阴险、虚伪,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提高了警惕。“舟中西望故国,岂惟慨叹,直不寒而栗耳。”尤其是日本在经济上对台湾的控制、压榨,使梁启超不能不联想到中国的前景,“还顾我祖国,其将来又岂堪设想也”。
访台之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下诏罪己、改组内阁、开放党禁。北方各省一般舆论“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梁启超利用有利形势,计划取道奉天入京参政。日本政府对梁启超此行极为重视,奉天领事专门派人迎接,又派两名警察随护。梁启超一面借力日本为己所用,一面对日本保持警觉,“此行日人非常巴结”。不仅梁启超本人,其党内同志也都对日本保持警觉。盛先觉奉派由日赴沪活动,在下关与太谷尊由“部下某之深通我国情形者相周旋,言次并突问觉旅费充实否,意欲馈赆,觉乃重谢其厚意而婉却之。甚矣哉,日人用心之深也!”抵沪后,盛先觉发现瞿鸿禨欲求日人保护,“乃以实略言觉居日本久熟悉,告日人阴险不可托命。委婉曲陈,务动其听,且引传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证之”。在京活动的罗惇曧也致信梁启超,警告日本有分裂中国的活动。“外交团对于中国,日俄最利中国之分裂,日来种种阻碍,皆日人为之鼓动,将来政治进行,惟日本之阻力最大。”“近者东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国之分裂,其言固不可信也。”凡此均可见梁启超等人对日本的行为保持警惕。
总之,辛亥台湾之行虽历时短暂,但它反映的是梁启超对清末政局的观察、思考和决断。作为梁启超政治谋划的一部分,它又是梁实地探究日本施政成功之道和移植中国的可行性,同时验证自己政策理论、学习执政经验的一次尝试,在政治思想、行动策略等方面对梁启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探讨清末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角度而言,这是不应忽略的一个侧面。
作者丨樊学庆
整理丨吴鑫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