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承、渊源、宿命
师承、渊源、宿命
凤凰网文化: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林旭东先生,陈丹青先生,还有韩辛先生。
韩辛:小时候我去看陈丹青,我带着我的画,我想他可能知道我比他画的好,但是他每次都要摸一下我的头,然后我非常生气,然后旭东就会在旁边帮丹青笑说,你是不是怕才气给丹青摸了去,再也超不过他。我记得我当时最狠的一句话是,我比你小两岁,肯定超过你。
林旭东:一直到今天小辫子还是给揪起来了。
陈丹青:这两天我们的展览在通县的油画院美术馆开了,几位朋友问到我们是什么维持我们40年的友谊,我想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妒嫉,主要是我和韩辛之间彼此妒嫉,但是他很早就非常坦率的告诉我,他妒嫉我,不服。可是我一直到最近才好意思对他说,我也很妒嫉他,这么多年大家其实对我熟悉,不知道我身边这么两位老朋友一路过来,其实对我有多大的影响,而且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交代一些往事,其中包括妒嫉。
凤凰网文化:感谢大家非常艰苦的等待,但不用等40年,我们已经等来了三位我们非常敬仰的老师,我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主持人,大家都可以来提问,只不过现在这个时候话语权离我近一点。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去看了画展?
观众:有。
凤凰网文化:好像也不是太多,有没有人昨天去了昨天的活动?
观众:有。
凤凰网文化:非常感谢,我们这次打败了昨天的活动,这么多人都没有去过。如果去过的人就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大概做了所有讲到的东西,昨天都没有讲到,我昨天冒着感冒去看那个活动,然后随看,就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三位老师基本上把很重要的话题都留给了今天,他们故意不说,只说了一些八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40年。但去年的时候我曾经想要邀请陈丹青老师过来,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是他的一组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西藏组画的30年,我们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各种各样官方关于30或者几十的一个故事,当然今年有100。
这是状况其实都无关个人,我们今天其实关键就是看到了三位个人的个性和创作。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要借助一些背景资料,首先是一些人物,比如说几位也许是概念上的老师,就是俞云阶先生,在林旭东先生这里就是颜文梁,之后还有他们的老师马克西诺夫,可以从陈老师来讲这个脉络。
陈丹青:我们这次三个人同时露面,展示这么多画,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个困扰,就是非常难与跟今天的年轻人分享我们的经验,这个展览分四个部门,就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然后是新世纪这11年。
大家知道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反而在历史过程当中每一代都是一个断层,都不知道上一代的来历,刚才主持人说的几个人物,我相信在这个礼堂里面99%的人都没有听说过。
比方说1949年以后,中国油画的一个教父,并不是中国人,是苏联人叫马克西诺夫,他在1955年被政府请来教授中国新一代油画家,他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俞云阶是上海派去的,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人去,他回到上海以后,就变成右派,在政治压力下面,曾经带了几年上海美专的学生,这里面有一位学生大家一定知道,就是陈逸飞。
然后,陈逸飞在上海美专1964年、1945年毕业以后,进入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为专业的创作人。此外还有两位,其实在当时我们的年轻人圈子里面,比陈逸飞更有名,一位叫夏葆元,一位较魏景山。在此下,大概年轻个七八岁到十岁,就是我们三个,当时失学的青年,大家知道1966年文革以后,所有大学关闭了,中学也关闭了。
所以我们从1971年认识,一直到80年代我们先后到中央美院来,差不多10年期间,我们从来没有上过学,而且我和林旭东两位都是到农村去当知青。
所以真的是自学的一代,但是我们有老师,其中一位老师就是大家知道的陈逸飞,而陈逸飞的老师就是我刚才说的俞云阶,俞云阶的老师是苏联人马克西诺夫。这就已经是一个断层,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20、30年代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油画家到欧洲去留学,最有名的是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而颜文梁就是林旭东当时的老师,他就住在他隔壁一条弄堂里面,我曾经为了几年颜文梁,叙述文革期间1973年左右林旭东怎么带着我去拜见这位当时80出头的老先生,从法国回来了。
刘海粟去以前就创办了上海美专,颜文梁回来创办了苏州美专,徐悲鸿回来创办了中央大学美术系,此后就是变成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的,也不能叫前身,因为徐悲鸿先生后来当了中央美院的院长。
所以是这么一个脉络,可是这个脉络对今天来说,第一它已经完全过时了,完全是失去了实际的教学系统。第二,我们三个人的系统今天也完全过时了,因为那是文革的一个系统,大家可能刚才在画册里看到,70年代我们的作品有两个面相,一个面相就是习作,我们在练习画脑袋,画素描,画风景,画静物。
另外一个面相就是所谓革命创作,这是一个平行的脉络,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知识青年,因为被假定是革命青年,也只能画革命创作,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露脸的一个机会,我们都画过革命创作,这里面有一个秘密,现在已经把公开了,就是陈逸飞和魏景山非常重要的创作,里头有一些很精彩的局部是韩辛画的。
在座的有没有清华美院来的学生?有,当然今天80后的孩子可能对文革创作也不是很熟悉,但大家一定知道陈逸飞,陈逸飞很重要的一幅作品叫《踱步》,里头陈逸飞的背影,旁边一张椅子,都是韩辛画的。此外我也画过,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画了一张画,这都是过时的作品,过时的美学。
 由体制内向外的告别
由体制内向外的告别
此后,80年代我们就分散了,韩辛娶了美国太太到美国去了,顺便说一下他现在是三位孩子的父亲,他的大儿子1982年,二儿子1986年,三儿子1993年,这个礼堂里1982年的有没有?
观众:有。
陈丹青:都是老同志了,刚才领我进来的学生头好像是1993年的、1994年的,比他最小的儿子还要小一岁,所以你别看他梳着辫子,他其实看上去像80后,但他的大孩子却是80后。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很多经验,无论是私人经验还是我们的学习经验,还是我们的作品,跟今天北京的美术界,当代的艺术和在座的年轻人,可能很不容易分享,当然我们有很多故事愿意说,所以回头我跟主持人讲,希望多一点互动的时间,可以棒话题谈一谈。
韩辛:刚才说了,我比他小两岁,今年夏天才忽然发现其实他只比我大了18个月,所以他们现在说我要装嫩,我可不想装老。我去美国比较早,比丹青还早一点,所以他又比我早回来,他是2000年就回来了,我是两年前才刚回来,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丹青,包括看到陈逸飞,他已经去世了,他2005年就死了。
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又熟悉又陌生,因为这个时光过的实在是很快,我现在对丹青也好,对过去或者对艺术我好像要重新找一个定位,今天看到这个场面,让我想起他很久以前带我去看色情电影。
陈丹青:1985年,他30岁的时候,那时候大儿子已经生出来了。他在纽约命令我为他过30岁生日,然后我就做饭,我有照片可以证明,白天我们去博物馆,晚上他说那地他还没去过,我已经去过好多次了,现在大家都能看到,大家电脑上都能看到,我不太清楚电脑上怎么看,你们真幸运。
韩辛:是的,我是1981年的夏天去了美国,丹青是第二年的春天,春节过后。当时陈逸飞和丹青都在纽约,我是到了加州在上学,在西部。我就很想念他们,然后春天就去看他们,丹青领着我,我们一起去了博物馆,很多画,当然是非常激动和感慨,看的时候每一幅画我们小时候有的见过很差的印刷品,或者有的根本没看到过,我们看画的时候也说了好多,我们不约而同的想到了旭东,因为当时他还在中国。
看了一整天,出来了以后,当时在时代广场那一代完全是色情场所,全部都是成人电影,晚上灯光是闪亮闪亮的,的确如此,我就跟丹青说,我说我还没看过,然后丹青就领着我进去了,我写文章还特意写了一笔,我说黑暗中坐定,看的喘不过气来,聚精会神比白天在博物馆还要聚精会神。
确实是亲身经历,40年的故事,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很多的。
陈丹青:你讲清楚哪一类故事,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更早的时候,我刚到纽约的时候,陈逸飞带我去看过。看那种高级的多,那个是当时百老汇秀里面,百老汇大家知道就是音乐剧,其中有一个当时很红的,那个是全部男女演员都是裸体在台上表演,陈逸飞带我去看的,而且他替我买的票,他是第二次看,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就像现在学生会的一样。
韩辛:当年的生活和政治形式在中国今天是你们不可能想像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算是从1979年开始,1980年逐渐逐渐的有很多国内的干部或者是公开的留学生出去,他们都要过这一关一样的,就是说有一个什么代表团去了以后,在那时间很短,但是也挺想看这些电影,就想尽办法,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今天回想起来特别有趣。
陈丹青:我另外一个经历不是带韩辛,是带一位50多岁的老大姐去看,她是一位共产党员,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她的名字就不用提了,她因为一个公差到了纽约,给我打电话,说丹青啊我现在在纽约住在领事馆,我说老师您来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她说您别忙,我就想看看那一面,就明白了,所以我成全了她,因为她一直是单身,现在还是单身,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真的,我说的是真话。
说起电影来,我就要稍微提一下我身边这位老朋友林旭东,大家在画册里已经看到我们在1971年认识,一起画油画,可是他在90年代中期几乎到现在,他有一半的时间,有一阵子是全时投入做中央电视台的影视工作,还有和第六代,一直到贾樟柯这一代,深度介入他们的电影。
这里有没有学电影的同学,或者比较了解电影圈的事情?你大约应该《铁西区》这部纪录片,知道吗?
观众:知道。
陈丹青:《铁西区》这部电影导演是谁,摄影是谁,我现在说不上来,可是全程剪辑是林旭东剪出来的,100多个钟头,全是他自己做的。他居然不挂名,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情。他是1971年跟我们认识到今天,可能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的把自己的画挂出来,还不是个展,是我们三个人的展览。
我昨天在重点讲了这件事情,他说他享受做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做完的那个结果,这是我亲眼看到他少年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画过很大的创作,还画过无数的画,他画完这幅画就不管了,就忘记了,不当回事儿,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是这样子,结果他做电影也是这样子,40年来一直是这样,《铁西区》只是我所知道,他亲自全程参与的一部电影,远远不止这些,在座的太年轻了,如果在座的有60后、70后的应该记得在90年代中央电视台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系列叫《东方时空》、《实话实说》、《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真正参与其中的也是林旭东,是中央台那位夭折的陈虻当时郑重委托他的。
电影圈那么多人,为什么委托他,因为他看出来第一林旭东博览群书对美术史、电影史整个的文艺史有一个大的知识背景,大的判断,其次他的人格非常踏实、厚道,不求名利,做事情非常负责,所以这都是我事后知道的,老林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我们这么近的朋友,我离开中国11年,1992年第一次回来,我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骑着自行车从东城骑到定福庄广播学院去看他,寻找我们少年时代的朋友。
林旭东:事情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我是觉得我很幸运,碰到很多,结果来参与这事儿,也很有意思,这个过程我也很享受,就是这些。
陈丹青:我来补充几句,以前我从美国回来,他就跟我说美国电影,说这说那,问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后来我就是说你是不是看到画画的人就跟他说电影,看到电影的人跟他说画画。他说不是,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去跟他们说,的确如此,我们都知道他弄电影好多年,他做了很多工作。
在2000年以后,像我们这些在国外看到很多张艺谋、陈凯歌这些人的名字,连我妈都在说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怎么好看什么的。我就想起旭东,我说你弄了这么多年,在海外没见过你的名字,或者也不放,做了这么多工作,好像我应该有这点功劳,我就逼着他,我说要放名字的。
前些年开始,比如像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还有《海上传奇》这些影片大概是我唠叨的结果,他总算把名字放上去了。但是他刚才说的《铁西区》是给法国权威的电影手册评为2000年以后,第一个10年最佳的亚洲影片,只有这么一部。
林旭东:全世界最重要的十部影片之一。
陈丹青:亚洲的唯一一部。我知道像旭东这样的性格不应该在这个场合,有这样的老朋友代他说出来,好像涉嫌我有什么目的。大家知道我对今天教育体制的厌恶,我在清华工作的时候,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年要你填表,其中有一栏就是你的学术成就是什么,我每一栏都填我没有学术成就,结果清华有一位人事科的老干部,现在可能退休了,个子非常高,我看他脸上表情很痛苦,最后就把我叫到会场外,他说陈先生你不可以这样的,你写的纽约所那些素材得算学术成就,我说这个既不是学术也不是成就,这是我在纽约出版社叫我写,我就胡扯,不能叫学术成就,这里是清华,我不能把这个叫做学术成就,我现在明白这是一个何等功利的一个空间。
所有人露面,哪怕你们现在年纪很小,可能都要被迫填这些,你的论文是什么,你哪些作品发表过,教授就不用说了,讲师慢慢熬成婆这个过程,在座的老师比我更清楚。可是旭东做过这么多事情,他从来没有自己跟我说过,信里也没有说过,当面也没有说过,更没有跟校方说过。
旭东2004年就默默的辞职了,他跟我一样厌恶这个教育制度,可是我的辞职2004年底被社会大规模过度的渲染,一直说到现在,可能还算一个话题,林旭东就默默的辞职了,所以我在为这个展览写的文字当中,我忽然发现我们三个人又像1971年刚刚认识的时候一样,都没有职业、没有单位,也没有一个权利的说法,我非常骄傲,我有两个这样的朋友,我也值得。
有一点不是叫大家不要有单位,不要混饭吃,大家如果知道在文革时候,我们多么渴望能够进入体制,能够进入学校上学,能够有一个户口,能够有一个校徽,夜里坐火车的时候,人家问起来,年轻人你是哪个单位,我们不必再害羞说我在哪个县、哪个市、哪个村,我们曾经长期非常屈辱非常绝望,我是1978年考上的,韩辛是1980年考上的,旭东最晚,他保持无业知青身份大概有十多年,一直到1984、1985年才考上,我至今想起他去投考的过程,我还是感到非常屈辱,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可是,他最后还是辞职了,为什么?就因为校园里现在只剩下权利,只剩下表格,只剩下你的学术成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说的只是他的一小部分,比方说他干过一件小事情,你们如果愿意赏脸到通县那个美术馆去看,我把他的手稿放在橱窗里面,,什么手稿呢?就是在90年代美国有一份中国杂志叫《今天》,是北岛他们创刊的,到今天还是一个纯文学理论的刊物,有一期是专门试图回顾中国的新电影,就是文革以后,可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写一篇第五代导演整个的一个回顾性的,带有历史评价的这么一篇文字,这篇文章当时编辑找到我,我说我写不了这个,我就向他推荐了林旭东,林旭东就一声不响就写了一两万字,我相信第一次有中文版第五代整个的作品,整个导演背景,整个历史背景真的捋了一遍,这个原稿今天就在那橱窗里展览,这是他做的一件小事情。
大家说算不算学术成果?第二件中事情,也不算大事情,叫中事情,就是在90年代末,他凭个人的力量,当然也受人委托,也有一部分官方的资金,很少的人,主要是靠他独立担当,请来了全世界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年纪最大的80多岁,两次到中国召开国际纪录片研讨会,我的转述可能不正确。这是迄今为止,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能够得到世界范围的一个平台,让最优秀的电影导演、纪录片导演来谈论纪录片。
而他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跟韩辛有关,什么呢?就是韩辛在1981年娶了美国太太阿雅兰,这位阿雅兰是中央美院第二位留学中国,研究明清绘画的美国留学生,这位美国留学生非常热爱中国,是白求恩同志的远房亲戚,如果白求恩还活着,他的三个孩子,就要叫白求恩做舅舅,大舅舅或者大舅公,因为他们更早的亲戚是来自加拿大。
所以在改革开放初立刻就来到中国,然后带回了一位中国丈夫,回去以后他们拿到了鲁丝奖金,在1986年夫妻俩再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拿到一笔基金就是写中国当代美术史,也就是说民国的一部分和1949年后共产党美术史,今天全世界关注中国,可是大家要知道,80年代中国所有文艺在西方没有任何地位,不但没有地位,没有任何知名度,没有人知道中国有电影,没有人知道中国有油画,中国有歌剧、有交响乐,什么都不知道还有现代文学。
陈丹青:现在咱们有钱了,到处想吹牛逼,玩文化,这是现在的事情。80年代我到美国的录像带店看不到一部中国的电影,美国的书店看不到一部中国的小说,绘画不用说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到底两眼一抹黑,阿雅兰当时也就30岁左右,他还不知道何从下手,所以这篇论文大纲,这本书的大纲是林旭东个人起草的,起草以后,把整个的历大战捋了一遍,开具了上百人的名单说你去找这些老画家,延安的、民国的、留法的、留苏的,还有建国以后重要的画家。
非常公正、公允,没有任何门牌之界,然后阿雅兰和韩辛就跑遍全国采访,回去以后花了六年时间写成了西方英语世界第一本中国美术史著作,题目叫《把心献给党,把艺术献给人民》,得了一个大奖,目前阿雅兰女士她今年有50岁了,也是老同志了,她是美国美术汉学界屈指可数的权威之一,就是凭这本书,而这本书的源起当时就是林旭东一个人在宿舍替她写出来,当时她还是学生,这个算不算学术成就?
可是副教授——旭东现在不要这些,撂掉了,我走了,我自己单干去,就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是一样。
韩辛:昨天在讲演有很多年轻人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谈到他们对所谓的结果有些是抱怨现实,我就认为你想想林旭东,对物质的需要是很少的,但是他对艺术方面的追求和享受就是非常高的。
我想我当时就对那个年轻人说,我说你有青春,就是资本,有什么好痛苦,他提到的是艺术,我说你想做艺术,你白天可以去端盘子,晚上可以做艺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都可以。包括像我和丹青,我想对你们是起到好的榜样,文革时候也是很苦的,这种经历。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我们的展览,在通县,在高碑店那,就可以看到原作,我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在那种这么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乐趣,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很骄傲,丹青还一直深深的印在脑海里,想寻回过去。
你们可以对照自己,可能会有些帮助,可以解答你们的苦恼。
陈丹青:你自然知道我深深的印在脑海里,告诉大家?这个展览是他要办的,林旭东从来没有办展览,我也尽量能不办就不办,因为我不要脸已经办过很多展览。
韩辛:哪里哪里。
陈丹青:他是回国第一次办展览,所以这个展览的动意是他起的,你们到展厅看画册,最多的页面,最大的墙面都是他的,这都是他的展览,俩老哥儿就陪他玩一会儿,他说印在我的脑海里,他怎么知道我的脑海。
韩辛:我当然知道你的脑海了。现在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丹青或者在文字上面念到的他总是什么瞪圆的眼睛,老愤青,有的时候我也被迷惑。
陈丹青:他不是迷惑,他是妒嫉。
韩辛:好吧。我的这次展览其实是为你们大家提供了丹青的另一面,你们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说我们一起展览,然后他居然很认真的在最后的一刻,就全身心的扑上去,我也去找资料什么东西,当我们旭东把我们当年在70年代初,文革期间,文革中听的那些老唱片,刚才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是一个单声道的老的唱片,是胶木的唱片,我们文革时候听的,然后他有30多年就没有听到,我也没听到,因为我们都到了国外。
林旭东:我自己也有大概20多年没听过了。
韩辛:我这次把它转换成CD,当那个音乐播放的那一刻,你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就想回到小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要让你们知道他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青葱岁月——各自为战的启蒙
青葱岁月——各自为战的启蒙
凤凰网文化:其实这个是一个导论部分,三位很快就进入状态,刚才说了半天其实还是虽然在讲十年的故事,但是这不是讲故事的故事会,因为这是一个展览的题目,所以肯定我们不只是在讲故事,还要看画。我们有一个次序,这个画册实在做的太好了,我们大概会用类似解读文本的方法,大家可以看到一系列画解读的方式,有的可能是单幅画,本身很有意思,有一些可能是一系列的创作构成某种意义,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某种对照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买到画册会看的更清楚。
这个很清楚出现了四个部分,1971至1981,1982至1990,1991到2000,然后就是2000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1982而不是1980,这个就说明我们通常讲80后是毫无概念的一个东西,如果讲1978后大家可能会明白,1982年是两位就是陈丹青老师和韩辛老师都已经到了美国而林旭东老师还在这边刻苦的准备考试。
我们先从这样一个结构开始,我们先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会在四个部分之中,当然前两个部门会相对的多一些,后面可能会有一些穿插,我们进行下一个。
陈丹青:这是我们现在的照片,因为巴沙艺术想给我们做一集专辑,我想回到1971年到1982年的首页。这当中最大的一张照片,就是有三个人站在一幅大画面前,最左面的就是陈逸飞当时31岁,最右面的是魏景山当时33岁,可是韩辛当时20出头,他大大咧咧居然站在两个当时官方画家当中,好像后面这张画是他画的。后面这张画叫什么呢?当时叫《占领南京》,后来正式题目叫《蒋家王朝的覆灭》,这张画当时被认为非常重要的历史画,现在还挂在革命军事博物馆,大家到长安街西端木樨地那的军事博物馆可以看到这张画,这也是陈逸飞履历当中可能最重要的一张画。
画在1977年左右,你看陈逸飞当时也是年少英俊,31岁以今天他可能还在攻读博士生,还在伤脑筋博士论文,他不可能用最好的岁月去画这张画。而此前实际上他从22、23岁开始已经好的系列创作已经画出来了。
魏景山当时比他名气更大的一个上海画家,两个人合作了这幅画。再下面一幅,就在陈逸飞身体下面那一幅也是韩辛和陈逸飞当年的照片。
韩辛:这个是1976年。
陈丹青:你看他这个猖狂的样子,他总是要站在陈逸飞前面。然后那张发黄的照片是我考上美院以后,我1978年考上,1979年林旭东到北京来,可能我们都得告诉他当时哪一年招生,怎么拿准考证这些。
我和林旭东就在这个花圈面前拍了这张照,当时我是26岁,林旭东27岁,还是一个无业青年,当时他已经画出非常好的画,大家到画展上都能看到。再下面这张黄照片旁边,是我18岁时候的照片,我还没有认识林旭东,当时大病一场在江西赣南宁都就是打游击的地方,我在公社医院刚刚出来,非常虚弱,在山坡上拍摄了一张照,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的。
另一张照片,在左端,左下方,就是一群上海青年在赣北的山区,其中有一位就是林旭东,他比我大一两届,所以比我早一年下乡。
这些照片证明我们真的没有上过学,这是我们的学术成就,我愿意填在表格上,我记得我刚到清华报道的时候,有一栏要我填我所有上过的学,我就说我上过上海茂名北部小学,然后此后初中、高中、大学我都没有上过,下一栏就要填你上这些学的证明人是谁,我就填了毛主席。
这是真的事情,是毛主席叫我们到乡下去,而且我们愿意去,我们愿意去,我不喜欢上学,旭东你喜欢上学吗?
林旭东:那个时候也不喜欢。
陈丹青:也不喜欢上学,所以我们蛮高兴就到农村去了。
我觉得这次跟大家很难分享的就是,第一我们那个时候喜欢听欧洲的古典音乐,17到19世纪古典音乐,但今天在座的青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古典音乐,可能你们喜欢港台流行音乐,内地流行音乐或者欧美的摇滚乐都很好,但是我们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兴趣点。
这一组照片林旭东上边那张有花边的照片是他插队落户以前,我们下乡以前都要到照相馆去拍张照,当时拍照很不容易的,不像你们现在拿起手机就能拍照,很隆重的一件事情。
下端还有我跟韩辛两个人在上海拍的照片,1978年左右,这是这一页的内容,下一页就是刚才说的最后一页。最左端这张照片我很喜欢,就是韩辛在听个哥们弹钢琴,他是谁?
韩辛:他的名字叫陈宏,也从国外转一圈回来了,现在好像是一个音乐制作人。
陈丹青:你说当时你怎么会跟他弹钢琴。
韩辛:他是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抄家以后还藏留了一架钢琴,他妈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老师,喜欢钢琴的,后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音乐节目。陈宏比我小一岁,也是一个很叛逆的青年,他白天有一个工作是在街道工厂里面,厨房里面做菜的,我记得去看他做馒头,12点半夜,他们为第二天早晨的早饭做,然后他叫我多拿几个馒头。
当时他在工作之余他就喜欢弹钢琴,那时候文革的时候,在70年代中,他在练一首肖邦的,好像是叫《革命练习曲》,我常常去他家听他弹钢琴,他还有个妹妹是拉中提琴的。
陈丹青: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音乐会,只有无线电就是广播,广播里面也没有任何古典音乐,甚至没有革命歌曲,一直到1972年以后,因为江青的恩准才有大概五首到八首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民歌可以播放,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互相认识的年代,你打开收音机差不多听不到任何音乐,连革命音乐都听不到,除了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音乐大家可能听过一些歌,其他没有音乐。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想像在上海、在南京、在北京,有那么一些青年后来被形容为地下音乐,就是稍微有点夸张,就是风暴过去以后,从70年代开始,其实各个角落都在偷偷的重新过一种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生活,就是看翻译小说,然后画一些画,等一下你们会看到我们临摹的欧洲画家的画,包括弹钢琴。
所以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男孩、女孩小时候家里都逼着你弹钢琴,跟那会儿弹钢琴完全两回事,我很喜欢这张照片,韩辛这样在听的时候,他真是拿着他的所有性命和神经在听。
韩辛:我插一句,我们当时其实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我们也很认真,觉得很值得骄傲的资本,就是我听过某一首曲子,而且我有自己的切实感受。今天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会比一下名牌,觉得是自己最高的一件光彩,在我们那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如饥如渴的,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天真,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可贵的,那种如饥如渴的求知欲。
陈丹青:我们继续讲,这张最陈旧的方照片就是林旭东小时候,我忽然发现有一点点像蒋经国。林旭东的家庭是什么呢?其实跟北大清华的老教授很像,他的父亲是抗战以后留学到美国,你来说比较好。
林旭东:我父亲在曾经也上过两年北大,后来因为参加运动开除了,后来就转学上。
陈丹青:太有意思了,我到现在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他爸爸上过北大,旭东不说这些事情的。他不说的是什么呢?我到很大才知道,他的爸爸跟杨振宁他们是一代人,是研究核物理的,所以林旭东是生在美国的,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些,他的父亲也是跟杨振宁一代一样想报效祖国, 1949年左右想回来,但当时大家知道那时麦卡锡主义,冷战刚刚开始,他没有得到允许,所以他用了另一个办法就是绕到巴黎,才能够回到中国,让美国人以为他不是回中国,是到巴黎去。
所以旭东在4岁以前是在美国和巴黎然后再回到上海,是这么一个家庭,这张照片很宝贵,你们可能不一定看得到杨振宁的儿子小时候的照片,但这个是其中那一代的科学家的儿子,现在就坐在我旁边。
下面这个是我和我母亲告别,我马上要到农村去了,当时16、17岁之间。顶端那张是我第一次去西藏,1976年我在草原上画那些西藏的小孩子。这张旭东板着个脸,好像给太阳晒的,他刚考上中央美院的时候。这个当然又是陈逸飞和韩辛,韩辛很早就知道怎么能够寻找到一个权力背景。
所以他说最早陈逸飞带他,他很诚实,那是我见过最诚实的一个集会主义者和妒嫉家。他说当陈逸飞给我撑腰的时候,我渐渐不把旭东和丹青放在眼里,所以他说等到林旭东画连环画的时候,把叛徒的脸画成他的脸,气坏了。
最右端的这张就是林旭东上学期间的样子。
韩辛:大家要知道他跟陈逸飞后来吵了架,18年不说话,所以他现在拿这个来报复我。
陈丹青:是吗?大概就是这样,下面两张是我在当知青时候的照片,我们当时喜欢穿中山装。最上面是幸福的年代,50年代韩辛跟他的哥哥和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妈妈一起在公园。
韩辛:当时上海唯一的一幢高楼,叫亚洲第一高楼。
陈丹青:所以我想大概有至少50万上海人在这个背景面前拍过照。这是我们的学术成就就在这了。
 交错独行——殊途同归的求索
交错独行——殊途同归的求索
凤凰网文化: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陈老师提到的一些画。这个是韩辛老师的,旁边的是林旭东老师,两位全部都是自学而画成这个样子,不知道现在考级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陈丹青:这两张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到今天这样一个教学模式还没有改变,但是40年的差隔,同样在画,意思非常不一样,40年前是两个上海的无业青年在家里画,第一他画的真的非常好,我很惭愧,我一辈子没有画过这样,我画不出来。
第二就是他画的非常有感觉,我相信李牧老师你等下可以评价一下这样的画,当时完全没有人教他们这样画,也没有一群青年在画,而且几乎只有这两个,没有别的。可是今天的石膏像作品,我看的要吐出来,太多了,全国大概几十几百万张,所有小孩都要画,就像所有小孩都要弹钢琴一样,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考试。
他们两位这样画的时候,只是假定有一天招生还会恢复,可能还需要素描技术,他们俩在家里,大概1974、1975年左右,画的这两张画。大家如果有兴趣,最好去看原作,我在这两张画上面看的不是石膏,就是青春,聚精会神在做这件事情,跟今天的孩子,今天的孩子画石膏就是苦役,完全是苦役,而且跟艺术没有关系,他的目的是换一张准考证。
韩辛:下面那个图说是我写的,旭东画的石膏像我亲眼看着他画,是1974年的夏天,天气很热,上海的夏天是非常热的,我去他家看到他在很暗的灯光下面,穿了一件今天叫体恤,那个时候叫和尚领,老头衫,他穿的额头冒汗,手里拿了一把铅笔,削的很尖,然后一丝一丝在那画我看着非常感动,我一直忘不了。
后来到了1981年,我娶了美国太太,他问我要什么结婚礼物,我就记得这一幅画,我说我就要这一张,所以这幅画是送给我的作为结婚礼物,后来我把它带到美国,这次我特意从美国带回来,为了我们这次展览。
陈丹青:最左面的这张画是林旭东画韩辛,当中这张画是我画林旭东,然后右边这张画,那个大脑袋是韩辛画他的妈妈,他画这张画的时候只有20岁,我正好在编排的时候,我收到上海一个15岁的小姑娘给我寄来的信,很厚的一叠信,她传达一个讯息,她说老师以后我要跟你学画,我已经很骄傲的宣布我通过了9级速写考试,我一定报找要通过9级素描考试,这专业证书我看了毛骨悚然。我真是要讨一句公道话,大家看看这幅素描,这幅素描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画的出来,不是说他们画的出这样的素描,而是画不出这样的感觉,艺术最重要的是感觉,什么叫才能,才能就是感觉,李牧你说对不对,他在20岁的时候画出这样的素描,我只会画速写,我不会画素描。
韩辛:我插一句,就是因为当年一天学也没上过,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束缚,现在我在国外转了一圈回来,也将近30年,30年前我来过北大,今天是30年以后第一次进来,我老觉得我的感受是现在的东西,规范太多,束缚太多,弄的学生好像担子都挺小的,有一点唯唯诺诺,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一种不怕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才会有创造,现在没有创造,哪怕一个最简单,我说的是画,像素描其实他们就缺一种精神,那种精神不是你不吃饭下苦功可以练出来的,而是要发自你内心的一种东西,没有。
凤凰网文化:我们继续来看韩老师的作品,请韩老师讲一讲。
韩辛:可以讲一讲,我刚才讲到有一种不怕的不畏的精神。小时候也不懂,因为是1966年我才1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文革,所以严格来说只上了三年小学,三年小学大概唯一的一个文化基础,所以也不怕,也不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都没有,年轻的时候十几岁也是如饥如渴的去学,那种求知欲望是非常强调的。
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很严酷的,你很容易被卷进去,我在1973年的时候就开始被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就是绘画展,绘画展是四人帮江青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在林彪事件1971年发生以后,国民经济已经是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
旭东是专门做记录的,所以他老是笑我不会叙述,的确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我只有三年小学水平。丹青的文字就不用说了,不管这些了,当时我只有十几岁,我有幸会卷入了“黑画展”,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和刘海粟这些前辈的前辈在一起,遭到批判,当时十几岁的我也就面临过这样的剧场,有一个叫万人大会,黑压压的一片,跟丰子恺坐在一起。
陈丹青:都是今天的多少倍,在这些老先生留法回来的老先生旁边,站着一个17岁的少年就是韩辛,是黑画家。什么黑画呢?回到前面他用野兽态画法画的风景。
韩辛:就是跟当时所流行的革命文艺是完全逆反的。所以当时很叛逆,卷进了这些事情里面我当时是幸喜,因为我的画能够给吴大羽并列,称为老小画怪,我特别高兴,我既然跑到当时革命创作委员会,我说还有没有入场券,多给我几张,我要请人去看。
陈丹青:我要说一下吴大羽是谁,吴大羽是吴冠中的老师,也是赵无极的老师,非常老的一个人,韩辛17岁就跟他同台挨批。
韩辛:对,所以是非常的得意,因为当时的政治高压是很厉害的,我亲眼看到很多老先生都痛哭流涕,当时叫“斗私批修”,就是要自己表示自己的检查。很多人看到我就很害怕,害怕我口误遮拦的会牵连到他们,人人都避着我,我当时只有10几岁,很喜欢跟别人一起玩,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认识旭东,我到旭东那,我问他现在没有人跟我玩,我来这可以吗,他说那你来吧,旭东是当时唯一一个对我这样说,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
刚才那个就受到很多政治的压力,毕竟年轻还是想挤到官方的展览里面,取得一定的承认,要大家知道。我的名字当时是被禁的,但是在后来,在陈逸飞一些好朋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了一些机会,也是开始去他们上海的画院帮他们做下手,当时发我15块人民币一个月,像现在的小时工。
现在看来文革当时很多大的画,很多老画家的作品都有我画的部分,现在有的时候在拍卖行看到一些拍着天价的作品,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是我画的吗。
这张画也很有意思,这张画他当年想临摹维米尔,学习他的作风,其实是更接近巴黎画派的作风。说起来大家不相信,他这幅画藏了40年,我到今年才看见,他不让我看见,他以为我看了就会学一下他画的那么好,好几幅画我到今年才看见,这就是我们的友谊,这就是妒嫉的力量和防范的力量。
韩辛:我要补充一句,的确如此,我说丹青多少年来,丹青一直是我心目中的一个竞争对手,我已经到了国外,而且我往往在一些美术馆或者在美国或者欧洲,看到一些画,我们小时候或者一起看过一起临摹过,那个时候就会想到很多过去的朋友、老师或者一些景象,其中丹青的影子是最让我感到张盲的,我有时候会问我,我到底超过了他没有。
陈丹青:你那环节已经超过我了,可是你不让我知道。我当时看到我也画不了这样,大家要是画画的就知道,我从来没有画过这样水准的写生画,我今天仍然画不出来。
韩辛:当年丹青和我一样,也是没有上过学,都是自己画,非常努力。我老是觉得我跟丹青差了好多,我要追丹青。然后当时70年代的时候,维米尔是非常不起眼的,可以说国内很少有人知道,现在已经有人知道他,国内也有很多年轻的画家学他。
当时我们都不懂外文,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画的好,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欧洲的东西过来,所以维米尔是没有人知道的,我自然绝对不能让丹青知道,所以我在学他,学的时候这张画一直没有给他看,今年9月份的时候为了我们这个展览,我把这个画从美国带回来,他一看看到,他大吃一惊,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他很生气的说你不给我看,我说我不能让你看就是怕你学,后来他说,当时给我看了我也画不出,所以我还是挺满意的。
陈丹青:这张画是林旭东在70年代临摹美国现实主义大师库尔贝的一幅画,叫石工,在座的同学知道库尔贝吗?学画的同学知道库尔贝吗?所谓现实主义,这句话在美术史上最早出现是因为库尔贝。在文革当中大家知道苏联绘画影响最大,压倒性的影响,欧洲影响当时随着民国画家,老画家被打倒,很少有人会关注。
可是旭东在70年代临摹了这张画,非常中规中矩临摹这张画,那么他从什么上面来临摹,是从一张单页的画片来临摹,这里面有故事,是什么呢?这个画页是他从一位叫何宜生的老师那买来的,这位何宜生是解放前颜文梁苏州美专的毕业生,手上有一些画片。
1949年以后,在上海开私人画室,教授学徒,这个历史大家也不太清楚了,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包括广州,我相信北京也有,私下当时的政策允许有私人化画室,等于是小小的学院,那么几个或者十来个学生,大部分今天来说也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能够交的起学费。
到了1966年,所有的画室必须关闭,所有画室的主人被批斗,他们就倒霉了,倒霉以后就无以为济,因为他没有单位,这位何宜生老先生就变卖自己的颜料、画笔、画布这些东西,继续为生,这里面最贵重的一批财产,就是他私人收藏的民国版的,从欧洲过来的原版画片,这张画当时像林旭东开价是人民币10块钱。
韩辛:那个时候是天价。
陈丹青:相当于今天好几千块钱差不多。
韩辛:哪里,上万。他相当于一般人半个月的工资。
陈丹青:那时候我家里非常贫困,后来我父母告诉我在60年代我们家最穷的时候,每个人个人生活费是7块钱,当时林旭东是17、18岁,咬牙就买下了这幅画,我第一次听到库尔贝的名字是在书上,可是第一次有一个活人告诉我,你看这是库尔贝的石工,就是林旭东。此后我的西藏组画被认为是摆脱苏联传统,回到欧洲的传统,事实上40年前,在林旭东身边,在他的客厅里面,我们三个人就开始想像欧洲,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蛮另类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幅画片为什么卖十块钱,也有他的道理,是什么呢?这幅画的原作已经毁誉冰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原作厂在德国德累斯敦皇家美术馆,然后二战期间联军轰炸,就把美术馆的一部分藏品给炸掉了,其中还包括另外一位重要的德国画家门采尔最重要的作品叫《铁工厂》,他与库尔贝同志的《石工》全部炸没了。
这个画片之所以珍贵,是在战前,当时电子扫描也好,高清晰的幻灯片制版都还没有发明,当时的老师傅用玻璃套版的那种彩色印制,手工制作,第一代留法画家,带回来大量这样的画片,林旭东有幸在当时能够买到这样的画片。
所以,这幅画片背后的故事说明了上海和欧洲的关系,这么如丝如缕,能够曲折的传到文革,传到这个小孩子身上,然后又传到我和韩辛的身上,后来又曲折的反映在我的西藏组画。西藏组画浪得虚名以后,被过渡议论,大家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差不多可以追诉到这些画片背后的故事,这就是遥远的一个东方,一个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跟19世纪的绘画有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库尔贝本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很感动,他的一张画在20世纪经历这样的变化,有这样的影响。
 归去来兮——西行之魅与未竟
归去来兮——西行之魅与未竟
凤凰网文化:我是想问问林旭东老师,因为这幅应该算是男裸体站立,在1971年画的一幅人体,其实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样的环境下面,为什么还可以坚持一个从美术或者说油画角度自己来完成这样一个方式?
林旭东:这个模特是我的弟弟,当时只能弟弟可以被我这样画。为什么画人体呢,这个确实是从颜文梁老师那,他说学油画一定要画人体,不然画不好,就是这样硬着头皮,我弟弟也不是太愿意,说了半天,最后就画了。
凤凰网文化:我们来继续,现在咱们可以部分的进入到80年代,我们先来看一组,都是韩辛老师的水墨。
陈丹青:介于油画染料和水粉之间的一种材料,他是一个天生的风景画家,远远的把我甩在后面,这是他在1989年获得美国的一个基金,进入美国莫奈花园,莫奈是影响他的老大,一直活到1923年,他晚年住在一个庄园里面,这个庄园是法国总理送给他的,他就住在那儿,现在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他跟莫奈的孙子变成好朋友,这批风景画画的我真是五体投地。
韩辛:可以说几句,小时候很喜欢印象派的画,中国当时实在是太封闭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西方任何原作,一直到1978年才有了第一次法国农村风景画展,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有莫奈和马奈的原作,小时候这种幻想就是说西方的杰作是怎么样,现在回想也很多是笑话,比如有一幅画我会拿去请教颜文梁老先生,也是旭东的老师,老先生是苏州人,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我才十几岁拿着那个画去问他,我说这个像不像印象派,老先生用苏州话跟我说,蛮像的,不过印象派现在不流行了。
所以这些烙印在脑海里是很深的,后来我有幸到莫奈的花园,坐在里面,有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我那一年的5月7号,1979年的5月7号,那天我就站在莫奈花园的桥上面,跟着莫奈曾外孙一起,我就跟他说,你知道10年前的现在我在干什么,他说我怎么知道呢,他说你在中国。
后来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记得很清楚,十年前的现在我就坐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室里面考政治,结果他说是吗,我说我不及格,所以我不会忘记。在莫奈的花园里面有很多经历,还是联想到了中国,在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美,莫奈建这个花园,我有幸在那住了将近一年,所以我画了两百多幅风景。
这张画是从莫奈的卧室看出去,当时我有莫奈整个花园的钥匙,我住在他的家里面,一般人不会有这个机会可以从这个角度画这幅画的,很特殊。我去的时候,你们后面可以看到我画的一组是纽约的地铁,其实根本不是画这些风景,在当时西方流行的艺术风格里面,印象派的确已经属于过去100年前的,当代艺术非常粗暴的一种艺术形式。
我当时是画纽约地铁里面充满了涂鸦,当时一些有名的美国艺术家,有一个委员会评选的,我被他们选上,是因为我画纽约的地铁,但是我去了莫奈的花园以后,当时还有另外两位美国的艺术家,我们三个人住在里面,都是当代艺术家,代表美国当代艺术家去了,我到莫奈花园里面,我还是像我以前一样很真实,我面对的是很美的景色,我就通过我的画画出来了,但是画的很美,完全是印象派的那种风格,其实我内心是想着我十多年前在中国的那种经历,这些画是充满感情的,有这么一个机会把它表现出来。
当时美国画家就觉得不理解,他们做的一些创作其实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根本不符合的。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很真实的去反应他内心的感受,如果你面对美管他印象派还是什么派,只要你有切身、真挚的感受,应该有勇气把它表达出来,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画出来了,但是这些画我从来没有展览过,这是第一次展出,我在美国当然也画过一些风景画,但是是卖钱的,我连照片都不保留的,但这一批画大概有200幅左右,我从来没有展出过,这次我带回来,我非常高兴丹青说好。
要说到后面,他这次办展览,他很恼火,就是有几幅画,他说怎么到这么重要的画怎么没带来展出,我就说因为你以前没有说过好,所以我想就不带来了,所以这几幅画他认为画的好,我觉得我带回来还是带对了,从来没展出过。
陈丹青:大家觉得画的好吗?
观众:好。
陈丹青:我相信莫奈的孙子会非常不明白,已经100多年过去了,怎么会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用施洋的手法用一个中国人的眼睛在他的曾祖父家里面画出这样一幅风景,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画真的是过时了,但是他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19世纪,只是欧洲这么小的一个区域的画,辐射到全世界,影响到那么多国家,可是对我来说,我这些年画了大量文人画的画册,元明清三代画家,黄公望、赵孟頫、董其昌等等,穿越将近700、800年,是另一种境界,另一种文明,非常高的文明,非常成熟透顶的,我们不能叫风景画,是山水画。
可是大家可以看看在法国莫奈的故居,能够每年会有奖金给各国选出来的才俊到那去住一年,拿到莫奈家的钥匙,住在那儿,这风景跟过去一模一样,大家有一天去到法国或者德国或者意大利,大家可以看到将近500年来的风景和人文景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都在那里,可是反观中国,第一董其昌的故居在哪里,赵孟頫的故居在哪里,没有了,完全没有了。
韩辛:主要一点是要真实,因为流行的东西。
陈丹青:怎么个真实法,我很想到董其昌家里去,我不知道他家在哪。
韩辛:我没有在说你说的话题,我在说我的画,因为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年轻人会改变自己的追求,从艺术的风格去改变,我倒不要盲目的去,你还是要凭着你的直觉,如果你看到一个美的东西,不要害怕。
陈丹青:像韩辛那样直觉。
韩辛:是的,是应该这样。
凤凰网文化:所以刚才提到地铁的系列,我们不会马上拿出来,我们先看一下80年代不同的创作状况,当时其实三位在不同的地方。这个是陈老师在纽约画自己的皮鞋。
陈丹青:韩辛你说吧,那个时候你已经远远把我甩到后面去了,你来评价这些画。
韩辛:是的,当时不但把你甩在后面,把陈逸飞也甩在后面。因为丹青他们出去以前,我总觉得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情要比我深的多,他到了纽约的时候,可能也是他的西藏组画害了他,他就放不下西藏组画的包袱,所以他住在纽约,我画了纽约的地铁,是找到了一个内容就是说我可以发挥。
他其实在纽约的状态其实还没有离开中国那种状态。当然现在来看,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在当时我就觉得他陷入这个困境里面,其实我心里还是蛮高兴的。去看他,看他还是在钟情于西藏,甚至于在国内油画,当时我已经全身心的把中国远远的抛在后面,就想进入到西方文化的环境。
我到纽约我也找到了一个体裁,就是有一个地铁,地铁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而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下系统之一,1907年纽约就有了,就像我们当时去到那,英文也不是很好,可以说是没有,所以每个人都会很紧张,当时坐地铁,越战以后美国的经济也很糟糕,年轻人非常不满,有很多就发泄,纽约的地铁是四通八达的,所以里里外外画满了涂鸦,有一种神秘或者残暴的感觉。
一般东方人过去以后,完全害怕的,心里很紧张因为也不懂,其实跟我们当时移居到国外的心态很温和,我就通过一些照片,拍了以后画了这个内容,这一画就画了30年,在这期间,丹青是住在纽约,但是他找不到一个像他西藏组画这样一个内容,在文革末期,让他有一个发挥他所有的知识和能耐的一个载体。
他很痛苦,那个时候住在纽约,他也寻找各种各样的道路,当时他除了到博物馆去研究西方绘画最真,过去几百年油画大师的一些作品,他自己其实在对话。
这个内容是很普通的,他其实内心在挣扎,他完全有能力去画一个很大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有点幸灾乐祸,他就找不到。现在回过头来看,几十年过去了,我觉得我现在成熟一点,能够比较综合的看这个。他的鞋子还是相当有内涵的东西,给他发挥成这样,但是你们一定要像我一样了解他,才能知道他的深奥在哪里。
的确如此,这幅画完全反映了他对法国的马奈的解读和他自己追求的一种境界,主要是用笔。
这里面也反映了一个,如果说我找到了纽约的地铁这样一个体裁,他去画一个鞋子,用旭东的话来说,有一种淡定,你不需要一个很宏伟的什么东西,一个普通的东西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寄托,这个鞋子寄托了什么,你们自己感悟,如果是画画的人会看到它的颜色,他的用笔,而且他和历史的一个传承。我这个解读不知道对不对,给他凭一个奖吧。
凤凰网文化:我们来看一下同期林旭东老师在做什么。
陈丹青:这是林旭东在1988年1989年左右从中央美院壁画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版画系毕业创作,内容是画沈从文小时候的插图。大家知道我们在文革当中是学油画起来的,素描、风景、静物、人像这些。但是我是这三个老朋友里面最幸运的,在1976年因为画毛泽东去世非常侥幸的被选上全国美展,而且初露头角被北京美术界知道了,之后又很幸运的1978年赶上第一届研究生招生,所以我被体制接纳,而且被承认了。
可是韩辛躲在背后画了这么多画,也没有署名,外界不知道陈逸飞的有些画是跟他一起画的。林旭东在文化大革命也画过,但是他从来不去追求怎么画扛出去,经过一系列就像今天的一个体制游戏那样,怎样进入全国美展,进入一个体制的适应,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其他人也替他做过没有做成功,这一晃就到了80年代,到了1984、1985年,他考上中央美院以后,前面有过几次失败的考试,画的这么好的画失败了没有能够进来,而且当时的招生不像今天这样,某一年忽然不招油画了,下一年忽然招版画了。
所以这个时候版画系的老师知道他在文革末年就开始画过非常精采的连环画,肯定了他在连环画上的成就,当时他画了老舍的《骆驼祥子》,还有鲁迅的小说,还有关于徐悲鸿的传奇,他都画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全国人民美术出版社都出版过,在美术界引起范围内的一个关注,少年刘晓东当时还在东北是个小孩子,他就临摹过林旭东的连环画,非常佩服。
然后带着这些连环画到北京来参加考试,此后知道林旭东的宿舍就在他对面,80年代他们俩成了好朋友,这是他早期连环画的一个履历。这可能是他在80年代末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他画的是沈从文,大家可以知道他都有个脉络的,他年轻时候去插队,然后对下层的形象情有独钟,回头再翻回到画《骆驼祥子》那个连环画给大家看一看,就顺理成章,一直走到画沈从文的版本,问题是像我刚才说的,旭东他不会抱怨命运,他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在就学这个问题上最坎坷,受最多委屈的人,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命运把他安排到版画,他就认认真真画版画,命运把他送到中央电视台做《东方时空》他就认认真真做,然后这些第六代、第七代导演找到他,他也认认真真把活接下来,而且也不声张就把事情做好,真的是像他讲的,他享受这个过程,现在这是他的过程之一。
韩辛:这个插图虽然是沈从文的小说插图,但是林旭东跟我说过,他当年插队的时候到江西农村,那种感受跟沈从文当时的感受差不多,所以他觉得一点都不陌生,去做沈从文的插图。
陈丹青:我们这代人和民国那一代人小说文本的关系,甚至包括东欧和俄罗斯小说的关系,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青年画家来说,可能也有点隔膜了,今天当代艺术非常重要,大部分年轻人的目标是做当代艺术,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绘画一个是受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我们三个小时候喜欢听古典音乐,也喜欢看欧美19世纪小说。
所以林旭东在这方面的认识又格外深沉一些,今天很难想像一个20、30岁的青年,会对那个时候的文本有那么深的认识,同时我们又从小就当农民,当知青。
所以这条线一直贯穿,你们回头看到他新世纪画的画,他仍然在画民工,而且他画的民工画直接启示了刘晓东,刘晓东最早期的创作其实是画他自己的小圈子,画他的女朋友,画他的爱人,画他的同学,在遛狗,种种这些,后来他慢慢走出这个圈子,应该说受到了林旭东画民工的影响,回头大家会看到他在90年代和新世纪画的民工。
这是个可以深思的问题,他是一个上海好人家的子弟,在美国出生,在欧洲长大,然后回到上海,可是他毕生感兴趣的,关注的,寻求绘画表达的却是下层的工人和农民,这是我们自己很难解释的原因,我比较居中,我也喜欢画漂亮的女孩,我也喜欢画很苦的农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韩辛从小画灿烂的风景,画一些非常能够吸引80后的一些画,我们没有交谈过这件事情,可是这次排版,等到我们东西都出来了,就会谈到这个话题,比方说到这一页的时候,左页就是韩辛在70、80年代画的上海漂亮女孩,旁边是我画的村里农民和西藏人,韩辛他说丹青我现在才明白你那会儿多苦,我在上海画小姑娘,你在农村画这些很苦的农民。
其实我画这些农民我自己一点都不苦,我虽然还在生产队种地,但是我非常高兴,当时只要能画画就好,给大家看看《骆驼祥子》的插图,《骆驼祥子》大家知道吗?老舍最著名的小说,林旭东在1978年、1977年左右就画了这样的连环画。
这个《骆驼祥子》的脸,来自他少年时代的一个下层的当工人的孩子的脸。
凤凰网文化:我们终于到地铁了,我们开始。
韩辛:这幅画名字叫前所未有的刺激,当时我画了一幅纽约的地铁,我寄了一封信,里面加了这张当时的明信片给旭东,我80年代中期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时候,去看旭东把我的这张画贴在他的床头,而且告诉我他跟丹青的通信里面,丹青说韩辛画的那些东西,我每天亲身经历,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丹青和旭东离的我这么远,他们居然在谈我的画,我就特别特别感动,也能想到丹青为什么不画。
这幅画旁边的那张照片其实就是丹青拍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画。
陈丹青:你画了我就不敢画,真的地铁,你们看看他一点没有夸张。
韩辛:对,当时纽约的地铁就是这样,整个一个系统,是非常庞大的,而且那种冲击力你就感觉到资本主义虽然老,而且味道很臭在那个地铁里面,但是感觉到一种震撼的力量,他开过来的时候,整个地面或者什么都会抖动,好像还蛮有力量的。
这一幅是转门,地铁的路口,如果你去到美国,很象征的一种,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选择,进去还是出来,它只有一次你过去,所以一般人都很小心,害怕乘错了地铁,或者走错了路口,所以都会比较紧张,当你面对这几道铁杠。所以我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最近还不停的在画,不断的画纽约地铁,但它也经历了好几次变化,当时去的时候很多景象,有熟悉的,也有根本不熟悉的。
陈丹青:我相信今天北大的学生,到了纽约以后,会非常看不起美国,因为看他们的飞机场、地铁站非常的破旧,跟今天中国新的硬件简直没法比,可是纽约牛的就是地铁1907年就有了,一直用到现在,1907年中国还是光绪年间,这就是所谓先进和后进的关系,今天后进国家就有后发优势,在硬件上都比老牌帝国主义要好。
老牌帝国主义很念旧,将近100年的系统,有地下这么庞大的一个像血管一样的地铁系统,巴黎伦敦都是这样的。伦敦地铁系统始于1896年,比纽约还有早。
韩辛:我这里再插上去说,跟丹青的情节,虽然我觉得我已经在某一个阶段会觉得我大概超过他了,我在纽约有了第一次展示我纽约地铁系列的展览。
我拍了一个照片,移花接木,就把它的头,安装在地铁乘客的头上了。当时我虽然不住在纽约,但是我也常去纽约,因为我画纽约的地铁。虽然我想我大概超过他,可是其实还是跟他连的很近。
陈丹青:这就是友谊的力量,一个是妒嫉,一个是记仇,我完全忘记我会这么刻薄的对待他。
凤凰网文化:现在时间很尴尬,我们进行了这么久,其实还没有进入90年代,这样的话,大家是想多看会儿画,还是提问?不能完全的还是用这种方式,可能太细了。
陈丹青:我其实希望大家,要是愿意画点时间到展览馆去看画会好的多,我看到这些播放形式我就会不喜欢,因为你们一天到晚在上课,今天好像又在上课,我不确实你们真的对画感兴趣,这都是一些过时的画。
凤凰网文化:我们非常快的看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些,旭东老师的民工。我们再过一个系列是陈老师的一些画,这是韩辛老师的。
陈丹青:这是我新世纪画的画,回国以来画的画。
凤凰网文化:这幅画待会儿还会出现,再给韩辛老师一个阶段。
韩辛:这是2000年以后。
陈丹青:这是他的第二位太太,是西伯利亚过来的一个俄罗斯青年,跟我女儿一样大,变成他第二个太太,然后在中国的合资公司不知道怎么他们俩就好了,然后他就去了俄罗斯,最好玩的是去俄罗斯进入了画廊,看到了我们小时候一天到晚谈论的那些苏俄大画家的画,他非常激动,打长途电话给我,当时我们年纪多过了四十好几,快接近五十了,他居然激动的寄了一封信给我,就写中国北京陈丹青收,然后我收到了居然。
写了另外一封信叫中国上海陈逸飞收,陈逸飞也收到了,就是把他当时在俄罗斯,这都是我们这代人在小时候梦寐以求能够看到原作的画,这是韩辛非常率真可爱的地方。
韩辛:是的,有的时候因为在国外居住了将近30年,很多习惯跟中国可能还有一些不同,因为我有的时候想的时候是英文想的,所以你们不要笑,其实是一种习惯,很真实的,是这么一回事,是这个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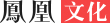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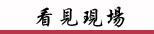






 交错独行——殊途同归的求索
交错独行——殊途同归的求索 归去来兮——西行之魅与未竟
归去来兮——西行之魅与未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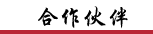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