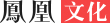于一爽:写作是一场超级自恋和虚荣心
导语:于一爽,1984年生于北京,她出过两本书,结过一次婚,喝过很多酒,做过无数传媒,水瓶座,问奇怪的问题,爱信仰中“怀疑”的部分。
她喜欢男女关系,说世界上一切都跟性有关;她喜欢疯狂,说有意识的东西都是为了无意识的东西;她喜欢时间,说人应该这样度过每天的“25个小时”:先是清晨,然后是晚上,然后是中午,然后是早上,然后是夜里。
她很温柔,但用蔑视回应温柔;她说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却又非常自我;她认真写作,可是觉得对任何事认真都很傻,于是就只写写两性关系,凡36篇,结集成书:《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张定浩评论一爽小说头一句“我喜欢她小说里一种轻的东西”。“轻”是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启示录》提出的跟“重”相对的同样高明的艺术,是一种“灵悟美”。我愿意理解一爽是属于中国的80后城市现代派,就像她小说封面的那句总结:“我不会构造故事,而是顺其自然,不是我在写故事,是故事本身就那样,我只是复述出来。人物也是,里面的人物不那么挣扎纠结,好像生活随便怎样他们照样那样,没有愤怒也没有好奇”。(文:吕美静)

我的想象力在人物关系的转换上
凤凰网文化:《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这本小说集写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写的第一篇小说?
于一爽:第一篇小说或者也不叫小说,我觉得就两千字,当时黄佟佟在《花溪》,我觉得那是一个知音之类的杂志,他们还敢说也能发小说,我当时对小说没有理解,就写了一个两千字的故事,写“我”在一个男人家,给另外一个男人打电话,我写的是我的虚荣心当时,写完挺爽的其实。
我还是很尊重刊物的,我不太在乎在网络上发表,但是我特别在乎比如说被《收获》发,我这方面有点死板,我觉得如果这个状况下鼓励我,我就会继续创作吧。《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这本小说集,应该是认识我老公之后写的,从2011年年底到2013年年底,差不多两年。
凤凰网文化:小说集共划分了三个集合:他,俩人,头等舱,划分的逻辑是什么?
于一爽:《头等舱》看起来是一个中篇,其实也是一个短篇,就是连缀成了一个中篇,但当时在一个刊物上发的时候就是这个形式。因为我没有写过长的东西,就对长的东西有好感,就把这个大概三四万字吧,放在一个里面。《俩人》是最早《人民文学》发的三篇东西,当时就叫《俩人》,就是写的两个人的关系,男女关系,或者男男关系,或者女女关系。我这么分是因为按人称,也可以不叫人称,它都是我把自己当成一个男性去写,虽然仔细看还是女的写的了,《俩人》就是正常的用女性性别去写。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喜欢用第一人称男性的视角写?
于一爽:可能当时是觉得很安全,还自以为是,我变身成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然后没有人能看出我写的是什么。就觉得那样姿势很舒服,其实最近都避免用第一人称写,因为我觉得我太自恋了,然后我觉得不用第一人称会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你那一下还是变成第一人称。
虽然没有人说虚构是判断小说好和不好的标准,但是我觉得虚构还是很重要。然后有一个词我觉得被广告界用坏了——创意,我觉得小说里还是需要很多创意的。这是韩东跟我说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可能有时候只是一个点,比如有一篇,一个女的很喜欢一个男的,但她最后见了这个男的老婆跟他说,你不要离婚,因为她觉得他老婆也配得到爱情,只有这一句话,来自于我生活中,我真的跟一个男的说过,可是前前后后连接起来的差不多一万字的小说,好像都为了到达这句话编的吧。
凤凰网文化:你最感兴趣的点就在两性关系吗?
于一爽: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很有限的,我还有一点想象力,就是在人物关系,或者人物关系的转换上。至少在我写小说这两年,我觉得感情生活仍然是我最在乎的,现在我的生活重点,可能也还不是挣钱,或者也还不是工作。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不写感情,我最近写的几个,没有怎么写到性,或者就写了性的前面和后面,但就没有性本身了吧。作为作者我自己感觉到的这种自我重复,比所有看书的人,感觉到的还强烈,我也会很害怕。
我理解的粗俗就是温柔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影响你比较深的作家?
于一爽:这个可能是某种误解和偏见吧,中国各地都有写小说好的,但我觉得真正集中的就是北京和南京,南京那些人的感觉,我是很喜欢的,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说具体的作家,我还挺喜欢美国作家的,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些吧,战后的一些作家,可能我看短篇看得多。
最近其实在看比如有结构训练的一些枯燥的东西,因为我出这本小说之后,就被好多人指点了,很多人说,你有你可贵的东西,但整体就是在胡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在这样就会写不下去了。
契科夫我也很喜欢,我都在重新看契科夫和海明威。比如说海明威那一篇《白象似的群山》,教科书就会讲白象的象征多么厉害多么好,可是他那篇小说真正打动我的,根本不是远处白象似的山的那种象征,那个东西根本不重要。本身的故事其实就是很好看,就是咱们是一对男女聊天,我怀孕了,我想生孩子,你又很烦燥,我一直在讨好你。我在讨好你的过程中,我三次看到了远处的群山,但我最后都没有说服你,最后你问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说好极了,我说好极了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打算讨好你,我已经不爱你了。我觉得他那个不是很具体的意向已经很好了。
我比较喜欢看粗俗一点的东西,比如咱俩都喜欢的《死水恶波》那种感觉。我是一个还挺讲究的人,但是就是无端地对美国中部城市有好感,比如所有人就吃炸薯条,他也不介意变成沙发里的薯条,所有人又很温柔,说不出来。
《死水恶波》感觉特别像《德州巴黎》,一个水管工去美国中部一个城市修理水管,那个城市太干旱了,然后到了那边,只有女主人,而且女主人总是问东问西,也不说水管的事,只说我的丈夫正在修理着。当然两个人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些初次见面的吸引,后来水管工来到农田,发现他的丈夫已经被电死了,他重新回到镇子上一直在想怎么委婉地把这个噩耗告诉女主人,最后他终于想到办法之后女主人根本无所谓。接下来的几天他继续在镇子上修理水管,有时候女主人会拿个干涩的三明治过来跟他吃,他一直控制自己,女人会跟他说自己的生活很乏味,直到有一天,他真的走进了女人的家里,发现她的生活真的一丝不差的像她描述的那样乏味的时候,他开着车就失望地逃跑了。
我写小说像谈恋爱只喜欢谈一开头
凤凰网文化:你的小说札记和小说本身不太相符,比如《看电视》,札记里写的是,女人幻想丈夫出车祸感到兴奋,小说写的是女人和丈夫看电视感到无聊。我觉得可能因为这篇小说足够短,只是生活一个片段,虽然写的不是一个事,但是小说表现出了札记的意思。
于一爽:这个东西算小说吗?可能也算,我不是一个很有突破性质的人,我还希望用某种小说的概念去规范。规范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片断,前两天别人也跟我说,你写什么东西都是一开头特别好,就像你谈恋爱似的,好像只喜欢谈前两周,可能两周都到不了。我现在觉得我可能写东西也是这样。比如我也可以跟你探讨,《看电视》的男女主人公是不是可以继续写下去,为什么两个人这么厌倦,他们明天也将继续生活吗?还是会突然有一个冲动,或者是错觉,马上关掉电视,改变,还是就这样戛然而止。这我都没有想好其实。
凤凰网文化:《自行车》这篇的札记写,余虹死了之后,刘明就会把浪漫视为一种不祥之兆,会不会你本来也只是想表达这个点?
于一爽:这篇小说当时在《收获》发了,当时发的名字叫《每个混蛋都很悲伤》,我觉得那个名字太抒情了,我还是喜欢《自行车》。这篇小说我也不那么喜欢,里面涉及到了太多的描写和抒情。比如说两个男女在中山陵骑自行车,每一路的风光,这是我写作经验里极度缺乏的,所以我当时这篇有意想写得很啰嗦。当时就是没经验,技术匮乏,又需要有个类似情节,人死其实就是最大的转折吧。
张定浩特别喜欢这篇小说,他说他不喜欢人死,但最后非常老土地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搭救了这种死亡,但我觉得这就是评论家的想象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让这个女的死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的死掉之后,男主人公身边又出现了一个男人,然后两个人可以非常云淡风清地谈论这种死。而且我现在觉得这篇小说头特别重,前面有十分之九写自行车旅行,后面突然急速下滑,有时候会觉得浪漫是不祥之兆,好的时候却觉得没那么好,没什么运气能够一直承担好的东西吧,就是觉得不配。可能我理解的那种挺迷人的男人都是这样,他应该不去表达感情,就是难过不难过,他还是会把生活应付地很好。
男人应该不会像我这样描写爱情
凤凰网文化:《打炮》里面表达了男人的感情,写他一夜情,他却回忆已死的妻子余虹,说他不会把对余虹的爱分给其他女的。
于一爽:对,我写作如果分三个阶段(天啊),《打炮》算第一个时期,就很杂。所以如果我现在重新写《打炮》,可能会写一个人不断地跟女人打炮上床,也不算麻木,他很卖力,但他也不留恋,我也不再跟读者讲他为什么不留恋,他可能有情感的前史,但可以留白了。当初是表达欲太强,说的太明确了,有这种生活的男的或者女的,应该会用自己的经历补充到空白里。
我第一个写作阶段的男人还挺像女人的,或者说整体三个阶段的男人都挺像女人的,因为我觉得没有男人会那么写爱情吧。我前两天在南京出差,很多男的跟我讲,男人和男人之间一起去泡妞啊,看对面房间女人洗澡啊,我觉得男人之间会写这种东西,男人写的感情或者是性可能更调皮一点。但是我描写的男人还是太关注女人了,是因为我太关注自己的感情,其实应该不会,他们应该只在乎自己勃起吧。
把性当做一种好玩的东西去写
凤凰网文化:但是你还有另外一种小说,两个好朋友终于有一次打了一炮,从此逃离。
于一爽:对,《同学聚会》那篇小说我唯一满意的地方只有一句话,两个老同学见面,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女孩,你一点搞她的愿望都没有了,可能很简单,就因为她有皱纹什么的,然后你又出门找了小姐。
顾前我很喜欢,他写的都是未遂的故事,就是男人对女人有想法,但是男人是很脆弱的,女人一个眼色让他觉得这件事不可以了,他就逃跑了,就未遂。他们说我写东西就是比未遂更往前一步,两个人做爱了,但也没什么劲,也不能改变两个人关系的实质,甚至又把这个关系固定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性没有起到什么很积极的作用。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未遂。
笛安说她认为好的性描写都是参与叙事的,还有人喜欢把性作为一种权力去写,我的小说里如果不小心写了这些,可能就是写到而已,我就觉得性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两个人之间那种试探、游戏。安东尼奥尼电影《放大》里面有一段摄影师和两个女模特,我不知道为什么拍那段戏,其实对剧情没有影响,可我就觉得很好玩,我希望写的性是那样子的,如果参与了情节,那可能是它正好在那个位置上。如果有什么能改善两个人关系,我觉得还是爱情,或者说运气。性就变成爱情一个必然的结果吧,没想清楚。
凤凰网文化:《钓鱼岛》和《地三鲜盖饭》里面出现了所谓的荒诞情节,《钓鱼岛》里面有熊熊大火,夫妻两个人特别无聊地看了一下;《地三鲜盖饭》里他跟女人约会的时候一直在想,送外卖的人为什么失踪。你写真的有一个重大的情节发生,但是也没有改变之前的生活。
于一爽:我本质上对荒诞特别感兴趣,虽然可能荒诞也有不同的定义。《地三鲜盖饭》不知道为什么写跑了,当时我是好奇,经常有人来家里送快递,他们为什么从来不会在北京迷路或失踪,他们甚至没想过有意失踪,也很难有意失踪。包括之前有一新闻,有一中学老师,平时是登山爱好者,后来失踪了,搜救几天认定死亡,很多朋友认识那个老师,他们说那个人的技术是不可能死掉的,他就是想消失,想离开老婆,离开孩子,离开父母,这样。他肯定是之前传达了某种想离开现在生活的信息,所以也给了别人这种理由。
安东尼奥尼《奇遇》里一个情节,上面写我女朋友失踪了,戏的下面写我和女朋友的朋友搞在一起,怕女朋友回来,你说这算完整结构吗?还是因为他是安东尼奥尼,所以别人就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结构。很多东西有没有标准?我觉得我应该确立一个标准,我本质随意,我就特别需要规定。
《钓鱼岛》,因为当时闹保钓的时候,我跟我老公住在26层,楼下在烧车,我们生活很平淡吧,就看着楼下那个火突然着起来,我们的车竟然也停在那排车里面,我一方面在想它会不会烧到我的车,但是这个担心只占很小一部分。我并没有让这场火去作用于故事。
什么东西会改变你的生活?当然现实中很大的事件冲击可能会。我们这种人可能太在意自己内心的想法,想去做或者不想去做总是最根本的,也没有把外界环境作为一个很大的考虑。但是如果我现在重新描写可能会更荒诞一点,在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里面,所有东西很中产阶级很平静,真的有人因为政治上的愤怒,甚至是被政治利用的愤怒,点燃了一堆车,点燃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但对波澜不惊的生活恰好形成了一个刺激,我觉得这个挺荒诞的应该。人的什么东西不会改变呢?比如说我是讨好型人格,没什么主体意识,这些东西都会跟随着我。
人是很卑微的所以更要保持天真
凤凰网文化:就像你喜欢跟娄烨用一样的主人公名字“余虹”,你的小说也跟娄烨的电影一样喜欢冒狠劲。比如《热天午后》人物莫名其妙地做一些事。
于一爽:这是我看了一个美国电影叫《热天午后》,很喜欢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有这个经历,炎炎夏日的正午,其实是很恐怖的,说不出来。但是这篇小说我前两天改掉了,改叫《三人食》,是“我”去一个女的家聊天,两个人的关系有点剑拔弩张,这个女人跟“我”说,她离婚了,她怀孕了,而且怀的是这个离婚男人的孩子。我特别想写,一种是你说的那种很无聊的,另外一种就是很卑微的,这两个女人都卑微,比如怀孕这个女人,她前夫来找她,她还是会跟他打一炮,她受制于这个人又不自知。“我”的卑微是很嫉妒这个女人,你有过爱情,有过固定的性生活,你离婚了竟然还能有性生活,就有那种不可遏制的愤怒。这个故事的另外一条线,他的前夫其实跟“我”有过有限的几次做爱,只是因为我真的是嫉妒,虽然我们两个是朋友。
其实我很少在小说里探讨女生和女生这种关系,但在现实中我能感觉到好多地方相似。最后两个女人有一些争执,“我”把她前夫叫来,可能怕这个女人出事,叫过来之后就更增加“我”这种卑微感,他们虽然离婚了,但是在他们原来住过的房间里,还是像一家人一样。我的位置就显得更加唐突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就去帮他们收拾一下厨房,看见有鸡蛋,就做了一盘炒鸡蛋,看上去很像三个人的温馨晚餐,我就觉得那个鸡蛋比得上古往今来所有的炒鸡蛋。
我觉得人是很卑微的,至少我对自己这样认知,人难道不是自我讨厌的吗?但我觉得这些东西还只是表面,我就很害怕在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里面,激发出自己那种恶的东西,就是很怕变得不善良吧。婚姻里争吵,然后诅咒,甚至羞辱,我就很怕变成这样,这就是刚才说的自我讨厌。我在乎善良,在乎智慧,在乎同情心,一个男人不管长的什么样,有没有钱,他要是四十岁还智慧,善良,有同情心,天真我觉得我应该会爱他。
总是描写悲伤可能是一种炫耀
凤凰网文化:《动物园》跟你刚才讲的很像,两个人各有心事,一起去动物园但是没去成。
于一爽:我现在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写《动物园》的时候,真的是处在一个谈恋爱的过程中,包括家人离世,感情上还是很充沛的。但是情节很弱,两个人去动物园,最后错过了,他们就在动物园四周谈论。当时写那个东西的阶段,我老想写爷爷死掉,但现在想这是不是一种炫耀呢?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亲人离世,但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正好是我有表达愿望和写作愿望的时候,我会把爷爷去世前后那些情感的经历,和这种死亡联系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看我爷爷,去的很慌张,因为我还约了一个男的吃饭,就下班坐地铁去看爷爷两眼,因为我觉得还可以再见,然后我坐地铁去约会,贴着地铁窗户,可能是想照镜子吧,就看到脸被刷刷刷迅速带过。现在觉得好像不值得,去找那个男的吃东西,应该陪更重要、更有必要的人待着,但是当时吃饭的愿望也很强烈。
我情节能力很差,有一个评论家鼓励我说你可以训练你的情节,也不用这么不自信,他们说你的情节转折点,可能就在语言上。比如别人写这个《动物园》,可能上一句和下一句是有逻辑关系的,但我可能没什么逻辑关系,反而丧失逻辑之后就到达了某种意外情节。比如我爷爷去世之后,给我妹妹打电话,我小时候跟我表妹是我爷爷带的,但是她在美国,正好在搬家,自己租了一辆大卡车,正在美国漫长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我给她打电话,但是两个人都不说话,拿着电话,电话费很贵,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东西讲出来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挺没意思,但是如果要我描写,我可能会首选这种东西,因为它给我造成的情感想象特别大,因为我不知道她拿着电话,穿过那些高速,车上放着自己在美国的所有家具,是什么心情。
犹豫的人都比较富有同情心
凤凰网文化:《酒店》讲的是女人,终于讲到女人了。
于一爽: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平常的,我觉得一百个人里一百个人都可以写这种情节,我写的很多两个人都是情人关系,我觉得这种不确定、不被合法的关系更有爱情。比如《酒店》,这个女人其实想跟这个男人挑明了,就说你要不要我一直陪你睡,你可不可以再对我有一点点耐心,或者我们两个人彼此有一点点约束,其实她是想跟这个男的说的,但在这个要做出决定的临界时刻,这个男的又走了,过两天回来,这个女的又会陪他,她又把最后可以挑明的时刻给浪费了,可能缺乏某种必要的品质,我可能也是这种人,没什么质变。
我觉得人其实都是很聪明的,其实想过代价,人哪怕最后做出一个懦弱的选择,他也觉得那个懦弱的选择比不懦弱更安全。我也想不起来哪篇,就是两个人想分手,她送他上飞机了,看着飞机徐徐起飞,突然恨自己,就觉得应该讲的话还是没有讲出口。我很犹豫,我也觉得犹豫的人可能都比较有同情心。这个场景有一点点现实原因,我在越南,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酒吧,闪烁着很粗俗的小灯泡,所有人领口有银边,但是我觉得那种粗俗很容易给我带到颇富深情的时间段。
女人根本不需要朋友只需要爱情
凤凰网文化:《长颈鹿》就是你第一本书《云像没有犄角和尾巴瘸了腿的长颈鹿》里的序言。
于一爽:对。那个也是最早写的有原型,我现在只是场景转换,就是我去一个情人家,想跟他说实际情况,但我看到他们的孩子,没有说出口,人物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又选择了不做,做了也未见得失败,但是不做肯定不会失败,那就不做了。虽然不会失败,但也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她宁可选择没有价值,然后继续生活。
我生活里好像也是男性朋友多,昨天我心情不好,一个男的跟我聊天说真想给你推到墙角,抽你十个嘴巴。如果把我的感情困惑跟女人讲,她们可能会分析认为是别人的不是,男人就会觉得是你要的太多,事实上我就是一个要的很多的人,他就觉得你需要清醒吧。我觉得女性根本不需要朋友,女性只需要爱情。
总是在写作中消解人物感情可能是种自卑
凤凰网文化:《俩人》跟《十年》很像,她终於找到了爱情,但是又觉得很无聊。
于一爽:这些是和《动物园》一起写的。我跟老公谈恋爱初期,大连有一个小巷子叫忠诚巷,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写一对男女在忠诚巷里谈论忠诚,虽然谈论的过程里没有忠诚,但是关系初期的彼此试探,女人一直坐在台阶上,后来站起来,感觉了一阵难以言状的空虚。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产生的不是满足,我也说不出来,写作只能尊重第一感觉吧,当时就是想到这个词了。
《三里屯》写的也是这个。我对三里屯并不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大而化之,它就是世界中心。对于三里屯我能记住一些场景,比如说有一次跟一个男的在三里屯喝酒,后来下雪,他出门摔了一跤,就跪在地上了,他摔下去的姿势就真的是跪在地上,他迟迟不起来,可能他太疲惫了吧,他突然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我有家庭很可耻?我记住这么个场景,后来写到小说里。还有一次跟一个男的喝酒,出来之后他说,我能体会到三里屯也挺无聊的。只是借用那么个场景吧,很多人对声色场所有误解。
前几天杨葵跟我说,说我写一个男人哭了,甚至都不给他一点空间让他哭一会儿,马上下一笔就写可能是风把眼睛迷了吧。杨葵就说你为什么没有这种自信让人物哪怕哭一会儿,但另外一种,这种迅速转折代表了某种自我解构,你不希望人物占据任何一种情绪和极端。但事实上我下笔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一旦冒出一种崇高的感情,我就马上给它消解掉,不然会感觉很不安,会有损我人物的美感(我好自恋)。
就像《马桶垫》讲的是,这句话可能说出来很粗俗:有时候看着马桶你很奇怪,它会不会想吃屎。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状态,比如说你刚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甚至都不忍心在他家穿睡衣甚至卸妆,可是后来你跟他长久生活,两个人聊的竟然是你帮我挠后背啊,或者我这两天皮肤搔痒你帮我买药。“搔痒”这个词很日常,但我还挺愿意写,很多人不想把这种丑陋的词写在小说里,但我觉得非常好。
写作就是一场超级自恋和虚荣心
凤凰网文化:韩东、曹寇等等给你写的那几篇书评,你同意他们的说法吗?
于一爽:小安有一句话很特别,一般我们正常逻辑是玩一下过后就忘掉,她说我们来玩一下,过后也不一定要忘记,我写的很多就是人在游戏里面,最后他不说,但你根本忘记不了这个游戏。
写东西就是一场巨大的自恋和虚荣心。为什么不放在抽屉里?我原来是抱着这个性质去写,但现在突然被一些人看到,一旦被他们看到,这件事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反而就有点难了。
人要靠局限和缺点活着
凤凰网文化:你以后还打算写男女关系吗?
于一爽:我之前也说不想写,可以写的题材有很多,比如说我想写1983年,我出生的前一年。但是没有什么会不涉及男女关系,比如去东京到处都是霓红灯,可是我就觉得好安静,东京的年轻人很漂亮,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很多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可是他们恰恰是不做爱的,这个是未来的某种方向吗,人对性的需求越来越少,或者说他们有各种解决性的途径,性已经反而不需要。但是我挺喜欢这东西的,就是人对自己不满吧。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看纯文学?
于一爽:纯文学确实没有定义,我很喜欢人的弱点,就是认真面对真实的东西。比如认真面对自己的懦弱,自己的虚荣心,自己的强烈的愿望,我就很喜欢这种东西,会迷恋,因为这些东西不会让人舒服。他一定要追求一个不让他自己舒服的东西,所以我写的人表面还挺平淡的,可内心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要真平淡就会很舒服,很舒服就不值得写作的人描写和同情他了。我觉得人就靠局限活着吧,我以后就要靠缺点活着。
于一爽,作家、媒体人。
《年代访》为凤凰文化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