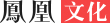徐皓峰:中国最早的侠客带有青春荷尔蒙色彩

(图片来自网络)
徐皓峰最近有些忙碌:陈凯歌的新片《道士下山》,他是原著作者,虽然没有参与编剧,但影片最后呈现出来的奇异面相,还是令各家媒体希望从他嘴里听到评价;身为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他拍过两部武打片,都是改的自己的小说,但因为没有走商业化路线,影响范围始终有限,现在他的第一部商业电影终于要面市了,离公映还有不到半年,目前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中;而这部新片的原著小说《师父》,6月又刚刚获得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说双年奖。
徐皓峰算是个“奇人”,作家格非曾说:“这人是个天才啊,怎么什么都懂!”他自小习武,后来又学了画画,最终念了导演系。毕业后写剧本没有要,各处谋生,最后觉得实在无趣,索性躲回北京的老胡同,钻研起道教来。再后来,他把听到的民国武林旧事写出来,成了一本《逝去的武林》,畅销之后的多年间一直是只闻其名无处求购的传奇。他又回到电影学院,开始写起《道士下山》。小说出版后,王家卫读了,找他做《一代宗师》武术顾问,时间一久,也就成了编剧,自此“徐皓峰”这个名字为大众熟知。
在徐皓峰对老派武人的记录中,经年习武之人可以通过武术调整呼吸,改变气息运行方式。不知这一点是不是也在他自己身上得以实现,不过他说起话来倒的确总是不急不躁,徐缓而沉厚。言谈所涉,则和他的小说相近,博闻广识,驳杂旁出;有的地方又像老派人一样,谨守规矩,笑而不述。与他聊天总是充满了你没听过的故事,这些故事的精彩完全不靠叙述技巧的渲染,而只是因为在那故事里,有一个已经离我们远去、曾经也未必显而易见的隐蔽世界。
(采访:徐鹏远)
自己不拍《道士下山》 因为喜欢陈凯歌的《孩子王》
凤凰网文化:您自己看过《道士下山》的电影了吗?做何评价?
徐皓峰:因为我是原著作者,按照影视圈的行规,自己人不评价自己人,所以抱歉,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回答了。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拍了三部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却没选择《道士下山》这个本子?以后会自己再来拍一遍吗?
徐皓峰:我自己不拍《道士下山》,因为喜欢陈凯歌的《孩子王》。
新片《师父》用最古典的叙事和表演方法
凤凰网文化:《倭寇的踪迹》《剑士柳白猿》获得业界好评,但因为商业化等原因并没有太多影响到多数观众。新片《师父》在演员阵容上已经看到商业考虑,那么除此之外还会有哪些区别于前两部的不同之处?
徐皓峰:《倭寇的踪迹》的电影形态基本上是话剧空间,《剑士柳白猿》是一个画面构图的电影,也就是以话剧空间和电影的画面构图来表情达意,而不是常规的剧情交代的层次来完成故事和主题。
投拍《师父》时商业性的考虑并不是用明星来说服投资方的,因为武打片已经式微,香港人拍一部式微一部,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拍武打片,其实他们看中的是别的东西。
我要把《师父》做成一个正剧,因为商业市场里充斥的是喜剧形态或者是强度的类型片形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是高度中国式的类型化的,不是生活常态的,剧情演进也不是按照古典的剧情逻辑来演进,是跳进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用最古典的叙事和表演方法做一部电影,本来这是最常见的,但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电影最常见的东西见不到了,最常见的反而可以称为奇兵。所以这部电影的商业性不是它的商业元素,而是它的叙事形态和电影形态。
这是电影整体的处理上,在武打形态上《师父》也会和我的前两部电影有所不同。《倭寇的踪迹》是一部戏剧空间的电影,这和我早年当过话剧导演有关,就是说它的武功可能是真实的武功,但表现武功的镜头和节奏方法其实跟《茶馆》第一幕的打戏的处理方法,包括一些话剧的处理方法,在理念上是相通的。《箭士柳白猿》是构图电影,在情节叙事上是留白式的,你只有情节留白,画面构图才能够起作用,不然观众就会淹没在情节上,所以我是靠画面来完成叙事和故事演进的。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箭士柳白猿》虽然用的是真实的武功,但呈现出来的形态是画面式的打斗,看完这部电影就能知道。就是说表现一个武打动作,要追求这个武打动作在全景画面的最佳位置,是这种东西。
《师父》在剧作形态上是正剧,在武打形态上是正拍,同样是真实的武打,但是拍摄方法用正写,动作是靠挖掘形态本身出现魅力,而且这个魅力是跟港台不同的。
现在中国文学其实是学《圣经》叙事
凤凰网文化:您写武林小说是从口述史转换而来,而且自己也说过得意的不是制造故事,而是武术的知识点,常常身不由己,到哪是哪。所以这也导致小说常常呈现出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比如结构稍显松散、人物容易仓促,就像陈凯歌说《道士下山》里许多人物像一把珍珠撒出去,有去无回。您自己对此有何意识?未来的写作中还会追求这种风格吗?
徐皓峰:这个问题是看以何种文学标准来看待的。现在中国文学,尤其是指通俗一点的大众文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向西方的通俗文学靠拢,向好莱坞影视靠拢,追求人物、意义、最后的高潮,这种文学观其实就是《圣经》叙事。
但是中国不是《圣经》叙事,中国的文学传统是笔记体小说,所以我在一开始写《道士下山》时就不是按《圣经》叙事来的,也不是按章回小说的方式,章回小说要求事件和人物的连贯性,我的方法是笔记体小说。
你看传统的中国字,每个字平均要用二十多笔才能写完,单个的字这么复杂,所以中国文学一定是无长文的。我这么多年的写作一直追求这样的东西,对于人物并不是太喜欢做解剖学一样的剖视,无非是人物性格成立、最终要表达一个什么意义、性格解构是什么,我上电影学院时受的剧作训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既然写小说,就不搞这一套了。
民国时军界政界的中外比武搞了很多
凤凰网文化:陈凯歌接受采访时说,从《黄飞鸿》以后武侠电影只有一部《功夫》不错。您对这二十多年来的武侠电影怎么评价?当然您说过一些总体概括式的观点,我想听听具体的点评。
徐皓峰:这二十年来是武侠电影的衰落期和转移期。中国有句话叫“风水轮流转”,最早武侠电影发源于二十年代末的中国大陆,但到三十年代初被国民政府禁了,四十年代末在香港复兴,一直到现在。1992年香港武侠电影的风潮就过去了,香港电影又崩盘,之后武侠电影的创作就再也没有形成香港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潮流,武侠片变成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了,周星驰拍了一部,张艺谋拍了一部,陈凯歌拍了一部,武侠电影作为一个商业类型在整体上已经走向没落了。
凤凰网文化:黄飞鸿、霍元甲、叶问等题材的电影都喜欢设置与外国人比武打擂的桥段(李小龙电影几乎直接以此作为主题),大家看多了就会腻烦,于是开始讨论这是一种自我意淫,包括讨论中国武术的实战价值并不高,拿来和泰拳、拳击、现代散打做比较。这里当然有些刻意而为的矫枉过正,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中国武术的实战价值怎么样?
徐皓峰: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到我们回忆一些年轻时代的事情,会觉得你们七十年代的人是不是太敏感了、总是阴谋论,因为他们没有冷战的生活记忆。而我们是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尾巴,有这个记忆,所以我们更能理解清末和民国时,中国作为一个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国家的处境,现在的小孩连这个处境都否认掉了。当然现在外国变得很好,但是事情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民众之间的交流和好感,上升到国家高度,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争夺,新一代的年轻人要对这一点有体会,不能做老好人,不能天真地想事情。
电影靠打外国人获得观影观感,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不良心态,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在面对外国人时确实有人种上被看低的羞辱感和不平感,这是一个历史。像韩慕侠打败俄国大力士、霍元甲打败外国大力士,这样的发生在民间的比武事件其实非常少,遍查当时的报纸等历史资料打败的外国人只有两三个,这样就会让人否定中国武术的实用性。但是其实在民间口传,和五十年代的交代材料--五十年代都要向街道办事处和单位写自传,说是交代材料也可以,基本都提到了一件事情,说当时北京武术界但凡有点名气的武术家都经历过日本人用重金买艺,就是花钱买武术套路和练功秘诀。日本人还登门比武,如果输了不是扭头就走,而是一定要跟你学的。还有当时的南京政府跟俄国的特工、军校部门比武和交流非常多。
所以发生在民间的事情寥寥无几,霍元甲那种就是个民间艺人,可以让老百姓看见,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砸了外国人饭碗。但是在军界和政界,中国拳大胜日俄都是留存在政府记录里的,因为是政府行为,所以老百姓见不到,。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的历史证据和来龙去脉,我已经梳理出来了,写在我的新书《坐看重围》里。
靠武术改变国民性是清末民国社会的共识
凤凰网文化:民国习武之风盛行,武术称为国术,包括在政治和国家层面,比如霍元甲的精武会就和陈其美有关,背后其实是一种民族复兴、强壮国族的意识形态。最后到底起了作用没有?
徐皓峰:这个还是起到很大重用的。因为民国时候的中国人,延续到朝鲜战争,整个民族有一种尚武精神。清末之后历届政府培育民间的尚武精神,才能让中国向后支持长达三四十年的战争。
因为靠武术改变国民性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共识。“国民性”这个词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是到中国来的一些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有一个共同点--一直说中国人坏话,所以发明了“国民性”,后来“国民性”这个词被梁启超、鲁迅、胡适他们继承。国民性在他们的手里成了一个有政治改革意义上的词,它的顺序是:先改造国民性,再带来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之后就强国强种了。当时他们认为西方有非常先进的政治制度,但是因为我们的国民素质太差,所以这么好的政治制度我们用不上,几次宪政和议会实验都很失败。所以当时培育武德,通过强健其体魄来振作其精神,成了当时上上下下改造国民性的风潮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孙中山给武术界提的词直接就是“强国强种”,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大的社会共识里的东西。
中国最早的侠客带有青春荷尔蒙色彩
凤凰网文化:从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开始,侠的概念就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学之中。而且从《游侠列传》以来,中国的侠就一直是与权力相对的一股民间势力,是庙堂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在王学泰先生的研究当中又是和“流民”概念紧密相关的。但是中国却没有发展出日本那样一个武士阶层,更没有形成武士道那样塑造民族性格的价值基础。那么中国的武和侠怎样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建构和民族性格的养成?程度和影响力有多大?
徐皓峰:因为中国的侠不是蝇营狗苟生存的流氓文化产生出的。首先中国的侠不是贵族,在经济上多是居民,或者是从居民圈里被赶走的青少年,所以中国的侠非常类似于嬉皮士或者摇滚乐手,是主动地选择了反社会的叛逆色彩。
可以举个例子,清朝时汉人都住到南城、外城,内城都是满人,满人自己也出侠,他当然也主持正义、抱打不平,除此之外,最典型特征一定是反讽挑衅皇帝和官方权威,这个更多时候是一个性格、是一个时髦,因为这种行为有一种青春荷尔蒙色彩,他首先是完成自己的个性,然后间接地帮助了老百姓。所以其实中国最早一批侠客,春秋和汉代的侠客,他们都是性格非常偏激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最时髦的人。
后来在香港电影里,“侠”的概念就跟西方吸血鬼概念一样,就是发生了一个近似于吸血鬼的变化。因为吸血鬼本来是阴森、恐怖、丑陋的,但是这个形象再往下发展,都带有贵族文化的特征,倒是吸血鬼继承了贵族的形象。中国的侠也是一样,侠最早不是欺男霸女、占人小便宜的流氓草寇,而是偏激的、激昂的少年,或者虽然是个老头但依然保持着少年之志,他本身并不见得是贵族阶层,而是城市平民。所以像在嘉庆、道光年间,住在北京内城里的那些侠客,一天到晚讽刺咒骂皇帝,皇帝也容他。中国社会里专门有这种人,见了皇帝不磕头,他要完成自己的个性,但是在以前的皇权里也容这种人,不跟你争执,你犯浑就犯浑。
但是后来在香港文化里,出身不高的侠普遍都带有贵族特征,白衣胜雪啊、行事作派讲究啊,属于贵族王公的行为特征、说话方式和思维方法。
日本崇拜的不是武士,而是贵族,而这种贵族文化是来源于中国唐宋,所以在日本老百姓崇敬的是王公,武士是王公的附庸,是社会的中下层阶级,武士在日本文化里从来不是偶像。
日本的武士道是明治维新之后生造出来的。因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把以前的王公、军阀集中到一起养起来,所谓华族,一定要瓦解公卿和军阀的势力以及社会影响力,派他们到外国留学去了,而把以前社会地位并不高的武士阶层给提升上来,成为一个文化偶像,这是他的一个文化策略。
国民性这个问题,除了中国,韩国和日本其实一直延续西方思路,武士道是日本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政治步奏。现实中,武士生活得都非常惨,但在文学和宣传上,把武士的地位抬得非常高。
所以中国清末时鉴于日本成功的改造了国民性,梁启超他们直到民国时孙中山才把发展武术作为基本国策,就是参考明治维新,日本明治政府创造了一个武士道文化的巨大谎言,但是这个谎言成功地改造了日本国民性。这个就造成了在民国时,武林人士像现在的歌星影星一样,是社会的明星。
金庸写的是幼稚男性 古龙是受日本影响
凤凰网文化:《一代宗师》编剧一栏里有三个名字:您、邹静之、王家卫,还有一个文学顾问张大春,你们之间究竟怎么分工?
徐皓峰:这个是王家卫的统筹安排,所以有机会让王家卫解释吧。
凤凰网文化:张大春写过《城邦暴力团》,其实也是一种创新的武侠写法,和你的小说一样的是,他也融进了史实和政治。您怎么评价他这部作品?
徐皓峰:因为有一个行规的常识,作家、导演之间都不能相互评价,所以我实在抱歉了。张大春是我很欣赏的作家,他的典故无穷无尽,所以看他的书给我很大的快乐,也能长不少知识。
凤凰网文化:古龙谢世、金庸封笔之后,武侠小说尚无足以继任的新宗师,武侠文学的类型也基本没有跳出他们的模式,这其实也是您的作品近来受到关注和讨论的原因之一。就您的了解,目前有没有值得期待的其他武侠小说家?武侠文学未来可以从哪个方向取得突破?
徐皓峰:金庸和古龙各有不同的文化渊源。
金庸小说里的英雄豪杰往往是性格上不太成熟的人,这个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就是,香港电影里的英雄、大侠都要回忆童年,保留着儿童的种种特征,这个是香港文化的特点,它的大众英雄一定要带着儿童的特质。所以金庸的人物也是这样,他实际上写的是幼稚的男性,是青少年。
在武功形态上,金庸继承的是还珠楼主,他的很多武功其实是巫术或者神仙术,跟《神仙传》是有直接的血脉联系的。
古龙的武侠,因为日本撤出台湾之后,日本电影还持续的大量的涌进台湾,所以台湾一代青年受日本电影影响非常大,以至于造成古龙小说里的有些人物性格是日本人的性格,他对武打场面的写法是日本的浪人小说的写法。所以金庸和古龙背后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渊源。
我的写作基础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想跟他们一样我也学不来。从八十年代之后,模仿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非常多,但是没有成功者,不是说文学才华比两个人弱,而是他们文学背后的文化是你所没有的,所以你模仿他们模仿不出来,而且从他们往外走你也不可能有新的变种和新的发展。因为金庸和古龙,这两个作家都自己说自己变不出来新的东西了,所以金庸封笔,古龙不再写长篇武侠,连他们自己都变不出新的东西了,更何况我们呢。
机缘巧合,我的文化基础主要是民国时期北京和天津这些北方武林的口述历史,所以这个没有谁强谁弱的问题,而是大家的文化基础不同,将来隔代还会各有发展。
(特别鸣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徐皓峰,1973年出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现就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导师。中国内地导演、编剧、武侠小说家。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其《逝去的武林》开创了中国武侠纪实文学的风气之先 ,武侠小说《道士下山》更使得硬派武侠小说重新占据文学市场的一隅之地,引起巨大反响。徐皓峰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风靡中国文学界。在电影领域,2011年,其首执导演的古装武侠电影《倭寇的踪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该片入围威尼斯和多伦多两大国际电影节,并斩获多个奖项。2014年,凭借《一代宗师》荣获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同年,首次涉足商业电影,执导拍摄“武林传奇”巨制《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