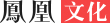83岁林文月:中日“摆渡者”的文学风景

林文月近照
论述、散文、翻译,林文月先生专擅的三种“文笔”;也正是藉由经年累月、谨严琢磨的三种“文体”,林文月教授凝思运笔,营构了纷繁婉丽的文学之“理型”(Idea)的世界,并以“一支敏感而温柔的笔”(余光中语),与事态人情、风景况物,做不倦的倾心交谈。
与通常的先沉湎浸润文学创作,再于学院训练中转向学术论文的写作的习常情形不同,林文月“正式”的文字创作是从学术论文开始。她首先面对的是台大中文系的本科及研究所要求的课业论文,在夏济安先生的《文学杂志》上的投稿也都是学术文章,而这也成为文星/洪范版的《澄辉集》、纯文学/三民版的《山水与古典》等著作的理路渊源。
1969年,已在台湾大学中文学系任教的林文月到日本京都大学访问一年,进行题为《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之影响》的专门研究,却促发了林先生的另外两项创作:一是因林海音先生之约,每月于《纯文学》月刊发表一篇叙记京都情状的散文,一年的连载,得《京都茶会记》、《奈良正仓院参观记》等十五篇,所结集而成的,就是散文集《京都一年》,这是散文家林文月晚成的“初作”,也是《午后书房》、《作品》、《回首》、《交谈》、《人物速写》、《饮膳札记》等一系列或清通朴质、或丰美厚重的名作发轫之处。京都之行的另一项新进展,则是因其对平安文坛的研究中,必涉及平安时期的重要著作(亦为日本文学的经典之作的)《源氏物语》,一年的旅居时光使得林先生有时间和精力通读、细味这样的大部头之作,也才有了后来《中外文学》的邀约下以五年半的时间“马拉松”连载《源氏物语》的全部译文,并继而翻译出《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要津,使得日文之经典再获中文的神韵。
凤凰文化对林文月教授的访问,是在她到港参加台湾目宿媒体新推出的“他们在岛屿写作Ⅱ”系列文学电影中的《读中文系的人——林文月》的首映礼之时。在访问之后,林先生还特别参加了由董桥先生主持的对谈活动,其间列席的嘉宾,除港大、中大的校友、教师外,还有著名的“写散文的明星”林青霞女士。虽然有重头活动等待,今年已经是“八十(岁)后”的林文月先生仍旧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一切的问询、思虑,就从她出生在上海日租界的往时往事,延拓开去。
上海往事:从“战败国日本人”到“战胜国中国人”
凤凰文化:林文月老师,在台湾的作家里面,您的日语经验和日文的修养都很特别。特别是您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同时会做很专业的日本文学的研究跟翻译,这其实是您的文学历练的一个尤其重要的方面,这应该是跟您个人的成长环境分不开的。
林文月:身在中文系而跨行去做日本文学的工作,这已经变成我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先讲一讲我为什么会以中文系的人而做日文的研究,或者是翻译。这是因为我的生长背景,我是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出生的、台湾人的女儿。在那个时候所有台湾人都是日本的国籍,那是因为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控制,我们那时都算是日本公民。虽然我们是在上海,但是我住的是上海的日本租界。我从出生开始,我的第一母语就是日本话。我在家里有时候会听爸爸跟妈妈讲一些话,尤其他们不想让儿女知道的事情,他们就偷偷的用台语讲,慢慢的我们也就会听了。
还有一种就是跟附近的或者是家里帮忙的阿姨,他们讲话就讲上海话,这三种话是我一开始会接触到的,很自然的会的一些语言。
凤凰文化:对于您真正的母语,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并且熟悉起来的呢?
林文月:母语,你说的是中文,那就要到我10岁、12岁的时候。日本败了,我们就变回了中国人。很有趣的是,也有一点伤心,因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的台湾人很快就变成了中国人,对我来讲我的记忆是这样:我在上海的日本学校读书,有一天学校播放广播,叫我们学生老师都到礼堂,去听很重要的天皇报告。我们就都到那里去了,不久日本天皇透过无线电给全国,包括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宣布日本无条件的投降。我的周遭、我的前面,我的老师们他们就开始哭泣,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受到这种感染,大家哭泣,我也哭泣。因为我觉得我是战败国民,怎么办?可是过不了多久,台湾人现在变成了中国人,“我们”又成了战胜国了,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要改变这种情绪,这对于小孩子来讲是有点奇怪的。我在我的小学里头只有我跟我的妹妹是台湾人,其他全部同学都是日本人。一下子间,我们就从战败国的子民变成了一个战胜国的。可是那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的上海人,就对我们有一种很不谅解的看法,说你们这些人在那里插太阳旗,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战胜国呢?你们是汉奸走狗。在上海的台湾人也有一点很不能够适应,当时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威胁的。
凤凰文化:当时的日租界的台藉人士,比如您的父亲,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回应这种国族认同的问题呢?
林文月:当时包括我的父亲在内,有一些日本籍变成中国籍的台湾人,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团体,想要表示一下我们会效忠于中国,于是他们找一个小孩子,少女献旗,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献给当时接管的将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需要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去献旗,我爸爸看来看去发现我的年纪正好合适,所以就带着我。那一天很紧张,一群叔叔伯伯带着我去原来的海军陆战队——现在变成将军所在的办公室。原来日本的孩子上学时经过那个地方,是要向警卫的日本兵来鞠躬的,后来我又以中国人的身份代表去献旗,说起来也是很可笑。而有因为是仓促发生的事情,我的发型还是标准的日本女孩子的那种发型,制服也是日本学校的制服,来不及换别的衣服,我们就去了。
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中国国民。但是街上的人不太习惯这样,我们也有一点不习惯,他们还是会常常会骂我们是日本的走狗、是汉奸等等。我父亲得知形势的改变,他就带着我的妈妈到法租界暂时躲避一下,家里一些佣人和我哥哥,比较大的孩子在家里,还是守着。但是后来也不敢再住上海了,太危险了,我们虽然变成是中国人,还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所以匆匆的,我父亲洽商他的上海朋友,他们有小船,是专运火柴的到台湾去。我们其实跟我们其他的亲戚,不超过15个人,坐那条船,跟满船的火柴一起,一路上走走停停,到了台湾。

林文月旧照
凤凰文化:当时是从哪里登岸的呢?上岸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是不是跟之前想象的“故乡”有很大的差别?
林文月:是到的基隆港。靠岸的时候,我看到岸上的人跟我们以前看的人不太一样,当时我们离开上海,是在二月的时候,我母亲穿的还是皮大衣,因为上海的天气很冷,我们也都是很厚重的衣服。可是基隆的岸上一些小孩子穿着短裤、短袖子的衣服,戴着一个木箱子卖冰棒。我想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是我的家乡,我们上去以后坐车子,一路还看到山,在上海举目就只是看到房子,一层一层的房子,比现在的香港当然是差了很多的,但是看不见树、山。
到了故乡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新鲜。然后我们就去读台湾人的中国学校,因为那个时代不准讲日本话,而是想要赶快推行中国的国语。我到了台湾,在六年级的国小上课;我们的老师其实也是一样,突然转变成为中国人了,中国国语怎么讲,也不是很清楚了,所以他们要教国语的时候,头一天先去补习,第二天才来教我们。因为不可以用日本话解释,他们就用台湾话讲课。可是,对于我来讲国语我也不懂,台湾话我也不懂,所以第一次的考试我不及格,这是很新鲜的,当然有一点难过。同学看到我是从上海来的人,他们就会问我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上海的钟都是金做的呢?我也不知道,我平常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也好奇,但是他们问我的问题我几乎都答不出来,我觉得我跟你一样可以讲日本话,但是不可以,老师也不可以讲。他们讲台语我也一知半解,所以我觉得我小小的年纪,一会儿这样的人,一会儿是那样的人,变来变去的,我都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
翻译本事:始于《长恨歌》与《源氏物语》的渊源
凤凰文化:是不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让您对日文和中文,都有非常特别的感受?
林文月:对。在还没有认识“翻译”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其实长期一段时间都是把语言在脑子里翻来翻去,这样我才能够生活。到了很后来才明白,虽然我只读了那么一段时间的日本学校,但是那些重要的文学作品我都有试着翻译出来,原来“翻译”这件事是一开始就跟着我的。
凤凰文化:也就是说,那种“状态”是自然而然的,甚至是潜意识、下意识的情景之下,一种语言寻找另一种语言的感觉?
林文月:确实是这样子。你看,在语文方面,我是学到日本的小学五年级的上学期。我记得最后读的日本的国语课本有一首和歌,我现在还记得。我上和歌的时候,在上海的日本国小教我们国语的那位老师,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可是他教我的那首和歌,我本来觉得我根本没有记得。可是有一次我在台大留校教书以后,有一个机会到九州大学去,有一位历史教授他知道我的生长背景,就带我去看一棵梅花树,坐了好长时间的车子到那里以后,他说我就是要带你看这棵树。他说这棵树是有一个历史来源的,他要开始讲,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知道这个,我想起来了,这就是那首和歌的典故。我在那个时候就想起来,那首和歌的最后一句我还能记得,我想一想,第二句也记得,前面一句也记得,我自己当初是把和歌分三段来翻译的——所以最后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三句我就统统都会了。
凤凰文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就不难理解您为什么读中文系,但是后来又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是翻译了像《源氏物语》那样的名著。不过,从读台大的时间上看,您其实比白先勇、李欧梵老师他们都早了几年,不知当时您在中文系的教育系统底下,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是怎样的?所以您那个时候的台大的氛围是怎么样的?
林文月:先勇是念外文系的,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会互相串系去听课,但两个系的确是不太一样。台大中文系是非常传统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要读古典的中文,甚至于从文学史的角度,《红楼梦》以后我们都没有开课。当然那时候也跟政治的立场什么的有关,都有一些敏感的因素,包括到我留校之后,也还是以古典的东西为主,像先勇他们的《现代文学》,就非常求新,那也是受当时去到美国的夏济安先生的鼓励的。
凤凰文化:那么,又是一个怎样的机缘,让您开始做翻译了呢?
林文月:那是因为在1972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个国际笔会,台湾也有一些学术界的人去。那一次笔会的主题是发表各个参与国跟日本的文化,或者文学,或者历史,有关系的论文。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用日文先写的,讲中国文化,尤其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对日本文学有很深厚的影响力,最明显就是《源氏物语》的第一篇,它就是要写一个皇帝宠爱他的妃子,就好像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这些故事处处可以看到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我以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关联,讲到两国之间文学的影响。开完会以后我回到台湾,我试图把这篇一开始由日本写作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当时只是想,翻译过来还可以让读者看得到、看得懂,特别是我所举的例子,很少人知道是《长恨歌》对于这种《源氏物语》的影响,甚至《长恨歌》的诗句有的时候就明明白白的出现在那里,天皇的妃子好像是杨贵妃的影子在那里,天皇就是唐明皇一样子。尤其是白居易对它深远影响,这是很有意义来谈的。
这样子我把它匆匆忙忙地翻译成差不多一万字左右的中文,登在台大的《中外文学》。哪晓得大家很有兴趣!倒不一定是我的论文写得多好,也许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讨论日本跟中国有关系,而且又不是那么大略的,没有细节体现的,而是通过《源氏物语》的文本这样子呈现出来的,很奇特的东西。
后来编辑就收到很多人写信,打电话等等,都是说催促这个人林文月再把它后面继续翻译下去。后面是一大条尾巴,全书54篇,我只是翻译其中的头一篇。后面有没有能力,要多少时间,我都不知道。外文系系主任,就是那个学术杂志的主要负责人,他很诚恳地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你能不能翻译了?我说你不知道这个后面的翻译是多大的事情。他说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本来就很不会讲话的人……讲讲讲,我就说那我就试试看吧,然后就扛下来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那实在是很辛苦,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凤凰文化:当时虽然是非常“艰巨”的翻译工程,您又有自己家庭的事务,不过您还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翻译的“创作”。
林文月:我大概有一点点傻气,我觉得既然答应了就要继续做,每个月一帖。有的篇目是四万字,我就分成两次或者三次,每月刊登。还真有人要看,认真的看,其中包括我当时的系主任。
凤凰文化:也就是台静农先生?
林文月:对,因为他自己很喜欢书法,也是书法的专家,所以他说“这个女作家”,那指的不是我,他讲的女作家是原作者,紫式部,“真了不起”。他说她讲书法的问题,三两句简单的话就把精髓给讲出来了。台先生很知道书法的这种特质,所以他看到对的说法就会去赞美这个作者。而作者怎么样让台先生听懂,那就是我。
我不懂书法,只是我很贴切地表达“她”的原意,尽我的努力,很直接的,很贴切的把它原来的说法都变成中国话。所以听在、看在中国的书法家,像台先生这样的人就会觉得我做得很好。其实我哪里懂书法,我只是看她怎么讲,我就去抓住它。仅仅是这样而已。
凤凰文化:那就是这样以连载的方式把大部头的《源氏物语》全部翻译完成?
林文月:那段时间,是连续的。除了《中外文学》要来做一个什么专刊的编辑不需要我供稿,才会让我休息一下。可是我教学时私下里偷偷的去做,放暑假我更偷偷的做,所以我一直有一些存货,不怕他们逼稿的。就这样,五年半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断过任何一期,五年半连载完,洪范书店就把书出版出来。后来大陆也出了简体版。
京都文事:京都一年成全人生第一本散文集
凤凰文化:《源氏物语》的翻译完成,可以说是您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性质的时刻,但是这次“翻译”的动因,却是在您之前到京都访学的时候就埋下的。
林文月:那倒是确实,那一次京都的经历改变了我很多。因为像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人,在我们那个时代并不被鼓励创作太多,像台先生自己以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家。但是我们到后来才知道,他原来也写小说。同样的我们觉得在中文系教书,就是要做文化的传承,做伟大的工作,所以写论文是最重要的,而且写论文的笔法跟普通的创作应该也不一定要相同,或者是要不同:所谓要理智、要清楚,要有详细的交待。
我自己那一年的生活的话,读《源氏物语》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侧面,我到了那边,整个环境变了,变成只有我自己,可以好好地把那么大一本书从头到尾读,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可是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在1969年到1970年,那时候我得到一个机会,国科会让我到日本去做一个研究,不必教书,照样有薪水给家里的人,我可以在日本自己过日子。但是那个时候我接到这样的消息,我的系主任打电话,告诉我这笔经费已经通过了,我可以到京都。一大早接到这个电话,我真的很天真,我说主任请你等一下,我去问问郭豫伦——郭豫伦是我的先生。我把郭豫伦摇醒,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怎么办?系主任要听我的答复。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让系主任为这个事情在那里等你,你先去答应他,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两个孩子,大的小学一年级,小的还在幼稚园的小班。所以我想我怎么可以自己跑到那里去,我先生说你快去答应了再说,我们再想办法。
凤凰文化:所以后面的“办法”是想出来了的。
林文月:后来我就是把家里很多责任交给我的先生,自己一个人去京都那边。在那边,我一个人只要写一点原来计划的论文就可以,时间比较多,也不必炒菜给全家人吃,可以简单化了。所以多出来很多时间,我不晓得怎么办。正好碰到一个从美国到京都做论文的一个台湾出生美国长大的女博士,她在写博士论文。我们在图书馆认识了之后,假期常常有各种空闲的时间,我们结伴而行,她很会找路,很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调、山水名画,各种各样的。因为她的日本话比较差,但很懂资讯,现在的讲法就是“达人”,而我可以讲日本话,但路不认识,我们俩一搭一档,常常一大早礼拜天就出去,就逛街,看这种平原、山川,或者是说很有意义的古迹,甚至还去吃日本料理。
另外一端,就是我在去京都之前答应了林海音先生,要给《纯文学》杂志写稿,她叫我不要一天到晚写好多好多注解的论文,“你写一点这种好玩的,大家喜欢看的文章。”我就说好,她说“每个月都要来稿”,我说好。就这样我就变成了除了写论文以外,每个月要写一个主题,但是是散文。
凤凰文化:所以这个就是后来结集了的《京都一年》?
林文月:对,我第一本散文集。
在我个人来讲是一个从论文到散文的过渡,那是我很认真的,很多散文的后面都有注解,也就还保留着论文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没有交待清楚不可以,尤其日本人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很多地方、很多事情都跟中国有关系。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在做学问,可是我已经养成了那样的习惯,所以要交待的清楚。我希望不关心的人可以不要看那个注解,但是如果想要追究,我在写的时候就已经去翻查那些资料,我就给你准备好了在后面,至少你可以有一个地方去查询。这也是很必要的。
凤凰文化:所以您就是用散文的方式做了非常珍贵的两国文化的互动的观察。
林文月:那个时候在台湾也不容易到外面的,所以我彼时的写作,还有帮大家开眼界的作用。住在京都一年,而且住在一个普通老百姓住的地方,我整个融入在他们的圈子里,我相信我当时是走的很深入了。不像普通的留学生住国际学社,在那个接触最多的是中国人,几年下来进步的是中文,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
凤凰文化:其实我们这样一路回顾下来,您的脉络也就比较清晰,特别是您会特别地把散文和论文做一个对照,而从您所从事的职业,也就是文学教授的角度,学术论文应该是更为重头的“写作”,因为不仅关系到“升等”,那也是您的学术见解的载体。但另一个方面,您又是华语世界最重要的散文作家,那这样的两种“文笔”之间,您如何总结您现在的看法?
林文月:我想论文也有很多种。比如说你是写文字方面、声韵、训诂方面的或者是比较牵涉到史观的这些的时候,你就得遵守那种非常严谨的范式。但是写文学的论文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东西,所以比较不会像那种别的非常专门的——除了本领域的人以外,其他的人不愿意看、不懂得看也更没办法看的。我这样讲好像有一点贬义,(其实)不是,就是非常专门的、专业的,那是非常重要,不能完全以读者的接受来判断好坏。如果研究的对象本身是文学的,那就当然也应该线路是很理性的。可是难免就会跟着那个对象的波动而自己也有波动。所以并不是太好.如果你在学术的论文上面太滥情,那不是好的选择,如果是我的学生,我会制止的。我就说这个方面可以有,但是最好是在外面,就是论文之外,不要太变成情绪化。
凤凰文化:所以就是从写作方式的角度来看,理性与感性的调节,其实是必须的。
林文月:对。只是写作的方式,有的人会宁愿倾向于合理性的,感性的就比较内敛一点、收敛一点。其实反过来,散文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太学术化。比如说我自己在京都的时候,就写了京都的种种,那我过了很多年以后再看,那个等于是说把我从原来就喜欢文学的人,可是因为进入到学术的圈子里,所以有这种训练跟写作的经验,慢慢就把感性的部分调整、训练到理性一点、更理性一点,变成什么要交代清楚,不能自己随便乱讲一句话。要言必有据。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京都一年》这本书,我自己觉得也是可笑。比如说我在记一个庙或者一个庭园或者什么,好多注解,我就觉得这个是散文吗?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渡,因为我已经受到这样的训练。比如说我去参观一个古代的庙,这个是受到什么时代的什么什么的影响,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影响,宗教的或者是建筑这些等等。我就会忍不住,我要是找到根据,我就会把它注出来。我就觉得我虽然是在写一个创作的东西,出于学术的习惯,我就不舍得把我知道的东西丢弃,我就附一个注在后头,有的时候有十条、十几条。我就讲那个读者你可以不看,可是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写了,也给自己留下一个特别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