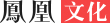洛夫:我们这一代,1949年就成了被遗弃的孤儿
导语:诗是永恒的追寻,追寻“永恒”。
15岁即发表文学初作《秋日的庭园》,战火动荡中背着冯至与艾青的诗集辗转赴台,1954年于高雄左营创办华语世界首席长青同仁诗刊《创世纪》至今六十余年不衰,1959年以超现实主义长诗《石室之死亡》开华文现代主义长诗之先河,1969年发起“诗宗社”,主张“现代诗归宗”,1996年移居加拿大之后,又以三千行长诗《漂木》为汉语诗歌写作创制新的标高,1999年诗集《魔歌》获选为台湾文学经典,2014年于文学电影《无岸之河——洛夫》台湾首映的同时,推出最新新诗创作《唐诗解构》,会通古今诗想,以独特的意象语言整饬国族文明的跨时代对话——曾先后三次获票选为“台湾十大诗人”的洛夫先生,以超过70年的诗文创作,精诚、恪守意象语言“永恒”意蕴的深邃之美,蔚为现代文学之大观,正是在以切身的实践来回应对永恒之美的追慕。
在美学修为上,由早岁的受启于阿波利奈尔、布勒东、艾吕雅等法国诗人的超现实主义和海德格、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理念,到晚近回望传统,细思中国古典诗与哲学的“无理而妙”,洛夫的精神进境可谓健动不息,亦使他的创作屡屡开拓新局。
在语言修炼上,无论是早期写作的繁复浓烈、诡奇多变,还是复归古典脉络后的明快简洁、自然浑成,都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洛夫的语言表现与技巧实验推进了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而其创作历程,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台湾现代诗的成长。”
而更有趣的,则是与其诗作的诡谲魔幻恰成对照的,这位两岸驰名的“诗魔”,在生活中却是一位和蔼亲切的长者,耿直中挥洒幽默,与年轻人的交谈总是鞭策与期许并举,并没有想象中的严肃甚至严苛。凤凰文化的本次访谈是在洛夫先生赴香港参加他本人的纪录电影的首映活动之时进行的,由于“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电影以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一直以来的热度,访问及发布活动安排地很密集,但这位年逾九十的“雪楼主人”(“雪楼”为洛夫为其在温哥华的房子所取的名号)仍旧不显疲态,在沐浴茶香的采访间,谈笑风生地回顾早岁探索,细述诗学心得,借“港岛怀古”的襟怀,发其当下思虑的“隐微与显白”。(特约记者刘道一 于香港)

洛夫 资料图
少年心气
凤凰文化:作为台湾著名的所谓“军中诗人”,您其实参军是非常早的,从您的年表上看,其实抗战的时候您就已经参与了。
洛夫:对,抗日战争是这样的,我1928年出生的嘛,那个时候还小,等于是在最后的阶段,日本快投降了的时候,我参加了游击队,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学,我念初中的时候,参加游击队半年,日本人就投降了,期间并没有打仗,也没有参加什么战争,只能说是有了简单的军人“体验”。
凤凰文化:虽然您说您当时的年纪还小,当其实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文学的创作,并且已经开始在家乡的报刊上发表。
洛夫:我是在抗战结束之后,念高二的时候开始写诗的,初中时候写一点小小的抒情散文,第一篇文章发表应该是在1943年。
凤凰文化:那如果这样比较起来,像痖弦老师虽然只比您小四岁,但您在遇到他的时候,也就是《创世纪》创刊之后,您其实是已经持续创作相当一段时间了。
洛夫:这样说起来,是的,我比他创作早一点,有几年的时间。他是要到参加《创世纪》之后才正式地投入诗歌方面的,以前在河南的时候,并没有写。
凤凰文化:那么,在您小的时候,您的阅读状况是怎么样的呢?会读哪些作家呢?从您的年纪来看,您青少年的时期刚好也是三四十年代文学最繁荣的时候,不知您是怎么看待那个时代的作品的?
洛夫:在那个年代,尤其我们家乡距离当时的大都市上海、北京比较远一点,能够看到的文学书也不多,但是像比较有名的巴金、茅盾的书都会读一些,但是那些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年轻的时候写诗,我读到冰心的小诗以后非常有感觉,就是那些表现爱情的作品。我读她的一首小诗,《相思》,只有12行,很短小,但是我读了以后非常感动,对爱情和相思能够这样处理,那完全是一个诗的意向的表达,对我日后写抒情诗有很大的启发。但是我到了台湾之后的创作,就整个就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完全改变了。
凤凰文化:其实这个也跟您后来的交游有直接的关系。
洛夫:有决定的关系,其实那个时代在台湾,像我跟痖弦、张默在办《创世记》诗刊的时候,我们这一群朋友,像白先勇、余光中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那个氛围是非常不一样的。
凤凰文化:是不是当时杨牧先生也会参与?
洛夫:杨牧那个时候还很小,他还是应该在念初中高中的样子,他比我们小多了,他那个时候就是来找我们玩,所以我们后来也把他算在一起了。那时候倡导现代主义,现代诗很有一种引导作用,当时我们继承的是五四的文学理想,可是那种表现手法太陈旧,而且语言很粗糙,也不够新鲜,也不够精炼,我们就希望能够找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来表现。就这样我们把五四的东西翻来翻去,觉得不行,文本不过硬,后来我们只好再向西方去学习了。其实那种影响也只是一种翻译方面的,我们有一大批诗人是在军中的,有本来就当兵的,从大陆到台湾,也有的本来是学生,到台湾以后再从军的,像我和痖弦原来都是学生,到了台湾以后去当兵的。我们这一辈人的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国学的修养也不是很好,那之后痖弦去念硕士或者我念继续大学都是以后的事情,所以对于西方的东西都是囫囵吞枣,也没有很深刻的体会。后来通过阅读对超现实主义产生兴趣以后,我也做了一些工作,那时候我在军中当翻译官,我也翻译了很多书。主要是一些理论的书,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凤凰文化:这也就是您这一代人对前人创作的思考与重新认识,因为据说您当时带到台湾的书是艾青和冯至的诗集?
洛夫:这个事情准确来讲应该这样说,我当时走得很匆忙,因为我喜欢读诗,那么当时刚好书架上有他们两个的诗集,所以并不是说我特别钟爱这两个人的写作,只是当时就带着就上路去了,从广州到台湾去。冯至的诗在当时也没有特别的研究,只是知道他的十四行诗很著名,有一些好的作品,但是他的作品也不多,非常少。艾青的作品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他是很红的一个诗人,后来在文革之后我还见过他。可是到了我接受西方一些现代主义的诗学的影响之后,我就对于艾青当时的诗歌有个距离了,我们的认识有一个距离了,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诗人,可以是一个很爱国爱民族爱乡土的一个诗人,但是他在表现的手法还是受那个时代的局限,包括阅读以及中文本身的一些问题。后来有一年因为他也好像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了,《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打电话来,要问我艾青对我的影响,应该是20多年前了。他打电话来问我,他问我说你跟艾青熟不熟?我说曾经跟他在新加坡在一起开过会,我早年也很喜欢他的诗,他也是我的偶像,不过后来我通过阅读、通过自己的翻译受了西方现代文学影响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他就继续说有一些资料,据说他已经被提名了,这次得奖也是有可能,是不是请你说几句话。我当时很为难,为一个还没有得奖的人预言他的诗得奖了,这个风险很大。我说不好讲,但是最后我还是讲了,说他对中国的乡土,中国的人民的那种爱是很可敬的,但是他的诗的写作还应该由后辈人继续发展、发扬。结果第二天没有得到奖。
凤凰文化:这其实也就涉及到您与您早年的阅读和写作的氛围构造有关的,您和您的上一代作家、诗人之间的交流,也就是留在大陆的这一批作家。
洛夫:对,我跟老一辈的,艾青、绿原、牛汉、冯至都有过接触,冯至见过一面,卞之琳见过几次,跟他就很熟悉;另外就是再下面就是朦胧诗的这几个人我也很熟,像北岛、顾城、杨炼他们几个我都认识,都很熟;然后再是年轻的第三代我也见过,也跟他们很熟,因为我差不多每年都去中国大陆。写诗的人就是这样,无论什么年纪,很容易成为朋友,大家是一路的。
修正“超现实”
凤凰文化:前面您提到了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的翻译上,花了不少的工夫,在这一点上,也是您相对于《创世纪》的其他同仁,比较不同的地方了,包括您后来在淡江大学也是念英文专业的。那么,可以说,从理论到创作,或者说是诗歌创作跟诗学理论的结合,是您的一个特色。而像痖弦或者是张默他们好像并不是那么注意理论这个层面的。
洛夫:在这个方面,我倒也不是理论先行,让某些理论作为一个引导来指导我怎么写诗,不是这样的。我的所谓的诗学理论,大多是以自序的形式出现,当然我也给别人写序,没有很全面的、系统的理论整理,我也不是很专注地来从事理论工作。不过我写诗的看法也是我写诗的一个方法论,尤其是在写自序的时候,就主要是为了梳理和诠释我自己的创作理念和表现企图,毕竟别人的批评,多是“隔靴搔痒”,有些事情,还是必须自己来做。
凤凰文化:那么在最初的阅读之中,有哪些诗人的作品和诗学的理论给了您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呢?如果由您自己来反思和回顾的话。
洛夫:对于现代主义对我的影响,首推就是法国的诗人的作品,可惜的是我并不通法文,所以说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不是通过中译,就是通过英译。我在念外文系的时候,读过兰波、艾吕雅、阿波利奈尔、瓦雷里的超现实诗,也读过邓恩的形而上诗,叶慈的象征诗,里尔克的冥想诗,现在的诗评家都说我的风格多变,在语言形式方面做了很多的实验,因此要称我为“诗魔”,这就是因为我七十年代曾经受到各种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影响。当然在这其中,重要的还是诗观念上的影响。在七十年代中期,是我全身心投入到超现实主义的探索的时期,那时我大量搜集相关资料,也自己动手翻译了几篇英文的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基本对这种艺术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发展历史都有了整体的了解,那么,渐渐的就投入到里面去了,觉得这种表现的方式,表现的手法很新鲜,从来没有过的,就很喜欢。所以我写《石室之死亡》的时候,是我刚刚开始接近超现实主义,还没有深入了解他是什么,但是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很迷人的一个方式,就拿《石室之死亡》做一个实验品。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是写战争,但是其实大部分写人的一种苦难经验、受难体验,所以里面还有一些宗教的倾向。一种对于人的命运,不知如何是好的迷惘的心态,都在《石室之死亡》里面表现了出来。而因为我考虑的问题,思考没有办法很清晰很理性地来表达,我只好用一种比较晦涩的语言来表达,尤其是对死亡这种主题,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又没有一个人,没有活着的人有死亡的经验,哪怕是宗教对于死亡的认识也是一种推论的方式,不是真正的体验。所以我写这个《石室之死亡》就是用一种非理性的语言来表现这个死亡。而这首长诗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时代精神,那一代人,包括我、瘂弦还有很多诗人以及其他的年轻人,从1949年从祖国离开,割断了祖辈的脐带,也割断了中国文化的脐带,完全变成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在海外完全要靠自己来打拼,那是非常残酷的状况。那时候就觉得人生非常渺茫,非常困惑。所以那个时期写的诗,包括像痖弦的《深渊》也是这样的,都是有这种倾向的。到了后来几十年发展以后,整个社会安定了以后,很自然的我们的诗风也改变了。
凤凰文化:诗坛通常有一个说法,说您是从《魔歌》之后会发展到一个更开阔的创作境遇。
洛夫:对,更开阔、更现实,比原来更生活化了一点,语言也更放松了。
凤凰文化:而具体到超现实主义这个问题,我记得您在前年的“《创世纪》6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时候有讲过,您的这个“超现实”的写法和西方原本的“超现实主义”不是一个概念,不完全是西方的超现实主义。
洛夫:对,我认为我是“修正的超现实主义”,对西方的东西不能不加分辨的拿来就用。在我看来,超现实主义最有问题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自动语言”、“自动书写”这件事情。在“自动语言”这个概念之下,布勒东他们这些超现实主义者追求的只是反理性,破坏一切既存的规律,而要用“自动书写”这种方式来开启潜意识中的“原始”的内容,但是里面没有诗的意象,更谈不上诗的趣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它的贡献也就是诗语言的解放,是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另外的面貌,一些从前没有用诗表现过的“新鲜事物”。我后来发现,当我回过头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像李白、王维他们很多的诗里面有一个东西,也就是叫非理性的东西,跟超现实主义里面的非理性,这两个有某种“妙合”,但是西方的超现实主义非理性就是为非理性而非理性,但是中国的非理性最后是叫“无理而妙”,表面上是无理,但是在心理方面要讲究一种玄妙的表现,那就是一种艺术的完成,一种艺术的表现,达到高妙的境界。这是与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的,西方的超现实主义就停在“无理”这个地方,没有更深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种自动语言,自动的写作不是从事文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凤凰文化:超现实主义所依据的哲学基础和“精神分析”的观念其实是一种“病心理学”,是非正常形态的研究。
洛夫:是。但是最初当我接触西方的超现实主义的时候,也正是被他们那种非正常的,也就是所谓的陌生化的语言意境所迷惑。但越是接近这个东西,最后就变得产生很大的距离,后来觉得这不是一个办法,所以我还是认为诗是一种介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介于现实跟超现实之间,介于感性跟理性之间的东西。这几个矛盾的、吊诡的东西,经过诗人的创作手法、语言意象和谐地编织在一起,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样创作的诗歌,才比较完美。
“永恒”之美
凤凰文化:您说到您现在的对于诗的平衡的这种感悟,如果具体到您最近在做“唐诗解构”的这种尝试,是不是应该可以说是您早年从西方的文学作品和理论吸收到的养分,再重新来回看我们自己文化传统里面的东西,然后再发现出一些新的形式与手法?
洛夫:对。早期因为我们读了胡适的东西,尤其是胡适对于诗歌的理解,对于诗歌新诗的倡导,白话文的倡导,反对旧的东西寻找新的东西,我们也很赞同,也很乐意,但是后来自己写了那么长时间以后觉得不对劲,因为他那个东西固然是也不错的,白话文的诗,写得大家都懂,但是懂了以后不是诗了,不是很好的艺术,我说这个不行,所以也从西方找一些新的东西,象征的手法、意象的表达,对一个诗人还是很重要的。后来学习西方的手法一段时间,差不多二三十年,都在追求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可是后来感觉到,一直走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好像那个路前面非常有限,再走也走不下去了,而且给感到一个中国诗人他的生存、成长、长大也必须还要在自己的土壤上面,在自己的文化中去壮大、去长大才能长成一棵大树。老是在西方流浪,你开始向西方求学求经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但是那个过程要适可而止,最后还是要回来。我不是讲回归传统,因为回归传统就是写旧体诗了,写传统诗去了,动不动就是“小桥流水人家”那一套,那就没有意思了。
凤凰文化:所以您的对中国古典的追求是指向另一种方向的?
洛夫:在文学里面、诗歌里面有一种可变的东西,也有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不变的因素,不变的那种美,诗歌里面像李白、杜甫他们诗歌的意境、神韵是一种不变之美,后人一定要珍惜它,爱护它,甚至传承下去,这些东西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很重要的。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了“解构”唐诗的一个方法,因为文学的传承也要不断地发展下去,尤其像诗歌的永恒性,美的永恒性。我们现在读李白诗的时候还是感觉非常新鲜,因为它有一种创造性的东西在里面,创造性就是成功了,有一种永恒之美。所以一个诗人的创作,不应该去追求时尚、热闹,诗人追求的是艺术的永恒性。
凤凰文化:对您来说,诗就是对“永恒”的追寻,这是驱动您跨越古今,进行创作的根本识见。
洛夫:古典作品的那种“永恒之美”,实在值得我们珍惜它、珍爱它,尤其是那种神韵,可是胡适他们就是要反对这个,他曾经说了两句话,他写旧诗里面两句话,“诗国革命何时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样同时也就把几千年来累积的美学的、意象的东西完全否定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后代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像中国现代流行的一些口水诗,好像乱来一样,在这方面网络也是一个帮凶,使得今天的诗歌发展到现在的境地,之所以被一般人冷落,边缘化,把诗写成那样很散乱,语言没有一点张力,没有意象之美,就像普通人说话一样的,那还写诗来干什么?诗还是要有一些条件应该具备的。所以我就用这个解构的方式把它原来的那种范式打破,我再重新用新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用一种新的意象的表达来充实、重新创造诗的境界,同时又尽量保留原作的意境在里面。
凤凰文化:比如我们看到具体的篇目,比如像《锦瑟》,那里面您一开篇就用到“痴”这个字的统领意义与意象的指涉,所以在“重构”之中,您其实有自己的一个解读,甚至自己新的代入视角。
洛夫:不是机械的重复,也不是翻译,是我认为他在诗里面有那个意思,意在言外,藏在语词的下面、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出来,我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提点出来。
凤凰文化: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您现在的这个年纪,还能做这么大规模的“重构”经典的工作,是不是也是因为您到了温哥华之后,您的创作环境更安静的缘故?
洛夫:对。所以之前还有一个记者问我,说您感觉寂寞吗?我说寂寞看怎么样解释了?在生活方面我一点都不寂寞,很多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如果谈到内心里面去的,那种“心灵的对话”找不到人,其实就不能强求,不如到经典里面去打转,跟古人来对话,更加合适。
凤凰文化:您之前在发布会的会场上是有对年轻的爱诗人有一个寄语,不知您此刻有怎样的话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讲?
洛夫:现在看,我写《唐诗解构》还有另外一层的目的,就是让年轻人看到“唐诗解构”这种书,因为它前面有原作、有解构之后的作品,如果他能对这个诗集解构的形式和方式抱持好奇,连带着也就是对原作有一种喜欢,间接地影响他去接近唐诗、去爱唐诗,这是我一个比较现实的目的。最近在温哥华、在台北都有一部分人说要发起运动,“唐诗复兴运动”之类的,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所以说我对年轻人还是希望他不要太忽视了、不要太轻视了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一些精髓的东西,这些都是不能因为那些政治的所谓乱象而被削弱的,如果失掉了,就非常可惜。你可以不写旧体诗,不依赖他的形式,但是它的内在的那种美感,那种永恒的意象之美,你还是应该尽量地喜爱它、接受它、继承它、发扬它。
版权声明:《年代访》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