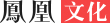刘剑梅眼中的刘再复、李泽厚、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
导语:刘再复、李泽厚、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这些如雷贯耳、名扬中西的学人在刘剑梅那里都成了父亲、伯伯、叔叔、老师。她不仅有幸得到这些学者的指点教授,更与他们有着深厚的交往情谊。在她眼中,这些大学者固然有着大学问,却也有着“小”的生活趣事,生活与治学共同构成了他们为人的完整面相。本期年代访,我们一起听刘剑梅聊聊那些海外的中国学人。(采访人:徐鹏远)
夏志清、李欧梵以及王德威

刘剑梅与王德威
凤凰文化:王德威先生一直被认为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这三位,您都认识,也都有深入交往。能不能谈谈他们在学术上的异同?
刘剑梅:王德威老师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班的导师,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我博士论文的确定,到具体的写作过程,再到最后的修改和论文答辩,他都耐心地辅导。我非常幸运成为他的学生,而且是他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批录取的博士生,算是他的“老学生”了。夏志清先生在我进入哥大时,刚刚退休,可是还回来教了一门课,所以我有幸选了他的“元杂剧”,跟着他踏踏实实地学了一个学期,而平时读书时,他和师母对我都像亲人一样照顾,总带我出去吃饭聊天。李欧梵先生是父亲的挚友,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把父亲请到了芝加哥大学,我因此在那里跟他修了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在我的学术道路上,他给我的帮助也特别多。
谈到他们的学术异同,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把他们三个列为同一个派别,其实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有意识地去形成一个“派别”,只是在学术上互相欣赏而已。当然,他们是有某些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台湾的背景,然后都在美国求学,毕业后在美国常青藤大学教书立著,采取的学术立场都是以“世界主义者”的身份来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可是他们在汉学家崛起时的历史背景都不同,学术侧重点也不一样。
夏志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受到李维斯(F. R. Leavis) 的理论和新批评学派的影响,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认为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挖掘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的高度评价,都是站在文学审美的立场,考察作品的实际表现。很多人批评他的冷战思维,事实上他最反对把文学研究当作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反对把文学看成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政治的反映。我认为夏先生是从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即普世视野)来评价中国文学的,这种视野超越国界(包括批评中国作家把“感时忧国”的民族情结固化),把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来思考判断,重视的是文学本性与文学自性。如果忽略这一点,仅从“文化政治” 、“话语霸权”的角度来批评夏先生,就会产生误解。倘若给他扣上“反共学者”的标签,那就更加“本质化”即更加简单化了。

刘剑梅与陈平原、李欧梵
李欧梵先生的文人气息很重,在学术研究上他很重视思想的灵性和流动性,属于以塞亚·伯林所讲的“狐狸型学者”,涉及的领域特别多,比如文学、历史、文化批评、城市比较、影视评论、音乐评论、大学教育等,因为有了这一知识分子“游离”的“业余者”的身份,他很像本雅明所写的大都市中的“爱闲逛的人”,深入中西方的文化肌理,用诗意的眼光欣赏文学、音乐、绘画、电影和都市文化。他早期对五四时期浪漫的一代文人的研究和后来对鲁迅的研究,受到Benjamin Schwartz和夏济安的影响比较多,把现代文人的文学作品和他们在大时代中的浪漫情怀和个体精神分析得特别好。他后期写的Shanghai Modern《上海摩登》,真是可以当作一本小说来读,结合了历史视野、文学文本细读和文化批评的方法,属于真正的“跨学科”研究。
王德威老师的学术研究覆盖面非常广,从晚清小说到中国现当代小说,再到世界华语文学,甚至到当下的科幻小说,他都有精彩的研究。他总是喜欢采用历史和理论结合、文学和历史结合的方法。早期他对茅盾、沈从文、老舍的研究,还有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一直在突破“五四”传统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定义,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多义性和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后来他在《历史与怪兽》中不仅重视文学文本,而且重视历史文本,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政治态度、不同价值视角的个体的心路文本。解构之后,我们能够建构一些什么?他去年刚刚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就试图重新建构一个现代多元的抒情传统,开辟了一个不仅区别于革命和启蒙话语的传统,也区别于载道与言志的传统的另一种思路,充分展示了文学人的一个情向度。最近他致力于对华语语系文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美学及其文论的研究,试图找到一个更适合研究和评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语言和体系。
凤凰文化:李先生和王先生很不一样,从外表上就看得出来。
刘剑梅:对,王老师非常温文儒雅,几乎任何时候都是衬衫领带,上课开会时永远都是穿着正式的西服,他属于纯粹的专注的学者,每天一回家就看书,看得相当广博,连《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都早就阅读过了。我知道他喜欢京剧,也会画国画,我们每个博士生毕业时都会得到一幅他亲笔画的国画。我和同学们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过的是一种非常单纯的学者生活,除了读书、教学,就是写作、做研究。相比之下,欧梵叔叔的兴趣爱好就太多太广了,他现在香港偶尔去做乐团指挥,成了资深的音乐评论家,还偶尔跑去拍电影,当然只是在电影里客串几个不重要的角色,在做学术研究之余,乐于做“业余者”和“边缘人”,把自己定位为“中国的世界主义者”。欧梵叔叔特别幽默,平时跟他聊天,我不仅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觉得非常开心。他跟他的太太李子玉极其恩爱,在太太受忧郁症折磨的时候,他始终耐心地守护在身边,帮助她走出了困境。
李泽厚的意义在于点破我们
凤凰文化:还有一个人想让您评价一下,李泽厚。他和刘再复先生的关系非常好,可能您是少数几个最合适谈他的人之一了。李泽厚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简直就是所有读书人的偶像和导师,我也受过他很深的影响,但随着中国学界能够接触到的理论和思维越来越多,李先生的很多东西也开始被质疑和被提出不同意见,当然最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了,只不过那个人现在不能提。尽管他是您的长辈,我想在个人方面尽可以尊重,学术上还是希望听到更为理性的您的看法。
刘剑梅:对李泽厚伯伯的体系,要真明白,需要时间,可能得三丶五十年,这之前有质疑,在所难免。李伯伯是个极为理性的无神论者,他完全相信人的理性的东西。相比之下,我父亲既讲人的主体性,也尊重神的主体性,常徘徊於理性与神性之间,這与李伯伯就有区别。李伯伯拒绝上帝,仅此一点,就让许多人受不了。他打通人文各领域,哲学上原创出许多大命题,历史学上独辟出许多大见识,美学上建构了一套新学说,不那么容易了解,我也只是在学习,在逐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我父亲对李伯伯理解较深,但他也一再说,只能感悟其部分内涵。
比如说启蒙与救亡的问题,大家一有了西方理论的视野就马上去否定它,刘禾很早就在她的书里提出了质疑。不过我觉得李伯伯讲的是一个常识,中国在五四时期最开始就是一个启蒙的主基调,后来到了抗日时期就是一个救亡的主基调,在国家危机的时刻确实很少知识分子在讲启蒙精神了。当然启蒙与救亡二者有交织之处,我们无法特别鲜明地把二者分割开,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确实代表不同的时代精神。我们现在总要解构时代精神,认为历史是破碎的和片段的,但是李伯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宏观概述其实是很到位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喜欢解构的立场,就一味地否定宏观的描述。
再比如有人批评李伯伯的吃饭哲学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他早就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的吃饭哲其实很重视中国的语境,也很符合中国的语境。他和我爸的研究都特别重视语境的问题,他们总说我们把很多东西从西方搬过来,可是没有搞清语境的差异性。李伯伯在他建构的哲学体系里很重视历史的维度,比如他讲的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矛盾就非常有意思。李伯伯的书是长期的畅销书,他打通了中西哲学的脉络,而且用非常深入浅出的语言,让更多的读者可以明白他的思想。其实他的观点和思想,点破了很多我们没有悟到的东西,这种点破最重要,思想家的贡献就是点醒我们,给我们启迪。
因为我父亲跟李泽厚先生在美国Boulder波德市的生活里是邻居,每天他们几乎都在一起散步,我也因此而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有机会向他请教,写《庄子的现代命运》时,就得到李泽厚先生和我父亲的指点。李泽厚先生的学术包括哲学、伦理学、美学、思想史研究等多方面,既广且深。他的一些独特的学术命题比如“历史本体论” 、“情本体” 、“度范畴” 、“儒道互补” 、“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 、“乐感文化” 、“儒法互用” 、“巫史传统”等,对我都很有启发。
我父亲写过一本《李泽厚美学概论》的专著,还做过《李泽厚哲学体系的门外描述》的讲演,让我对李泽厚先生的思想体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经常会贵远贱近,只崇拜西方的哲学家,看不起中国自己的哲学家,其实李泽厚先生的哲学水平已占领当代世界哲学的制高点,也已打通中西哲学的脉络,其成就绝不可低估。几年前,王德威老师在研究中国的抒情传统时,就非常赞赏和认同李泽厚先生的“情本体”的理论,还跟我说很想去Boulder拜访他,可惜后来太忙,没去成。
我对父亲刘再复既有继承也有挑战

刘剑梅与父亲刘再复
凤凰文化:在您的文字和言谈中总能提到父亲,许多著作也写着献给父亲。再复先生当然是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者,但有这样一个高度的父亲在,您会不会有一种总处在“阴影”里的感觉?
刘剑梅: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在北大的时候特别想摆脱我爸爸,那个时候特别不喜欢别人说刘再复是我爸爸,觉得自己总是罩在父亲的光环下,而我的个体价值没有被重视。因为八十年代我属于“文二代”,当时正是文化热,属于文人的天下,有这样一位出名的父亲,我在在北大总被同学另眼相看。
后来一家人到了美国以后,我父亲就从“社会中人”回归了家庭,回到了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父亲不再属于社会了,而真正是我和妹妹的爸爸了,有更多的时间教育我们,陪伴我们。在美国,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所以亲情弥足珍贵,从那个时候,我跟父亲的对话就一直保持着,其实也是我们互相的一种精神力量。
所谓影响焦虑,就是如果我完全受父亲影响而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就会感到很焦虑,可后来我发现我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有属于我自己的语言。比如我受到的西方学院派训练,跟父亲那代知识分子的宏观思维很不同,另外我有女性的视角,跟父亲的男性视角也很不同,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我当然继承了很多父亲的思想,但是也有对他的挑战。我们现在的人总是急于反抗父辈,急于解构,但是我觉得首先应该继承,然后才能谈超越,不应该为了反抗而反抗。
我父亲把文学当作信仰,当作心灵,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都很熟悉,他的理论批评有自己的体系,审美感觉力和判断力很让我钦佩,这自然也构成对我的压力。我常常既有老被一个人推着往前走的感觉,又同样感到庆幸能有一个同行的父亲,他不断地给我思想和精神的源泉。
我和他也有过冲突,但是我爸爸特别注意培养我的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他总说“学问”就是不仅要“学”,也要会“问”,会质疑,不能人云亦云。作为父亲,他是很民主的,他不喜欢总是摆出传统父亲威严的姿态,而是喜欢把我当做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处于一种讨论问题和辩论的状态中。这在中国文化里是比较少见的一种父女关系,对培养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