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2012年5月31日在北京去世,95岁

《我与胡适先生》(2005) 漓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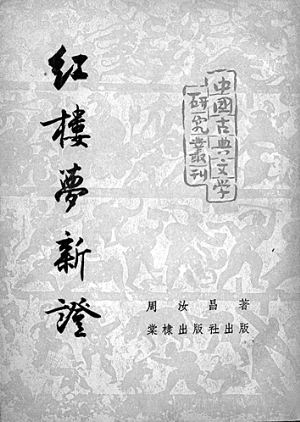
《红楼梦新证》(1953年) 棠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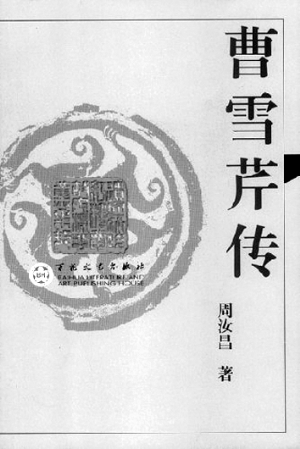
《曹雪芹传》(1980) 百花文艺出版社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2009) 漓江出版社
(上接B2版)
(自传说)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上的依据。
至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
从此,周汝昌开始了把“红学”进行“宏大叙事化”的历程。《什么是红学》一文直接回应学者余英时的红学史观点。余英时说“考证红学面临危机”,周汝昌则说考证红学正是红学的生机所在,甚至考证红学才是红学。
从1986年至1987年,周汝昌应邀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讲学,这期间他开始建立《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自序中,周汝昌说,这部书要探讨的是“三大基点”:“《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具体说来,“性质何属”指的是:“芹书到底是写谁(写人?还是写己?)的问题”。也就是说,周汝昌的第一个基点是要解决《红楼梦》的本事问题,即这个本事究竟是曹雪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也即是“新红学”与旧索隐(还不关新索隐的事)之间的老纠纷,是“自传说”与“他传说”的纷争问题。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与自己和红学的渊源和贡献。胡适与周汝昌的关系渊源和恩怨,也是红学研究史上的一段公案。周汝昌曾说,“我与胡先生的交往,主题起因是‘红学’讨论。”
1947年12月5日,周汝昌在《天津日报》的图书副刊上发表了关于红学研究的一篇文章,也就是简介《懋斋诗钞》。此时离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26年之久,他看到后,于12月7日写信给了周汝昌,请文献学家赵万里转交。胡适在信中肯定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贡献”,同意其对“《东皋集》的编年次序”的推定及“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但同时又表示,“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并说明了两点理由,这封信于1948年2月20日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
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感到“欣幸无已”,并激发了其继续深入研究《红楼梦》的兴趣。他于1948年3月18日给胡适回信,就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在这封书信中,周汝昌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依敦诚的‘四十年华’推雪芹生于1724,有根据,配入年谱,合多,抵牾得少”。这封书信发表在当年5月21日的《民国日报》上。从此,两人书信不断往来,切磋探讨《红楼梦》的相关问题,直到1948年10月为止。
也正是由于这段交往,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但周汝昌对此一直是否认的。1949年之后,两人长期未能通信联系,直到多年后才收到友人寄来的胡适批注《红楼梦新证》的手迹,才知道胡适在台湾时也还关注着周汝昌。周汝昌后来说,“直到他看了我那本《红楼梦新证》,里面又有几处不够恭敬的词句(我的手稿中不是这样的),再到批俞批胡运动时,他又读到了我的署名‘批胡’的文字(尽管此文也曾经过别人的‘加工’),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芥蒂于怀。从这些方面来看,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
对于自己的红学研究之路,周汝昌也曾有简单回顾,他说:“我自己的‘研红’的历程,大致是由史学考证入手,然后集中花费大力气,在纷纭错乱的不同文本中校定出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曹雪芹的原文手笔文本,不如此则无法对《红楼梦》进行真正的研究。在此奠基工作之后,我才决定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的崭新命题,此时已经到了1980年代的中期了。我提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小说的命题之后,再进一步,我才逐步把自己的目标明确起来,即:我的愿望是把读《红楼梦》的那种无以形容的美加以研究体会、解说;若无这一步骤,那么我几十年来的‘研红’工作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可言了。”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1921年)一文中确立了“新红学”的两大支柱:实证与实录。实证与作者、版本等研究相关,实录则成为实证研究的基本信念。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二文中确定了“新红学”的基本对象:作者研究和版本研究。与版本研究相关的则有佚稿研究和脂砚斋研究。然而,胡适却在实证的基础上引出了“自叙传”说,这个“自叙传”说是传统史学实录意义上的,其目的是为“以贾证曹”确立依据,反过来成为实证的原则。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然后把文献研究所得升华为人文价值阐释。在文献研究方面,他广泛搜罗材料、辨析材料、考镜源流,其《红楼梦新证》所搜集的资料之丰富在红学史上堪称一流,所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孙逊说,“这是新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是每个《红楼梦》研究学者不能绕开的著作。”
其实从1954年起,周汝昌就开始耳朵失聪,1974年,他的视力急剧下降,所以他从1980年代后期起,就对红学研究现状和进展已经不甚了解。但正是这种不了解,有人把他比喻成红学界的独行侠,他与红学主流为敌,为此他甚至续作曹诗冒充真品让一些所谓红学专家出丑。1980年代以后,周汝昌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丰润说、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争议。晚年的周汝昌还登上了百家讲坛再说《红楼梦》,这是一次对学术界红学研究的普及,广受欢迎。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频道推荐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
-
64620
1林志玲求墨宝 陈凯歌挥毫写“一枝红杏 -
42654
2曝柴静关系已调离央视新闻中心 旧同事 -
37237
3人体艺术:从被禁止到被围观 -
28599
4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曾以“神侃”天 -
21714
5李泽厚5月将在华东师范开设“桑德尔式 -
19652
6作家李翊云推新作 曾称莫言某作品“像 -
15979
7独特而温暖的画作 -
8591
8刘益谦举证功甫帖为真 称上博专家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