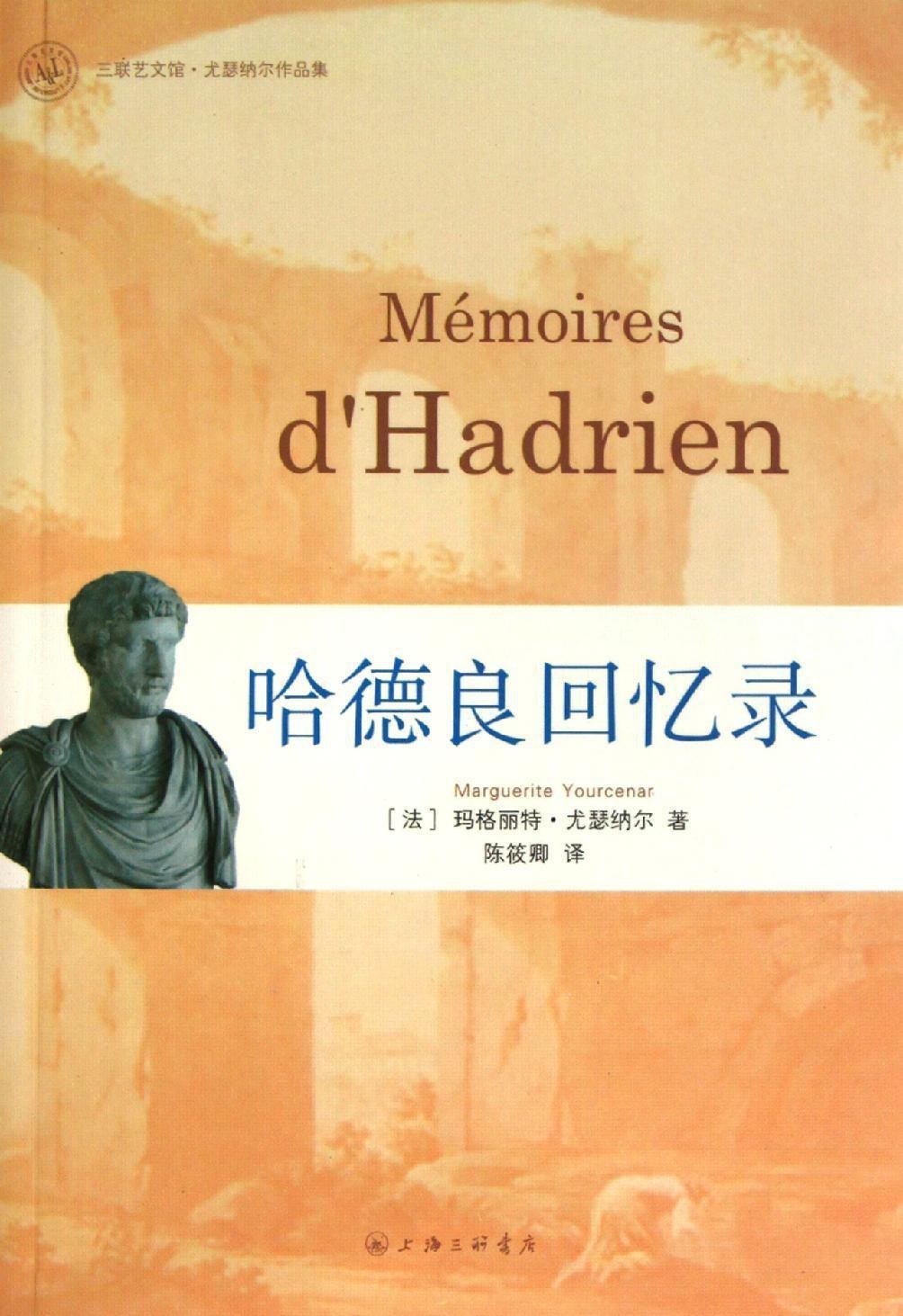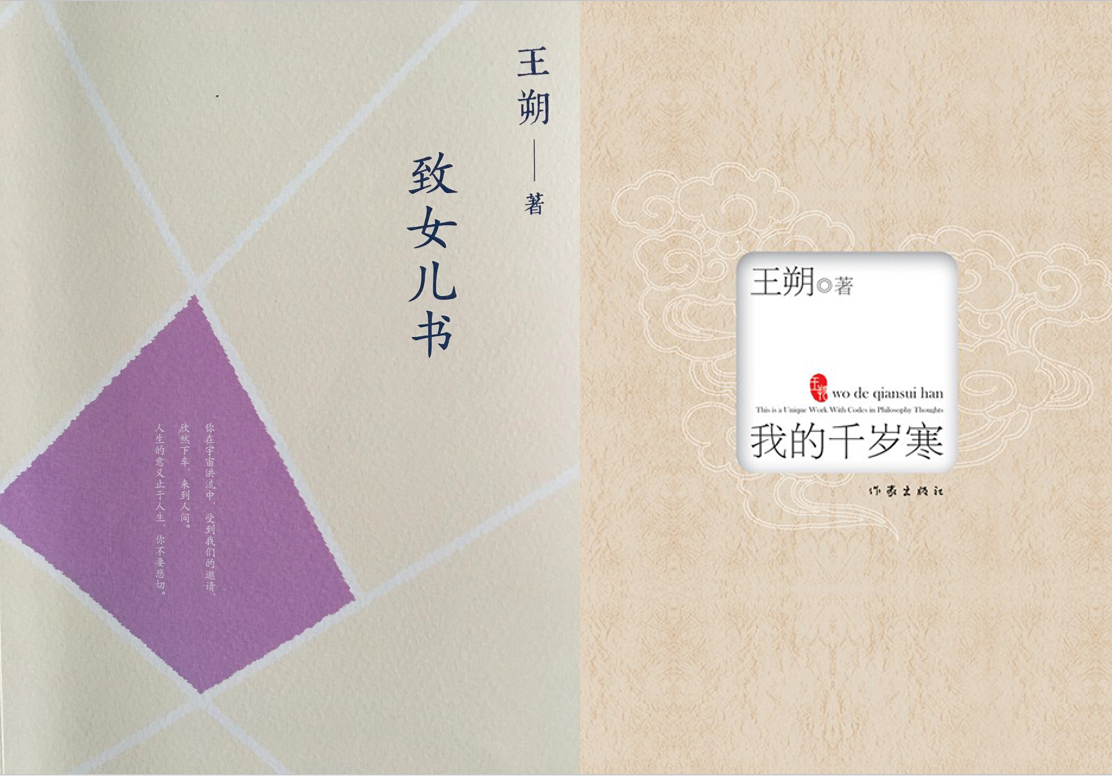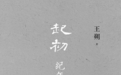
王朔新书,一场人至暮年的冲锋
核心提示:
1.时隔14年,王朔再出54万字长篇小说,《起初:纪年》。小说以汉武帝和司马迁为主要人物,书写汉武帝一朝的大事小事,串联起汉朝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
2.虽写汉朝故事,但依然最大限度延续了王朔的语言风格和精神气质。
3.王朔是大院子弟出身,成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名于商业与消费时代。他的作品源自前者,服务后者。他把崇高打倒在地,却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价值坐标。
4.比起许多已经罢笔的同代人,王朔的冲锋已经足够壮丽。
作者 | 宗城
时隔14年,王朔再度出新书,这个事情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文化现象。
王朔如今已不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他是中国内地最流行的一位作家。他的《动物凶猛》被姜文改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由他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开启了中国情景喜剧的春天;冯小刚从他那儿拿过来不少点子;他和徐静蕾的故事曾被全北京的媒体嚼烂舌根;他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永失我爱》等,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老舍之后,王朔可能是最能代表京味文学的作家,尽管他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上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但很少会有人否认他对一代读者和写作者趣味的深深影响。
《起初·纪年》,为王朔四卷本140万字长篇小说《起初》最后一卷,近日率先出版
一、《起初:纪年》:依然“王朔味”的小说
《起初》四卷本是王朔这辈子写得最长的书,也可能是封笔之作。王朔在《起初:纪年》的自序里说:“这本书开笔于本世纪初叶,原计划三年完成,后来一猛子扎出去,再抬头就是十啦年之后,街上流行戴口罩。”
这部140万字的小说分为《鱼甜》《竹书》《绝地天通》《纪年》。四卷本小说,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到汉武帝颁布罪己诏为止,意在“起大妄,上探我国文明源头”。
之所以最先出《纪年》,是因为王朔和和编辑讨论后觉得,《纪年》“文字最顺,阅读体验最好,而前数卷趣味、用典、用辞则多有可商榷”。
那么,这本《起初:纪年》到底写得怎么样?王朔为什么时隔十四年那么长,写起了汉武帝时候的故事?他为什么会觉得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这本书就是王朔眼中的《史记》,是他的童年、他的青春、他人生世界观和的价值观最重要的落脚之处。
这本书为什么不停地写汉朝的战略部署、汉朝和匈奴的对峙,写汉武帝和群臣的韬光养晦到出击漠北,及至李广悲剧、司马迁的隐痛、汉武帝晚年对人生的回望,以及整个汉家朝廷从战争时期到休养生息的转型?这些事件投射在王朔心里,实则地唤起了他的成长记忆。此中的历史与现实互文,或许才是王朔的抱负所在,他想写出一部属于自己的《史记》,他要从上古写到汉朝,为一代人的光荣与暗影留下一份隐秘的见证。为此,这一次他投入了自己最大的进取心。
这本书表面上看,其实是按照通鉴纪年——汉武帝年少时,到后元二年汉武帝驾崩——把汉武帝一朝的大事小事走了一遍,串联起汉朝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期间阿老、田蚡、窦婴、东方朔、司马迁、李广、卫青、霍去病、李陵、桑弘羊、戾太子、刘弗陵等重要人物都有登场。其中,贯穿全书的两个人物是汉武帝和司马迁——一个是皇权的代表,一个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这体现了王朔的整体立意:他就是要写一部涵盖君主、文人、武将、外族、宦官、外戚、宫闱、诸侯王和江湖人士的书,要把自己对于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化的理解融汇在这本书里。换言之,王朔要在这本书里自问自答的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如何形塑自身特殊性的问题。
理清楚这层,不妨就来看看王朔这一次的完成度怎样,进而归纳几个这本书明显的优缺点。
首先需要说明,如果是想看历史非虚构或者微观史学著作的读者,最好还是放低对王朔这本小说的期待,不然开篇洋溢的北京话就会让你纳闷,这到底是西汉故事,还是北京胡同老大爷跟你唠嗑?王朔这部小说最具特色也最可能引发争议的就是他的语言,他在用自己改造后的北京白话潜入历史,在历史故事的基础上彻底过一把文体游戏、语言风暴的瘾。
这部小说把王朔的“碎嘴”发挥到了极致,试举几例:“我汉乡下不识字的人也是这么数日子,今天出门倒霉,今天出门不倒霉,把倒霉事儿挨着过一遍就一年了。”又比如这句有点俏皮感的:“阿老,求心疼,用咱听着不闹心正经汉语。”
与此同时,王朔在文中,还混合其他方言、结合文言文,创造了许多新的语言实验、比如七十七章最后两句:“上终日独坐,绕膝、坐膝皆猫咪,抚猫若抚幼子。嗫嚅自语人皆不解其意,惟猫知。”明显是“文言腔”的表述。又比如说全书最后一段节选:“其实全无动于衷,再追忆难过亦干涸。由是可知情感为世间物,一世情一世了,人格秒删,对象亦空置,恋怨无所寄。”
至于王朔这么用语言是不是好,是否适合用以重述汉朝故事,这需要由时间检验。但从创造的角度来说,其实《史记》《汉书》乃至后世史学著作已经就这段历史说过很多了。王朔没有“中规中矩”,而是用一种借古喻今、故事新编的手法,带领读者进入一场怪异的体验,这或许还算不上杰作,但至少有新意。
可以说,语言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它仍是具有“王朔味”的一本小说。
第二个明显的长处在于此书的收尾。这本书后面比前面写得好。前半部中,王朔像是一股脑泥沙俱下地来了一盘历史故事大乱炖,对于历史素材的使用上难言精妙,未见作者的精心剪裁,部分章节读罢仍有堆砌之感——出场人物多、事件多、叙事者又嘴碎,特别喜欢拉家常、讲战略部署。刻薄一点说,就是五个不停:“不停打仗、不停战略部署。不停男人唠嗑、不停人事流转、不停发生外忧内患”。这导致行文拖沓、滞重,若非作者是王朔,有多少读者真的能耐心读下去,其实是一个问题。
然而到了后半部分,当王朔写到李广、李陵父子遭遇、巫蛊大案,写到汉武帝写《轮台诏》时,却更加沉郁、凝练,也更具有一种“人间沧桑”之感,让小说的质感更浑厚了一层。这也许和王朔人到暮年的生命经验有关——世事终究浮沉寂灭,汉武帝一代雄主,晚年终究也逃不过昏聩、忏悔与孤独的命运。
二、帝王故事里没能回避的缺点
与此同时,王朔此书还有一个缺陷无法回避。
王朔以汉武帝为主角本身并无问题,但如果过于沉溺于君主的心理世界,对于帝国的武功爱慕有余而警醒不足,将民间疾苦视作一种帝国风景的边角料的话,一本小说的穿透力就会打折扣。
比如《哈德良回忆录》也写君主,作者尤瑟纳尔写的就是罗马“五贤君”之一,但她不是平铺直叙地展现皇帝的一生,而是把叙事的“现在时”设定在皇帝罹患心脏病的晚年,通过诗意而怅惘的回忆建造起一座历史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重点已不是皇帝功绩,而是对于人类命运的追思,对于个体意志、欲望、身份与所处环境冲突的描绘,乃至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卑劣一面毫不掩饰的暴露。这些使得尤瑟纳尔这本《哈德良回忆录》区别于歌功颂德的流水账。
《哈德良回忆录》,作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讲述罗马“五贤君”之一哈德良一生的故事,实际亦体现20世纪中期法国文学界对2世纪罗马的态度
相较而言,《起初:纪年》多战争筹划、宫廷政斗、江湖逸闻,却对武帝时期连年征战导致的劳民伤财着墨较少。
汉武帝在位54年,有四十多年都在和匈奴等国打仗,期间远征人数动辄数万,十数万,这还只是前线士兵数量,再考虑到后方转运、补给部门,汉武帝时期投入一次大规模战争的人数,超过百万不在话下。
连年征战,国中疲惫,到了武帝末年,全国人口较汉初直接减半,民间暴动也频频发生。若非汉宣帝励精图治,汉家后人在休养生息和开疆拓土之间找寻平衡,汉武帝恐怕既要成为开疆拓土之雄主,也要成为点燃民众怒火的众矢之的。
不过说到底,我不觉得王朔在歌颂汉武帝、重复陈词滥调,但他的历史意识本可以更深入,本可以在历史剪裁、叙事手法、人物内心世界勘探的层面上,对自己更狠一些。这是一个完成度的问题,我并不怀疑王朔的野心和努力,但他更深的立意在漫长琐碎的叙事中深陷于迷雾,他在用北京白话解构传统历史书写的同时,并没有让我看到一个更有创造力的东西。王朔在做的东西,和多年前“新历史主义”在做的、王小波在做的(例如他写《红拂夜奔》),其实殊途同归。但王小波至少在批评乌托邦幻觉、苦难叙事、民粹主义后张扬理性和自由的可贵,提倡一种审慎的、基于理智与共情的人生的态度。王朔解构后捍卫的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王朔:一个夹在反抗和迎合中的人物
很多读者阅读《起初》,冲的是王朔的名头,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太理解,王朔对上一代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九十年代标志性的文学人物?
王朔
王朔本名王岩,满族人,出生南京,祖籍辽宁鞍山,大院子弟,在他出生那一天(1958年8月23号),金门响起炮火声,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正在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发动猛烈炮击,国民党军亦做出反击。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出生在八二三炮战这天。按迷信的说法,不知有多少冤魂托身,小时候不觉得,四十以后发现脸上带着一股戾气。”
王朔说话直接,有孩子气,他擅长写小时候经历过的事、写通过孩子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以文字中颇有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荒诞意味。
他盛年时嬉笑怒骂,甚至化用别名批评自己,但骨子有一股柔情,对于至情至真之人,他有恻隐之心。王朔是个正经人,但他要用不正经来包裹他的正经。有一类人本来不正经,要装作正经的样子,这类人很多,王朔要面对的就是这类人,他要用自己的笔,来戳破那些道貌岸然和装腔作势,所以他一度把自己活得“特别能战斗”,成了文坛“坏小孩”的代表。
王朔并非孤军奋战。他在文学界中不乏拥趸。风头正劲时,王朔在《钟山》《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刊物都发过小说,如果他真是一个人和主流文学圈对着干,就不会有“王朔现象”的出现。
某种意义上,王朔才是九十年代的主流,他代表一种无法压制的声音,那就是把假模假样的东西从台上拉下,将事物还原成本来的模样。谁也别装孙子,站着的就是个人。
许多批评家说他俗,市场却欢迎他。在上世纪末,王朔是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写作明星和编剧,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初的几部现象级影视作品,比如《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非诚勿扰》等,都跟王朔有关。
如果要为中国1990年代选一位代表性作家,综合文学功底、影响力、象征意义,王朔也是不可忽略的人选,因为,他真切地影响了一代人,掀起过一场反思语言和价值体系的风潮。
此前友人问我,王朔和王小波是同时代人,两个人都具有反抗气质,但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解题之处在于出身和成长环境。
王朔是大院子弟出身,所谓“红旗下的蛋”,从小对卫国守边的军人生活耳濡目染。之后,他经历文革和改革开放。可以说人生的前三十年,王朔经历了两次天翻地覆,“根正苗红”所带来的优越感在时代中慢慢磨成了五味杂陈。说他是“痞子文学”、拥护商业,或者说他与主流保持一种暧昧、说他其实是“假反抗”,都有道理,但不够详尽。
王朔的一只脚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另一只脚又踏在改革开放的土地上,享受着市场经济的红利。他在生存经验上受惠于“公家”,他的成功经验中,又有对“反抗权威”、“亲近民间”的九十年代话语的巧妙利用。他把崇高打倒在地,自己却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价值坐标。于是,读他的文字很过瘾,但过瘾完了又茫茫黑夜空落落。读他的作品,会感到失去了什么,但又没有重建什么,那是一种未完成的中间状态。
王朔是一个九十年代的宠儿,那时候他的“叛逆姿态”很新。但迈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成为定局以后,王朔依然有名,只是已不再是弄潮儿和先锋者。王朔2007、2008年出版的作品《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口碑明显没有之前好了。
王朔作品《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
当一个个“小王朔”抢班夺权的时候,王朔依然有执着。他需要一个交代,一个给自己文字生命的交代。无论是《看上去很美》《致女儿书》还是《新狂人日记》,都担不起这份重量,但一百四十万字的《起初》可以。这就是王朔的执念。
四、王朔真正的价值和局限
九十年代王朔的真正贡献在于:第一、他对北京白话的创造性使用。使得北京白话在老舍之外,有了另一种进入文学的方式,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和创造性的;第二,他激励人们重新思考艺术内部的分界。通俗文学一定就低人一等吗?影视剧是否能成为艺术?又是谁人为制造了雅俗之分?王朔持续在用小说和影视剧创作推动这个议题,他的小说不被一些纯文学爱好者认同,但他又是能代表九十年代精神气质的一位作家,而他在中国影视剧发展中的作用、分量更不必说。未来,王朔在影视剧史上的地位,或许更高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至于说王朔作品中“反抗权威”、“亲近民间”的精神、姿态,其实他的身份和所得决定了,他很难构成真正的反抗。过了“动物凶猛”的阶段,人会变得柔软,不只是追忆“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知道那“看上去很美”的东西,终究有冷暖自知的成分。
王朔不是变保守,他只是知道九十年代的姿态已经不合时宜。王朔是一个擅于解构却无法建构的人。他曾经与一切看不顺眼的东西为战,但他拥抱的那些——娱乐、商业、消费主义、民粹倾向,现在都已经成了潮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故作姿态只能是一种撒娇。
当王朔离开时代浪潮,从以他本人命名的时代符号中抽身而出,他更像是一个退隐者和本分的写作者。骨子里,王朔知道自己的软弱,在《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中,他甚至毫不掩饰这种软弱。那脆弱让人伤感,让人喜欢,却也让我们更意识到他的局限。
在新作《起初:纪年》中,王朔看起来变了,但你发现那个内核其实并没有变,他只是换了个时空。小说里不断出现的北京白话、拉家常的氛围、对于英雄悲剧的追缅、对于死亡的思索等,其实仍是王朔的舒适区,也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
所以,喜欢王朔的读者会很喜欢这部作品,不喜欢的就会觉得又臭又长。因为在书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活在90年代的忧伤影子。他越是热情地跟我们讲述,我们就越叹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注定被他的时代封印。而这,几乎是大部分写作者的宿命。
五、了却了汪曾祺的一个心愿
最后,不妨说一段题外话。在王朔写汉武帝之前,其实汪曾祺也计划写一部名叫《汉武帝》的长篇小说。
文学季刊《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汪曾祺未竟的“汉武帝”写作计划》(作者徐强)。文中介绍:“他(汪曾祺)有一些系列作品的写作计划完成了,但还有若干计划则因种种缘故没有实现……长篇小说《汉武帝》的写作计划属于后者。”
据说汪曾祺为写《汉武帝》酝酿了十五年。他对汉武帝本人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倒不是因为他热爱这位皇帝,而是因为在汪曾祺眼中,汉武帝是一位“变态心理学”的代表,他的一生既是一部命运史诗、悲剧小说,也是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高度概括。
汪曾祺不是一位犬儒主义者,他只是一位清醒的“后撤步大师”,当你以为他“岁月静好”的时候,他其实在琢磨如何用婉转的方式,为过往遭遇的荒诞留下一份见证。所谓古人,无非假托言今的手法。
汪曾祺熟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对汉代乐府熟读成诵,他写汉朝该是活色生香、别具一格的,但可惜直到汪曾祺去世,《汉武帝》终未面世。王朔和汪曾祺文风截然不同,但他们曾身处同一片天空,感受过时代变幻的寒与热。王朔写汉武帝,或许不是为了歌颂汉武帝,而是写下一种长久发生在中国的命运。
作为人至暮年,棋手终局的作品,这本《起初:纪年》能否再度唤起新青年的感动?也许,这一次王朔打了一场漂亮的“败仗”,他的语言风格和精神气质一如既往,而他与时代的矛盾仍没有得到化解。但至少,比起许多早就罢笔的同代人,王朔的冲锋已经足够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