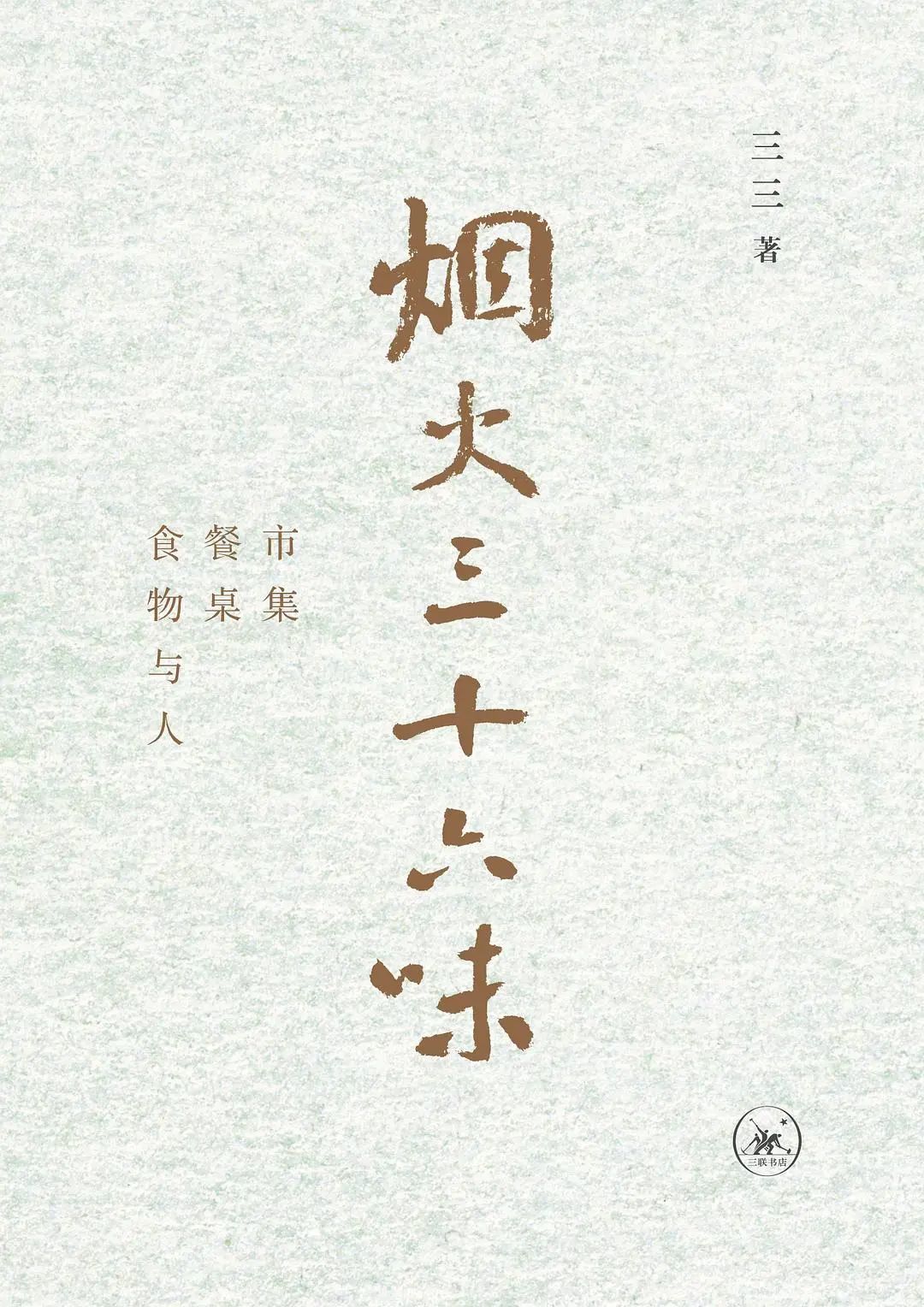没有鸭子能离开南京,没有牛能逃出潮汕
如果说中国数不清的各种美食有什么共同点,那想必就是它们都有着强烈的地方属性,和浓郁的人文气质。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夏各地的劳动人们创造、发展出了食材丰富、品种多样的食物,它们构成了各地独具特色的美食文化,也赋予了各地丰富的人文景观。
下文中,美食作家三三将带我们走访南京、成都、潮汕三地——
在六朝古都南京,感受南京人对于“斩只鸭子”究竟有多大的执念;到天府之国成都,体会方桌茶杯如何构筑起成都人心中的一小块自由天地;来到素以美食闻名的潮汕,看嗜牛的潮汕人如何将牛“吃出花来”……
“品尝”完这三地的美食,除了“垂涎三尺”,你也许也会想起自己故乡的食物。欢迎你在评论区与我们一同分享,你的家乡,那份不可替代的味道。
下文摘选自《烟火三十六味》,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南京的鸭:烹鸭的第一要务,鲜
鸭馔始于六朝,烤鸭自明代流行,清代《调鼎集》鸭菜有80多道,如今南京已是鸭都。一到饭点儿,老百姓的口头禅就是:走,斩只鸭子。家里来客,斩鸭子;老友欢聚,斩鸭子;懒得做饭,斩鸭子。只要上桌吃饭,就一定要有这只鸭子。
在南京人的心目中,国泰民安的意思就是天天都有鸭子吃。一百年前出版的《金陵物产风土志》里就写着:“鸭非金陵所产也,率于邵伯、高邮间取之。么凫稚鹜,千百成群,渡江而南,阑池塘以畜之,约以十旬,肥美可食。杀而去其毛,生鬻诸市,谓之水晶鸭;举叉火炙,皮红不焦,谓之烤鸭;涂酱于肤,煮使味透,谓之酱鸭;而皆不及盐水鸭之为无上品也。淡而旨,肥而不浓,至冬则盐渍日久,呼为板鸭。远方人喜购之,以为馈献。”吃鸭子之于南京人,就如同空气一样重要。
岁月再怎么变迁,南京人的舌头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统一。如今城里依然遍地鸭店,是名副其实的“鸭都”,大宗鸭市也属全国少见。且不说现在南京人每天能消费多少只鸭子,仅上世纪三十年代,城中三大板鸭店“韩复兴”“魏洪兴”“濮恒兴”,全年售出的板鸭、水晶鸭、冻鸭就已达三百万只。聊起鸭子经,南京人的讲究较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街头大小饭馆、菜场档口里,盐水鸭、烤鸭、酱烧鸭、煨鸭块、琵琶鸭、加汁鸭、珍珠鸭、黄焖鸭、鸭羹、熏鸭、松子鸭方,不计其数。
想吃鸭,先要选鸭。南京选鸭子讲究取入秋时的“桂花鸭”。正如《金陵物产风土志》中所说,南京城里不养鸭子,江浙传统养鸭人都散落在长江沿岸的水畦与湖泊上,豢养的鸭子大多以麻鸭、水鸭为主,与北京填肥的白鸭相比,肉紧实而脂肪少。养鸭子也有季节之分,一年产三拨,尤其以立夏前后新生的仔鸭为优。彼时溪水间小鱼、小虾、螺蛳正盛,鸭子自由自在地取食,给筋骨打下好底子。等到秋风起、桂花香的时候,再用新熟的稻谷给大鸭们增肥。如此养出的鸭子,身宽体长,胸腿肌肉饱满,称为“桂花鸭”。每至产季,江浙各大湖区、郊县的鸭子们,渡江涉水进入南京,是个阵仗极大的差事。一路奔波难免消瘦,鸭子们进城一般都暂养在莫愁湖与南湖一带,一围几百只,大群上千只,嘎嘎声破天,等歇几天才能渐渐缓过劲儿来。这时候老师傅就亲自出马去选鸭了。
城内已无蓄鸭池的踪影
挑鸭子也是一门学问。一群鸭子只需瞄一眼,羽色与身量出众者心中就有数了。随手拎几只,掀开鸭翅摸一把,肋下有两朵核桃大小的肌肉且充盈有力的,就是好鸭子。大馆子每隔一两日就要去蓄鸭池选几十只大鸭,自南湖市场一路赶回店里,鸭子们边走边把肚肠清空,进店后也不再喂食,等到凌晨时分就开始制鸭了。活鸭入厨,净毛、浸水等程序都要有经验的师傅上手,光鸭须清理至全身及头颈无一根杂毛,再用清水浸一两个小时,血渍去净,鸭皮白润饱满,无一丝破损。如今的禽类市场规范很多,鲜鸭全由鸭厂直供,重量、月份、品质一早细分,送进后厨的光鸭被处理得干干净净。老一套选鸭、制鸭的程序,小师傅们早就不学了。然而规模化、规范化的工业流水线,无形中也消减了几分南京鸭子的旧时风味。
光鸭摆到案上,师傅还须“因材施教”。四斤左右、肥壮洁白的大鸭是第一等,肉质细腻而皮薄鲜滑,专做烤鸭;三斤的略小,脂肪也少些,制盐水鸭;两斤左右,皮肤不够白的,做烧鸭;两斤以下,做红焖或小炒。然而不论几等鸭,也不管大店小馆,南京师傅烹鸭的第一要务就一个字,鲜。
在南京吃鸭,头一道就是烤鸭。金陵烤鸭是北京烤鸭的前身,京城“便宜坊”百年前刚现身就是打着“金陵烤鸭”的旗号。清末广东出现的“金陵片皮大鸭”,抗战期间四川流行的“堂片大烤鸭”,寻根都在南京。若是金陵烤鸭溯源,可至明代三叉之一“叉烤鸭”,另两叉是“烤方”与“叉烤鱼”。彼时南京城的宴席上号称有“八大叉”,叉烤火腿、山鸡、鹿脯、鸭子都作为主菜,并列入席。
人气很高的烤鸭档与鸭油烧饼摊
今天老百姓其实根本不在乎金陵烤鸭到底打哪儿来。大家最关心的只有自己家楼下那家鸭子店好不好吃。往南湖一带的老社区闲逛,水面上的蓄鸭池虽说早已消失,但是老南京人的舌头却从未忘记过鸭子。每隔几十米的路,必有鸭血粉丝店、烤鸭店、盐水鸭店、鸭油烧饼摊儿,家家墙挨着墙,档靠着档,看着就像一大家子。烤鸭店在后厨搭出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炉子,个把小时就能烤好十几只鸭子,刚出炉的鸭子全部大头朝下,倒插在大竹筐里,控干净余油,然后再亮堂堂地摆在档口里见客。下班回家的人路过,看着心痒痒就斩半只。小贩手脚极麻利,片刻间斩好的鸭子就连皮带肉整整齐齐地摆在饭盒里了。南京人吃烤鸭没有什么春饼、黄瓜、葱白的规矩,但一勺烤鸭汁是必备的。这勺绛红色的油汁以鸭油、酱油、香料、红糖熬制而成,咸鲜回甜,鸭香馥郁,甚至比鸭子还出彩,是小店揽客的真正秘诀。
地道的烤鸭店不卖盐水鸭,而盐水鸭店也不卖烤鸭,因为烹饪手法不同,从选鸭子开始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金陵盐水鸭讲究皮白、肉红、骨绿,鸭子的脂肪不能过厚,鸭皮白皙,制作工艺极繁复,八九道工序完成至少要十五个钟头以上。夏夜餐桌上一碟盐水鸭白中透粉,表皮上的每个毛孔都裹着盐卤鲜汁,嚼几下,鸭鲜迸发,消暑爽利兼下酒。
烤鸭店的鸭舌与盐水鸭店的鸭肝,是两项隐藏菜单,因为量少一般不会摆出来,只有熟客赶早来才能买到。前者火烤之后依然柔软多汁,后者盐卤之后丝滑裹舌。这一浓一淡摆在桌上,咂咂味道,咪咪老酒,乐趣无穷。
苏州人的大饼里夹的是猪油,而南京人的大饼里夹的是鸭油。鸭油烧饼现烤现卖,小山一般的鸭油酥就堆在案板上,每只烧饼里都要裹一块。贴在烤箱内壁的烧饼遇热膨起,鸭油香便从缝隙中钻出来,纠缠着每一个路过的人。鸭油烧饼也有甜咸之分,但是阿姨爷叔们最爱买刚出炉的原味大饼,夹上几块卤菜店里还温热的猪头肉,一咬满口油。
南京城里那么多吃鸭的好地方,谁也说不清最好吃的鸭子在哪儿,唯有一家一家去吃。全部吃完之后,也能算半个南京人了。
成都的茶:喝茶从来都不是最终目的
成都人上茶馆是为了见人、谈事、发呆、找安逸,区区几块钱一杯淡茶,能从早坐到晚。
茶馆在成都遍地开花,不过是两三百年间的事。这习惯似乎始于清初,朝廷为征西藏、川西大小金川,调满洲蒙古兵二十四旗入川。官兵们拖家带口数千人进驻成都,重建少城,开辟胡同,生根发芽。今日成都地图上依然能清晰地看到,长顺街俨如脊背,串起东西几十条胡同,齐整如军营。就连人气景点“宽窄巷子”也出自满人手笔,原名“仁里胡同”。生在京城胡同里的茶馆,就这样也跟着入川了。
两百年前的成都就有街巷五百条,茶馆四百家,全城六十万人,除去一半妇女儿童,每天有十万大军泡在茶馆里。官吏、商贾、贩夫走卒,彼此交通,不同世相皆在一张桌前粉墨登场。茶馆多了就有圈子、用途之分。文人茶馆须选址幽静,铺白桌布,提供报纸杂志;洽商茶馆要空间宽敞,架势摆足,茶桌茶具茶食皆精致;听戏听书也要上茶园,有搭戏台唱川剧的大场合,也有说书先生、板凳戏的小场合;三教九流泡茶馆不拘什么地方,公园、水边、佛寺、祠堂,只要有块空地,放几张桌,拉个天棚,掀开盖碗,支起老虎灶,就能从凌晨四时喝到午夜时分。
大众茶馆一条街总有一两家,茶桌短腿必定斑驳,桌面一层油泥,看着邋遢,但透着轻松。落座大半是竹椅,矮而有靠背,半躺半坐下来,舒服得长吁一口气。再破的茶馆也不用大茶碗,清一色盖碗,但十碗九豁,能讲究也能凑合。茶客们彼此背靠背,脚下踩着从四面八方丢过来的瓜子皮、花生壳。摆龙门阵,开口都当对方聋子一样,提高音量大声喝出,家常八卦、天下新闻,各嚷各的。距离越近越是彼此听不清,肆无忌惮,无拘无束,最后汇成一片巨大的嗡嗡声。
若是一个人没什么话想讲,静坐喝茶,闭目养神,听着隔壁桌风云变幻,也不寂寞。掏耳朵的、算命的、擦鞋的、按摩的、卖茶食的,在身边穿梭,伸伸手就能找点舒服。要是饿了,隔壁面馆、二荤铺、豆花坊的小贩一早就准备好了,只要招呼一声,马上就有人两三下摆满一桌。花小钱,大热闹,听新闻,遣辰光,茶馆可比自家客厅快活多了。
如今京城茶馆式微,成都却依旧火热,被视为传统文化,细心呵护。比起往昔,现在城中的茶馆数量至少翻了两倍,有临河搭起的竹楼,有沿街露天的茶座,也有进门是假山、花木透香的豪华茶馆,酒店里还有西式红茶、西点,吃下午茶……人气最旺的还是传统老茶馆,人民公园、望江公园、南郊公园、大慈寺、文殊院,名号最为响亮。
人民公园是少城内第一大园,清末民国时期就是成都人小聚、集会、募捐、演出的首选,曾经园中仅茶馆就有浓阴、绿荫阁、永聚、鹤鸣、枕流、同春、射德会、文化、荷花池等近十家,每个茶馆就像一角社会缩影。
有权势的士绅聚在“绿荫阁”和“浓阴”,少有警察、袍哥去那里喧哗,连地下党也在那儿接头;谈生意在“永聚”,练家子去“射德会”,“枕流”是学生据点,还附设澡堂子;教师文人多在“鹤鸣”,边吃茶边把时事添些佐料,搬出来闲谈。局势紧张时,官府甚至在“鹤鸣”茶馆里贴了一道“诸君吃茶,勿谈国事”的禁条。今日人民公园内仅存了一家“鹤鸣”茶社。
“鹤鸣”茶社位置极好,传统的中式长廊沿湖而建,荷花、绿树、游船,四季景移。门口牌坊上挂着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走东西”,说的正是成都茶馆的真谛。廊内廊外铺满木桌竹椅,每日数千人在这里叽叽喳喳地吃茶,桌桌放一个暖瓶,添水自助,老虎灶、掺水工早就消失了。紫铜大茶壶成了表演道具,每隔一会儿就有人在空场上耍一套,游客围着拍照。
虽说这样聒噪,还是有个把老成都散落其间。中午到了饭点儿,游人退去,就能看到穿着白袜布鞋、麻布衣裤的中年男人,双手交叉于脑后,半躺在竹椅上,脚跷起蹬在小凳上,双眼半眯,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偶尔翻个身,头始终朝向湖面。可能心里在盘算着什么,也可能什么都没想。只要看看他脚下瓜子壳的面积、烟头数量,就能判断这人坐了多久。
再看看面前那杯半凉的碧潭飘雪,这是“鹤鸣”的看家茶。取峨眉山一带明前嫩茶芽与伏天鲜茉莉,沿袭京城满人的喜好,窨制起香,芽叶挺立,花瓣雪白。这种川式花茶浓烈耐泡,一二碗喝着刮嗓子,三四碗后脊微汗,六七碗腋下生凉。有这么一杯茶陪着,保管坐得稳,摆得欢。盖碗还隐含着暗语,茶盖掀在桌上,表示要走;合盖往中间一推,表示去去就回。
茶馆人气越旺,周边的小吃摊儿、苍蝇馆子就越多。喝累了总要填填肚子,再继续接着摆。蛋烘糕、豆汤饭、糖油果子、凉糕、粉蒸肉、牛肉焦饼、龙抄手、蹄花汤……花样多得数不过来。走出人民公园的大门,街头巷尾远远就能闻见蛋烘糕的香软气息。上了些岁数的爷叔手艺最好,守着几个扁平的铜炉,浇上浆汁,左右摇匀,加盖略等片刻,一张黄嫩薄软的蛋烘糕就成了,还能夹上芝麻、核桃、花生,一口咬下香甜酥脆,润和喉咙。
糖油果子与红油抄手
隔壁的糖油果子是能上溯到宋代的吃食,具体吃法是以微微发酵的糯米粉团,搓成圆球下锅炸熟,趁热再厚厚裹上一层焦红糖,三四个成一串,举着边走边吃。米果子过热油而鼓起,外脆中空,咬起来有淡淡酒酿的香甜味,外加糖皮的脆甜,老成都几乎人人爱吃。
曾经听过一个成都人说,饿的时候吃牛肉焦饼,比捡到一万块钱还解恨。一只煎到金黄酥脆的焦饼,烫烫地捧在手里,油香与肉香直往鼻子里钻。怕烫又嘴急的啃上一口,牛肉汁顺着饼皮淌下来,什么烦心事都忘记了。
想要体验老成都风貌的茶馆,菱窠茶舍是个好选择。“菱窠”翻译过来就是菱角窝棚,是菱窠西路上的一处老宅,1939年日本人轰炸成都时,四川文人李劼人为自家茅草屋起的雅号。李劼人留过法,当过成大教授,在军阀眼皮底下开过报社写檄文,他笔下的老成都格外生动。因为懂得调羹之乐,非常时期李劼人还开过饭馆儿,文人菜烧得有声有色,全城大人物纷纷来光顾。
他在“菱窠”长居了二十四年,直到去世。旧居带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往昔成都的记忆,而开在隔壁的菱窠茶舍,也沾染着旧日气息。茶铺木廊高架,梁上挂着竹笼,七星灶内三江水滚,竹椅宽大,任人翻来覆去地跷脚拽瞌睡,一杯一心桥茶厂的老三花茶,味道顺畅。下棋的、掏耳朵的、吃豆花的,气氛始终静谧。
在成都泡茶馆,喝茶从来都不是最终目的。方桌茶杯之内,泡的是大家心中的一小块自由天地。
潮汕的牛:一只只生得油光水滑
吃牛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工业革命之前,温和又倔强的牛是农业社会的脊梁,殖谷之王。它们日日身负百斤耕种,被看作家庭的重要一员。直至清中后期,政府依然特禁屠牛,只有除夕祭祀时被誉为“犊祭祀”的全牛才会出现。食牛似乎是一种被压抑了数千年的欲望,一旦开启即刻成瘾。
全世界嗜牛的人不计其数,知名牛种如日本和牛、美国安格斯牛,不仅各自衍生出一套繁复严苛的养殖标准,还有针对原产地、血统以及食用的细则。美国牛的干式熟成法迫使专业的牛扒餐厅要先盖一间恒温恒湿的熟成房,再等待数月,才有一口牛肉吃。一块布满大理石纹油花的拍卖级日本和牛块,以白布包裹,灯光照亮,置于专属木盒内,厨师看它的眼神虔诚如信徒。相比之下,中国黄牛的出场亮相就质朴得多。
离开潮州与汕头之类的大城,车行潮阳、普宁、揭西一带的乡间,大小村落紧密连接在一起。冬日阳光依然炽烈,午后甚至有夏日炎热感,晚稻已收,早稻未种,大片土地一览无余,时不时就能看到牛。黑毛、角长而弯的是水牛,黄皮、角短而直的是黄牛,无人看管,它们就三三两两散在田间,啃食嫩草,或立或卧。即便靠近些,也闻不到什么异味,一只只生得油光水滑。
其实潮汕并不产牛,中国黄牛的发源地在鲁西、河南一带。如今潮汕本地牛很多来自川黔。中国牛的肉质并不肥嫩,和昼夜咀嚼玉米粉的美国肉牛很不同,它们也从不喝啤酒或是做SPA,仅仅白天啃嫩草,晚上嚼稻壳,长得肌肉发达、纤维粗壮、脂肪单薄且均匀分布,牛味浓厚。这种传统散养的方式并不适合大量聚集牛只,所以潮汕本地的黄牛数量很少,每家农户不过蓄三五头,基本都被各区域的“牛经纪”早早下订。
吃牛在潮汕久已成风,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几间牛肉神店,打边炉喜欢小母牛,细嫩清甜,制牛丸喜欢小公牛,爽滑脆弹。嗜牛的人隔几日就得去涮几碟鲜肉,不然浑身不舒坦,甚至还能看到深圳、港澳的食客,驱车几百里特意来潮汕啖牛。
本地人想吃鲜牛并不是靠高价买断,而是靠人情维系。一个自然村里村民上数三代很多是直系亲属,养牛的、屠牛的、买牛的同一个姓氏,形成饲场、屠场、运输一条龙,彼此紧密衔接,外人也插不进脚。牛只午夜屠解,天光未亮已在案头,鲜肉滴水未沾,大力一拍还能见神经末梢在跳动。别说供给上海、北京,就连当地人也不够吃。尤其一头两百斤牛身上那些只得五六斤的刁钻部位,必须是与店主熟识、又勤于赶早的老饕,才能一窥。
在潮汕人心中,吃牛根本等不到什么排酸期,四至八小时之内上桌,越早肉汁越充沛,牛味越鲜浓,一线牛肉火锅店都靠这招撑生意。鲜牛每天进店可能是清晨四时,也可能是下午四时,牛骨清汤提前熬好,同样是每天一次或者两次。整牛进后厨,解牛的都是年轻男子,一身短打、寸头,持大刀,三五个站成一排,将各个部位多余的脂肪与筋膜仔细剔除。大块鲜牛挂在铁钩上,颜色绛红,脂肪不是死白而呈现鹅黄色,代表牛只是食草长大,在城市中很少见到。
有内部消息的老饕赶时间上门,去吃第一波现熬牛骨汤浇出来的牛杂,毛肚、小肠、百叶、肚仁、肚尖儿……什么部位都有;也有专爱肉眼边或肉眼芯儿的,切成薄片布满油花,热汤浇下五秒即色变,牛香充沛。第一口先尝原味,第二口蘸些沙茶酱,这样就能知道“新鲜”两个字究竟怎么写。
潮汕人吃任何食物,都讲究“咬口”,吃牛当然也不例外。牛肉火锅店里,当街怒啖十几碟牛肉的壮汉不在少数,而下锅第一碟通常都是牛丸。潮州牛肉丸是弹滑爽口的代名词,选脂肪少、黏性足的小公牛臀肉最佳。如今手捶牛丸基本绝迹,北京、上海的潮汕牛肉火锅店还会放些手捶表演,而本地火锅店的客人都熟门熟路,不用看“花腔”。火锅店老板通常并不手工做牛丸,而是与相熟的作坊合作,订制牛丸。
牛丸作坊通常选在四周无民宅的地方,午夜开工。机械铁棒模仿人手,捶打大桶肉泥,嘈到拆天。为防止机械生热影响肉质,捶肉桶之外还套着冰桶,师傅会根据肉泥细滑程度,随时调整节奏并降温。直到空气充分渗入肉泥,弹劲儿十足,才盛到盆中。手挤牛丸则不可以机器替代,全凭人工。几个女工坐在木凳上,守着肉盆与水盆,左手捏肉用虎口挤出乒乓球大小的牛丸,右手持瓷勺,丸肉应声沉入热水盆,生丸遇水下沉,十几秒内由红转白,定型上浮。半小时内热水盆中就挤满肉丸,蔚为壮观。只有凭借人手挤出的牛丸才筋道弹滑,机器从未能模仿出。
胸口朥以及各色涮牛味碟
汤锅上桌,先下一碟牛丸。不用在乎火候与时间,沸汤滚牛丸越煮越鲜,越煮越嫩。一口咬下清脆爽利,肉中含汁,弹力十足。其实,潮汕本地除了牛肉火锅店,更多是牛丸汤铺。牛骨清汤里浮两只牛丸,再烫些西洋菜、腐皮、粿条、芹菜粒,呼啦啦吃下去,肚皮能撑半日。还有多加了筋肉的牛筋丸,口感更粗犷爽脆。
重头戏当然还是涮牛。本地人把牛肉大致区分为八个部位:嫩肉、匙柄、吊龙、肥牛、脖仁、五花趾、三花趾、胸口朥。不同部位依照生长纹路有不同的切法,比如匙柄要长而薄,吃起来才滑;吊龙带肥,厚切油脂更为甘香;五花趾与三花趾多粗筋,横向薄切嚼起来脆生;嫩肉最多最寻常,厚切沾些牛油,老少皆宜。不同部位依口感的脆、嫩、滑,被严格限定了涮煮时间,通常整碟入漏勺,在滚汤中上下搅动均匀受热十至十五秒不等,待鲜肉变色,立即夹出蘸些沙茶酱,趁鲜分食。
只有胸口朥费些工夫。这是牛胸前一层薄薄脂肪,新鲜呈乳白色,略带嚼劲,冷冻后会发黄,除了潮汕火锅在其他料理中鲜少使用。涮胸口朥要花费十几分钟时间,大片带筋牛油会收缩成晶莹透亮的小团,每层筋膜中都裹着几滴鲜油。入口爆油而不腻舌,带着甘香尾韵,风味醇和。
潮汕嗜牛,每条街巷都有食牛馆,不似高端牛扒金贵,庶民也能日日食。外地食客也不用过分迷信名店,整体水准偏高的潮汕牛,风味浓得凭视觉就能分泌唾液。几年前这阵牛潮席卷全国,北京半年之内曾开出上千家潮汕牛肉火锅店,良莠不齐,几年后所剩无几。可见食牛看重肉味天然,并非那么容易复制。
本文节选自
《烟火三十六味》
作者:三三(刘珊珊)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