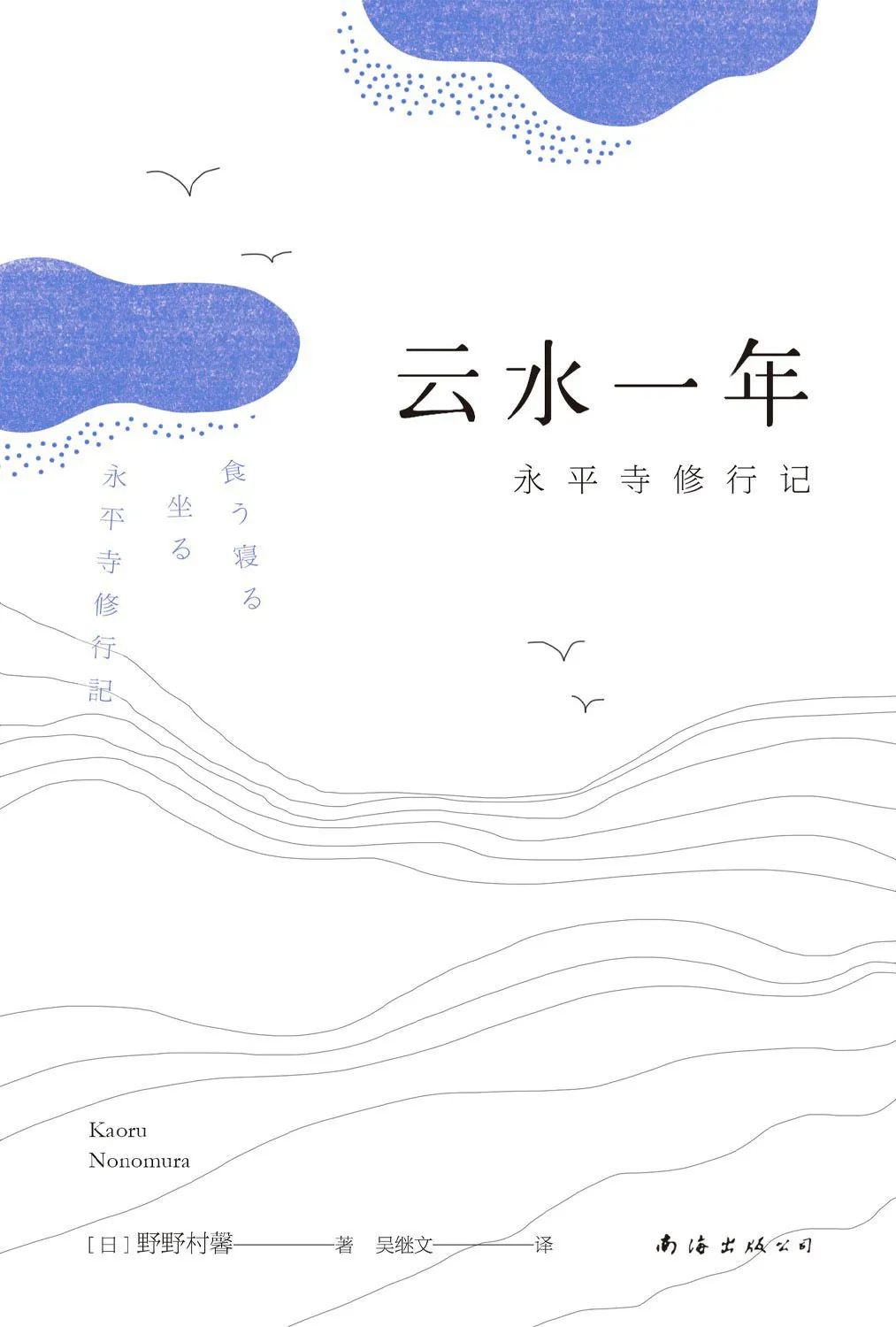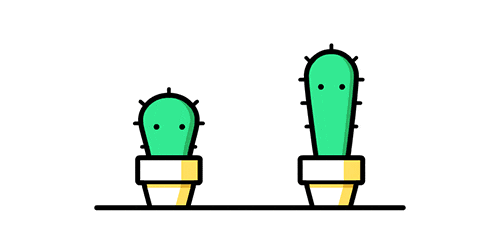三十岁那年,我出家了

关于出家,从起心动念到变成一股决心,并没有经过多长时间。
“我要去永平寺了哦。”
在爸妈家的餐桌上,我一边吃晚饭一边对他们说。
“是吗,什么时候去?”
对我所谓“去”的意思完全理解错误的妈妈,用那种好像自己也想一起去的语气问道。
我说明了下定决心的原委。但他们的惊讶之情比我想象中还轻微,让我多少有些错愕。
惊讶还是有的,但在他们看来,比起我老爱去亚洲政局动荡的国家或一般观光客不去的偏远地区旅行,成天担心我遭遇不测却无计可施,或许去永平寺还更叫他们放心也说不定。
在为上山去永平寺做准备,一一整理身边琐事的过程中,逐渐感觉社会离我越来越远。
想想还真是滑稽。由于对社会生活的倦怠,对身边一切都感到厌烦,难以忍受,为了逃离,于是决定出家。可一旦社会开始慢慢离自己远去,却不禁有些落寞,一天比一天伤感。
从每天下班后去游泳的泳池大窗看到外头满开的樱花,好几次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最后的樱花喽”。梅雨天突然放晴的时候,在镰仓的山路上突然看到提早露面的夏日蓝天,也会自心底涌起一阵恨意。
只要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人格外珍惜,好想紧紧拥抱。而对于逐渐加速的季节之流转,总是感到无来由地哀伤与恐慌。
就在这样的心境下,夏季尾声的一个周末,峰子来逗子的租屋处找我。
“听到野野村君要出家的消息,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呢。”
两人并坐在屋侧的走道地板上,仿佛观赏电影般看着眼前的小小庭院,峰子低声嗫嚅道。
“真的?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挺理所当然的。”
“是吗。”
峰子是大学时代认识的朋友。虽然我们平常往来并没有特别密切,但都很珍惜两人共度的时光。这种微妙的距离,是对彼此的体贴。
“这件事,不会是悲剧吧?”
“啊……当然不是。”
她突然这么一问,叫我迟疑了几秒才回答。
“我不希望这样。如果变成悲剧,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自己也不太确定。对于将要重启的人生,不可否认我是怀抱希望和期待的。但另一方面,我又忍不住有视作悲剧大哭一场的心情。
“那,我等你可以吗?”
手上装了冰麦茶的玻璃杯里冰块发出“喀啦”一声时,峰子问了一个意外的问题。我马上明白了峰子“等”的意思。
“咦,等?到底要等什么呢?是说想要躲在哪里等我剃光头后跳出来大声笑我吗?与其这样,不如像我以前告诉你的那样,找个善良又老实的上班族大谈一场恋爱,然后到无人岛举行婚礼吧。我到永平寺以后大概是没办法出席你的婚礼了,不过我一定会在寺里诵经,祝愿你们永浴爱河的。”
“……”
峰子八成是哭了。两个人认识以来,第一次陷入如此漫长的沉默。虽然不确定是因为什么,但过去无疑怀抱过的想要在社会上打拼的一点热情已经不在,连像一般人那样过日子都没办法,于是选择逃脱。我希望峰子不要等这么没用的家伙,并真心诚意祈愿她幸福。
我们都没有看对方,只是并坐在屋侧地板上。风从开始失去夏日灿烂辉光的海上吹过来,我们凝望着眼前被风吹得摇摆不定的枫树,定定地、定定地看着。
穿过寺前商店街时雨势稍歇,铅灰色天空也比先前明亮了。沿路仿佛精细镶嵌出来的小商店一间连着一间,因为下雨而失色的风景当中,色彩鲜艳的土产、纪念品显得特别醒目。当我微微抬起被雨水打湿而稍显沉重的网代笠,看着笔直街道的尽头时,突然停下脚步。
“看到五代杉了!”
树龄据说有七百年的高耸巨木,在水汽氤氲中若隐若现,强烈的威压之感迎面扑来。在五代杉下面,永平寺的山门应该是开着的吧。我终于来到了这里。
永平寺
的确,从起心动念到下定决心出家,并没有经过太多挣扎。问题是之后,“现在还来得及后悔,如果要放弃就趁现在”的念头,那种内心深处剪不断理还乱、对红尘俗世的眷恋,就像一波波涌向海岸的怒涛,总是周期性地向我袭来。如今穿行在寺前大街,抬头看到五代杉时,心中又掀起了最后一股巨浪。
这是回头的最后机会了。突然觉得血液一阵沸腾,全身冒汗,仿佛被高耸的五代杉震慑而不得不后退似的。
然而我还是迈出了下一步。此时此刻,除了再度前进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水撞击在岩石上,遇到堤坝停留打转一下,最后还是流到了这里。我相信就这样顺势流进永平寺山门,是最自然的结果了。
再次迈步时,突然被泡了雨水的草鞋之沉重吓了一跳。饱含雨水的沥青,因为冰冷而僵硬的双脚踩起来反而觉得柔软异常,简直像要被吸进地里一样叫人难以举步。
一旦开始感觉,到此刻为止已经麻痹的身体五感同时苏醒,才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由于下雨而冻得厉害。搭在背上的行李,由于无数的不安加上若有若无的希望,重重地压着双肩。
身心都在颤抖,发出“嘎嗒嘎嗒”声。脚步益发沉重,雨水也更加冷冽地渗进皮肤。
就在这几乎要被冷雨击溃时,正好经过一家茶店。从打开的窄仄入口里边,一个老婆婆忽然出现,颤巍巍地跑到我身边,对着我大声说:“云水桑(云水取“行云流水”之意,指为了修行而云游各地的行脚僧。“桑”是对人的尊称)加油哦!”
一瞬间,因寒冷和紧张而僵硬的双颊突然滚下两行热泪。为什么会流泪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停不下来。仿佛到那一刻为止一路所背负的失望与沮丧、后悔与眷恋等等念头,决堤一样与泪水一起从双眼流了出来。真想大声号啕,将心中郁积的那些纠结的情绪全部流得一干二净。
直到今天,我仍忘不了当时滚落脸颊的灼热泪水。
总算把模糊的泪眼擦干,我也来到了地藏院的斜坡下。这里是永平寺上山云水的所在。
当我抬头看着地藏院时,内心已经一无烦恼。接下来就是走上这道斜坡而已。之前一路走来的岁月感觉变得如许悠长。脑海中不断闪过人生至今的各色光景。
只要登上这段斜坡,人生中的某些部分也就告一段落了。
父母、朋友叫人怀念的容颜,在脑海里闪现又消失,我对着他们一个个说“谢谢”与“再见”,然后走上斜坡。
登上斜坡后,我依照预先收到的指示,拉过门口旁边挂着的木板,以木槌用力敲打了三下。每打一下,木板干硬的声音也在身体深处回响。
这座地藏院是永平寺的塔头(大寺所属的分院)之一,自愿上山的人正式上山前一天在此暂住一宿,接受上山的各种点检与指示。简单说,地藏院就建在娑婆与佛界的界线前面一步之处。
打过木板,我从正门进入地藏院内,看到先来的两位正默默地闭目伫立。我没说什么,也学他们朝向地藏院大门站着。
从现在开始会发生什么事,我一概不知。唯有用力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即听到雨滴从屋檐滑落到石板地迸散的声音,在背后广阔的寂寥之中激起轻微的回音。
不久,陆陆续续又有人敲打木板,八名上山者都到齐了。每个人都因为前程未定而难掩不安,双唇紧闭,一动不动。
上空低垂的雨云不知何时散去,地藏院的屋檐下照进温和的春阳,突然紧闭的大门打开了。
眼前出现的这位云水,仿佛独自承担了世上所有不满,表情苦涩严峻。
我们听从他用凶恶口吻发出的命令,从边上开始一个一个大声报上自己的名字。每个人卯足全身力气,几乎是喊出来的。
“听不到!”
立刻被骂了回来。
“只能发出这种声音的家伙,休想修行!”
“像你这样的家伙,不如滚回家去算了!”
我们的声音够大,不可能听不到。这样不合理的回应,首先是在考验上山者愿心的强弱。
每个人一次又一次声嘶力竭,感觉全身血液都要逆流,从喉咙喷出来似的拼命喊叫。在交错的呐喊声中,只有获得允许的人才可以脱下草鞋,走进沉重的木门里面。
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外面。每次用力呐喊,声音就变得沙哑一些,更加难以发出想要的音量。天晓得我还要像这样喊多久。
早春的残阳逐渐暗淡,当最后一道光线自地藏院屋檐下隐去时,四周立刻被山间的冷冽空气所包围。
终于获得允许脱下草鞋的时候,整个山区都已经被夜色笼罩了。从冻僵失去知觉的脚上脱下濡湿而坚硬的草鞋和足袋后,我总算可以走进屋里。
进去一看,里面不是别的,是小而美的寺院本堂。走上前去,首先得到的指示是用准备好的纸砚,写下自己的姓名与来历。纸上已经依照脱草鞋的先后顺序写好了名字。
此刻,一旦在这张纸上写下姓名,就要与之前社会的各种关系完全断绝。墨水开始渗入纸张的刹那,手上的笔也轻轻颤抖着。
看到我填好所有资料以后,负责的云水只留下“接到下一个指示之前给我正坐等待”一句话,即转身离去。
比我先脱草鞋的同伴已经面朝里默默端坐。我也依照指示,将硬邦邦的脚打弯,坐在他们后面。
时间分秒前进。即使地藏院墙上挂了钟,也没有心情去看一眼。另有别的东西让我们明确感知到时间的流动。那就是逐渐发疼的脚。
榻榻米变得像石板一样坚硬,慢慢地,两脚除了疼痛以外完全失去其他知觉。那种痛就像脚要被折断一样,叫人突然一阵恍惚,睁眼一看,其他七个人也正为脚疼而痛苦。
一直不被允许脱下草鞋、最后才开始正坐的我,比起他们,疼痛想必轻多了。他们的疼痛肯定比我剧烈好几倍。我对自己的松弛涣散感到羞愧,赶忙抖擞精神端正坐好。
突然天井的电灯亮起。在我们与脚痛格斗期间,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只有在重见光明时,才惊觉到时间无形无影却分秒流转不息,我们已经被夜色包围了。
电灯亮了以后,刚才的云水再度现身,以明快的指示带领着我们。看来晚餐已经开始了。
本堂的侧边有排列成“ㄇ”字形的长桌,一汤一菜装在朱红色食器中整齐摆放在桌上。最大的食器装的是米饭,次大的装着味噌汤,最小的里面放着一点青菜。最后传过来一盆酱菜,每个人拿筷子夹几片放在饭碗的边上。
负责的云水确认一切都分配好后,即简单说明,教我们应和名为“戒尺”的拍子木打出的节拍声,一起唱诵《五观之偈》,接着就开始举起戒尺缓慢击打。同伴们跟着唱诵起《五观之偈》,唯一不会的就我一个,只能错愕地站着。
由于身心处于紧张僵硬的状态,根本忘了肚子饿这回事,等到食物像这样在眼前一一摆好,肚子立刻饿了起来。麦饭也好,油炸豆皮煮的味噌汤也好,还有煮得几乎变成透明的白萝卜片,每一样看起来都比平常好吃很多。
但是并没有慢慢咀嚼品味的时间。装在大药罐里的茶汤已经传过来了。邻座同伴接过药罐,将茶汤注入装麦饭的碗时,我心里叫了声“完蛋”。
我把酱菜吃得一干二净。开始用斋前,我们接到的指示是不要把酱菜全部吃光,留下一两片,最后茶汤倒进饭碗时,可以用酱菜来刮洗容器,再把汤水喝光。
已经吃进肚子,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装作用筷子夹着酱菜,在碗里刮了几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将茶汤喝光,满嘴都是焙茶的清香与甘味。
吃过晚餐后,又来了三四名云水,开始点检行李。我们面对面排成两列坐下,面前摆着今天各自带上山的袈裟行李和后附行李,加上一具坐蒲团。接着依照指示顺序解开行李。行李里面的东西,都是上山之前通知单上详细规定的。
袈裟行李中放的是:袈裟、血脉、龙天善神轴、《正法眼藏》、上山许可状、印鉴、保险证、应量器一式;此外还有修行期间本人因故死亡时,作为吊唁用的涅槃金一千元。
后附行李中则有:盥洗用的牙刷、牙粉,净发用的单刃安全剃刀,袜子与足袋,以及针线盒。
这些物品依照一定的折叠、收纳方式分别装在两个行李袋中。
每个人都接受详细的行李检查,规定之外的东西一律没收。我的手帕被没收了,其他人则是现金、手表、肥皂、成药。还有一个同伴因为花粉症过敏而带了一大堆卫生纸,这些全都被没收。没收物品被放到写了各自姓名的塑料袋里统一保管。
点检完成后,接着将解开的行李再度回复原状包好。两件行李都是用几块鼠灰色的棉布包裹的。这几块棉布不单用来包裹行李,同时也是修行生活中不时会用到的洗面手巾、服纱、护膝布。行李就是将这些布巾以仪礼般繁复的手法加以包裹。
终于包好之后,我看一下其他人的情况,发现有人完全呆在那里什么都没做。
“嘿,为什么不会包?这么重要的行李竟然不是自己打包的,你哪根筋不对!”
云水一边怒骂,一边狠狠甩他巴掌,我们都被那惨烈的声响吓到,一起转过头去看。
由于事出突然,被打的同伴眼睛睁得大大的在那边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当然,我们其他人也因为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而狼狈不堪。
到此为止,今天表面上看似寻常的光景,瞬间被撕得支离破碎,露出可怕的、暗黑的真相。会不会我们来错了地方?
行李的点检告一段落,我们从原地站起来,开始点检衣服。衣服也和行李中的物品一样,都在上山通知里做了详细规定。
当天全身的装束是这样的:纯黑无花纹的直裰、纯黑的络子、白色以外素色的袍子、黑色手巾、角带、白脚绊、白足袋、网代笠。内衣为白色,如太长则必须自手肘、膝盖以下剪断。眼镜必须是黑框的。
所有人排好队后,由一名云水负责指挥,一起将身上穿的衣服一件件顺序脱下。每脱下一件,即教给我们正确的折叠方法。最后身上只剩下内衣,内衣也一一点检。点检结束,接着以相反顺序,以正确方法将刚才脱下来的衣服一件件穿回去。
在永平寺,依照规定作法正确而优雅地整束自己的外表,也是修行的要素之一,受到特别的看重。问题是,我们这些人直到昨天为止,都是一路穿着西式服装生活、工作过来的。和依照身体线条立体剪裁的西式服装不同,直线裁剪的传统衣袍,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穿得惯的。又有几个同伴被大声斥责。
好不容易大家都穿戴好了,接下来教我们在永平寺举行种种法要或仪礼时须知的各式基本进退。
首先是合掌与叉手的正确姿势。双手合掌时,指尖高度要与鼻齐。叉手则是左手握拳,拇指置于拳心,然后再以右手包覆之,放在胸口的位置。基本上除了坐着还有合掌之外,都要这样叉手交握。如此一来,无论是站着还是走路,手都不会摇来晃去。
其次,合掌或叉手时,我们的手肘都必须撑开举高,手肘位置的高低,也是用来判断古参或新到尊卑序列的方法。
“你们这些家伙怎么回事,只会这样合掌吗?”
或许是紧张和害怕的缘故,身体僵硬而反应迟缓的同伴,马上就被扇耳光。在被扇的瞬间,他们条件反射式地举手来挡。
“喂,你的手在干吗?怎么教你的,混蛋!”
连骂带打,巴掌一次比一次用力。肉打在肉上迟滞却刺耳的声音响彻堂内。同伴的脸颊很快又红又肿。
“你们给我听好了,绝对不许反抗,知道吗?”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对一个毫无抵抗的人施暴的场面。
之后还是直接教我们各式各样的进退仪节,对做不好的人照样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大家错愕万分,一方面明白无法反抗可能的后果,一方面拼命记牢云水前辈的教导。
对古参要绝对服从。不管任何场合,都不许直视古参的眼睛。和古参说话,唯一可以用的词就是“是”或“不是”。
我们毫无例外都是接受近代教育长大的,从小就被教导平等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要注视对方的眼睛,以适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才是待人接物应有的态度。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全部被否定,平生所知所学,以及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在此简单地被彻底抹杀。
在责骂、踢打中硬着头皮学习一连串的仪节作法,终于告一段落,取出靠里边的橱柜中收纳的棉被在堂内铺好,就寝时间就到了。
内心很想早一点休息,却怎么也无法入睡,只能不断地翻来覆去。可即使能够安稳入睡,明天早上醒来以后将要面临的种种状况还是叫人非常不安。光是想一下都快喘不过气来,胸部觉得闷闷的很不舒服。
在完全看不到一点光明的幽暗之中,突然有掉进水里的感觉。不管往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没有可以爬上去的岸,也没有可以抓的木片。为了呼吸,拼命用手脚划水,只能勉强让脸浮出水面。不知道像这样窒息般的痛苦,我到底还可以撑多久。
可是一旦来到这里,就已经没有退路。入口和出口都被重重地堵死,如今要做什么都不可能了。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
脑海里尽想着这些负面的东西,不经意转头看看两旁,其他人也一样睡不着,眼神呆滞地看着一片漆黑的天花板。是啊,受苦的不只我一个人而已。身旁的同伴正在和我一起分担痛苦。这念头是那个晚上心中唯一的安慰。
闭上眼睛注意倾听,分不清是雨水滴落还是激流撞击岩石发出的水声,在地藏院外面的漆黑之境轰轰作响。
本文节选自
《云水一年》
作者: [日]野野村馨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 青马文化
副标题: 永平寺修行记
原作名: 食う寝る坐る:永平寺修行記
译者: 吴继文
出版年: 2021-1-1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电影《海街日记》《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