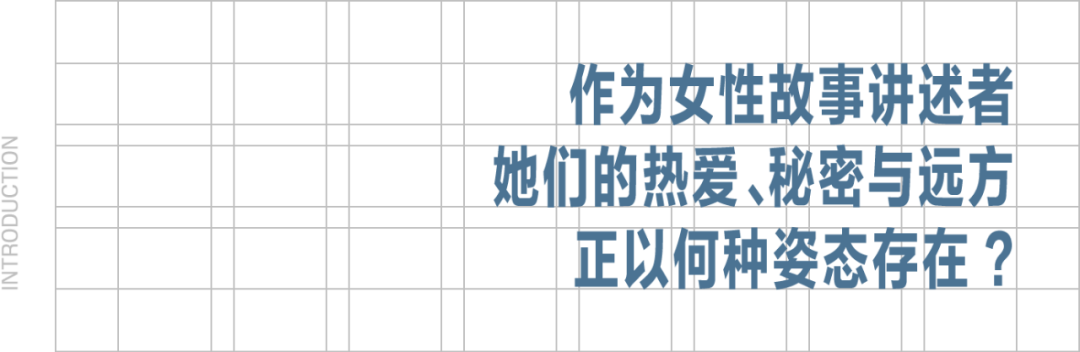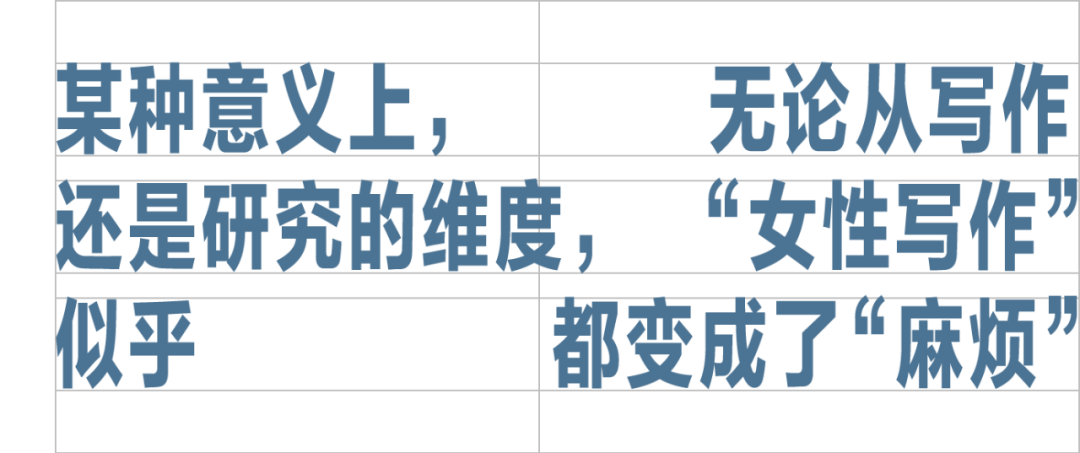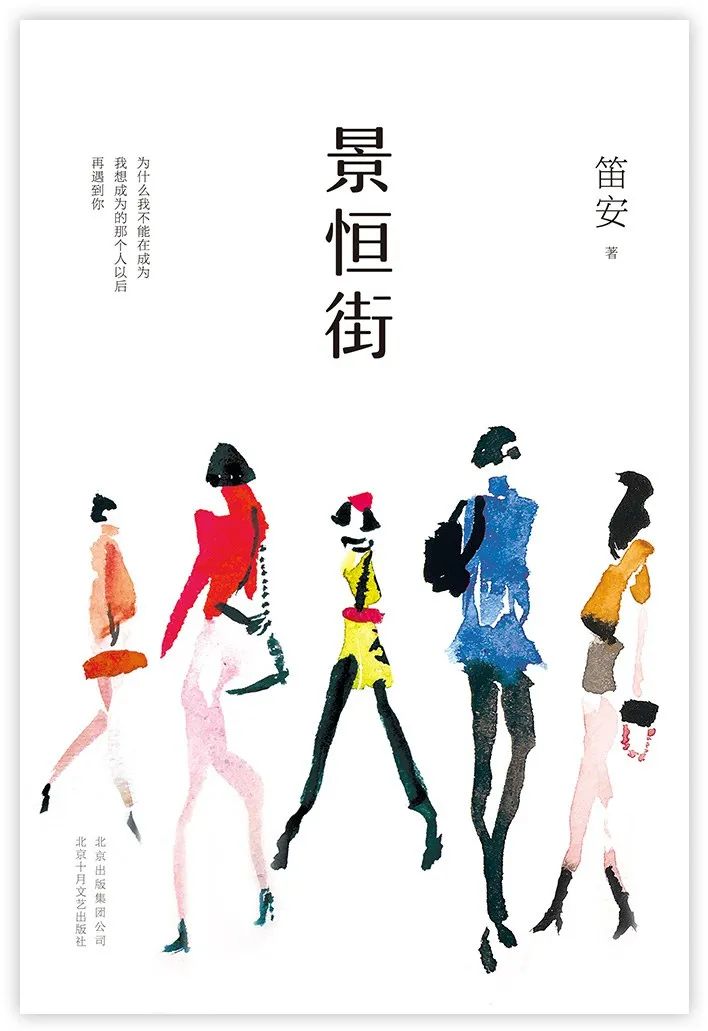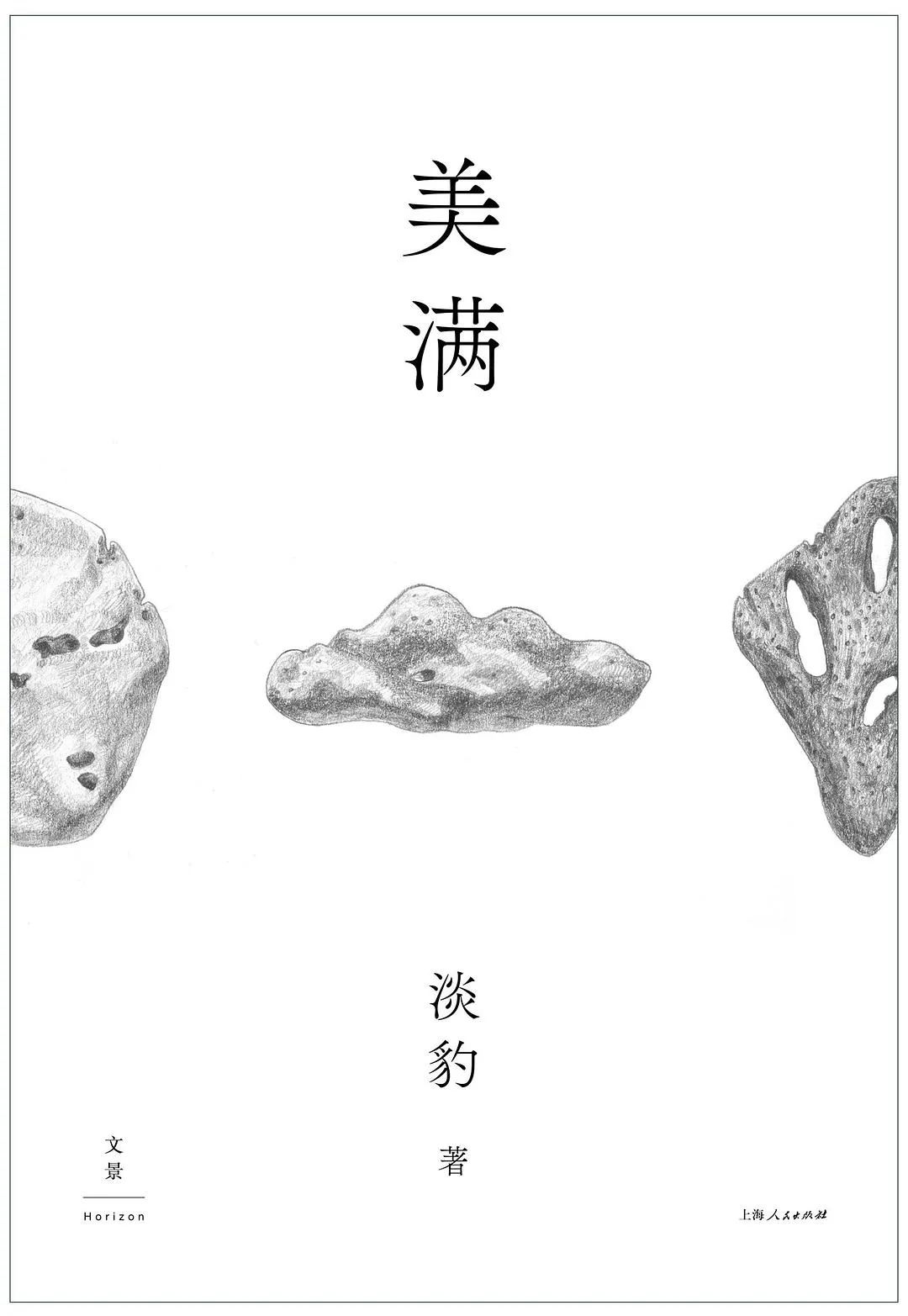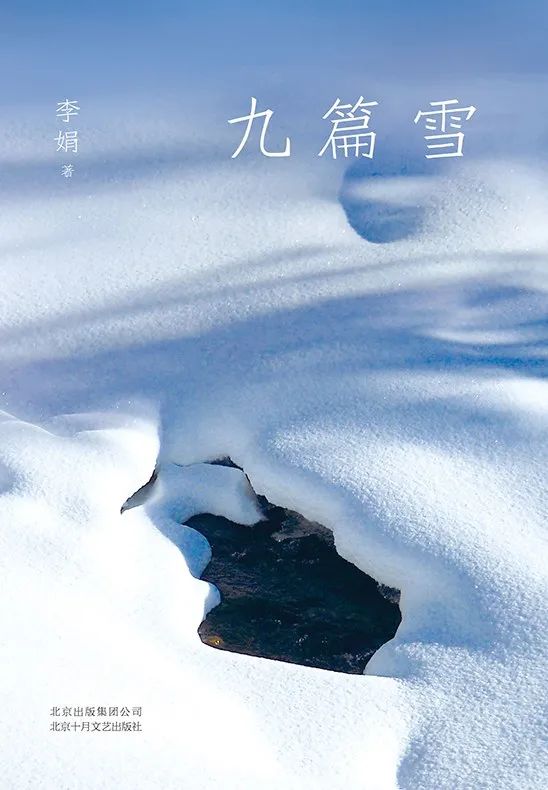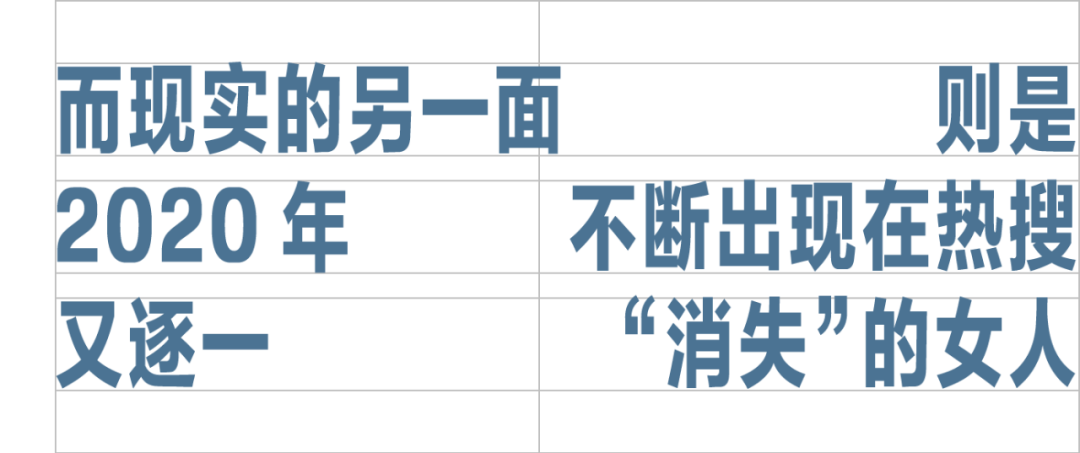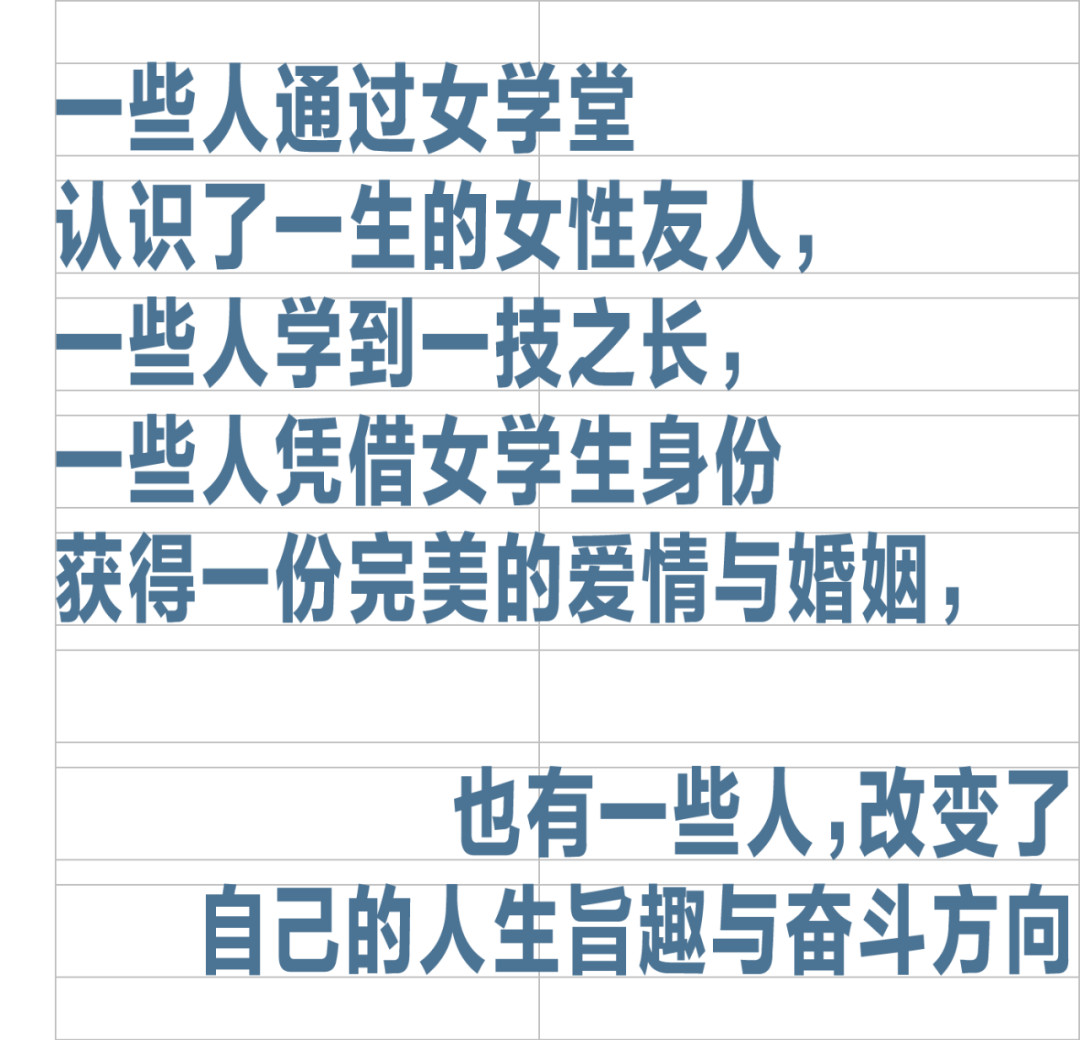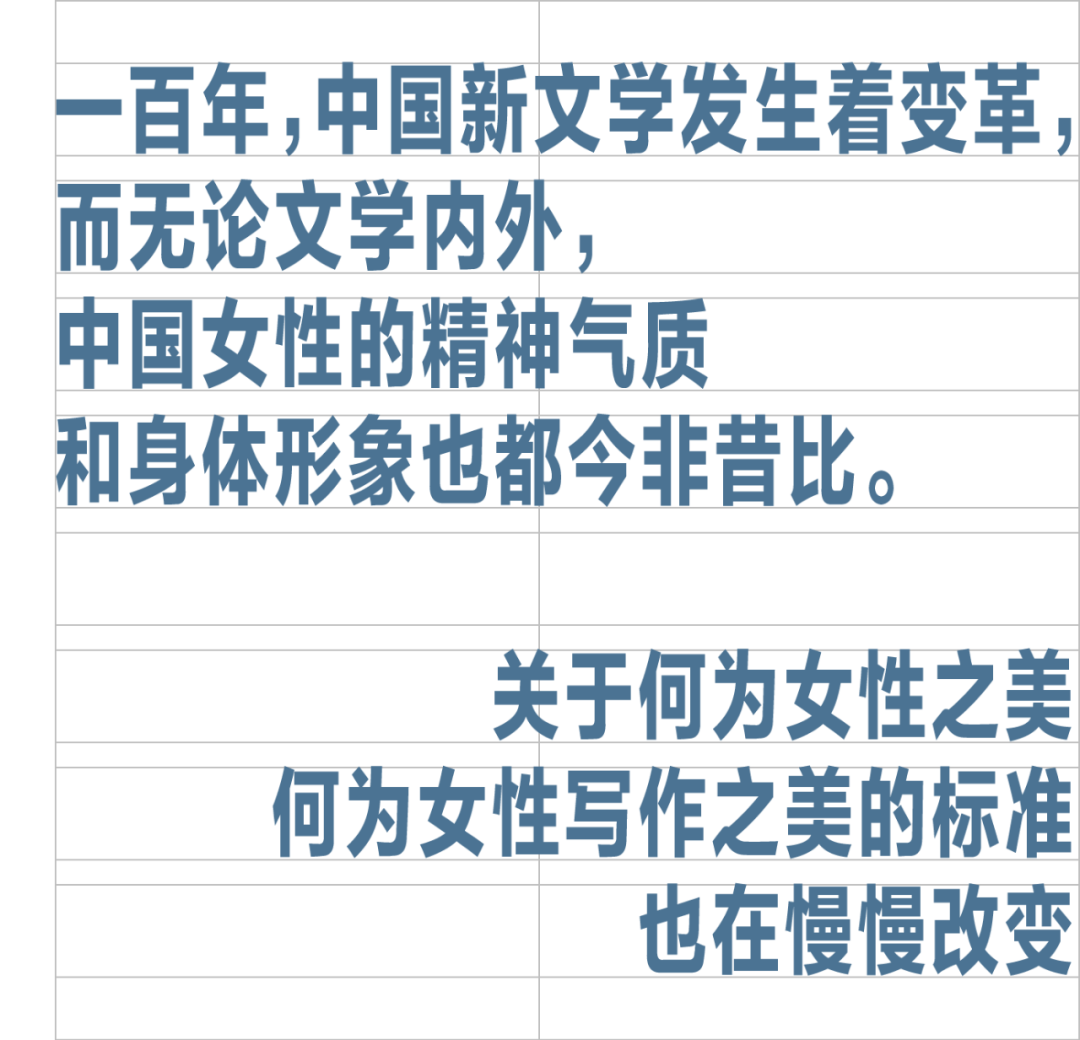怎样才能将文学的触手伸向时代深处?女作家自有回答
在这篇特别报道中,我们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以 8 位青年女性作家为引,结合她的阅读和持续推动女性写作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属于这个时代的女性写作,以及它的社会意义。但终究,我们还是要回到阅读中,才能找到答案。
谈青年女性写作者的创作,不由想到她们的前辈:张洁、铁凝、王安忆、翟永明、林白、迟子建 …… 这些作家和她们的作品 ——《方舟》《玫瑰门》《永远有多远》《弟兄们》《逐鹿中街》《女人组诗》《一个人的战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早已构成了光彩熠熠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史。当然,在这样的脉络里,不同时期的女性写作,也与「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中产写作」等标签纽结在一起。
今天,我们会说这些青年女作家能代表「女性写作」吗?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迟疑。作家会迟疑,读者会迟疑,就连一向喜欢下断语的批评家也会迟疑。因为,当我们讨论女性写作、女性文学时,不得不面对我们要谈的是哪种女性写作,是何种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等问题。某种意义上,无论从写作还是研究的维度,「女性写作」似乎都变成了「麻烦」。近十年来,它已变成一个可疑的命名,一种模棱两可的存在,就连许多女作家谈起它时,都会小心翼翼地避让。
是的,我们不会将笛安、孙频、张悦然、文珍、周嘉宁、淡豹、蔡东、郭爽、张天翼、张玲玲、杨好等人的写作归入严格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至少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女性写作」。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她们的作品里,有一种内在的关于女性生存和女性现实的思考。尽管她们的作品不复前辈作家的尖锐和愤怒了 —— 她们每一个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几乎都拿到了著名大学的硕士学位,有好几位是「文二代」;她们中有人学文学,也有人学商业、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这样多元而丰富的教育背景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女作家都不具备的 —— 事实上,她们是前辈女作家的「女儿们」,她们受益于前辈开拓的文学环境、生活环境。虽然没有人再特意指出她们作品中的女性精神,但是,却无人否认她们作品的女性色彩,尤其是那些以女性视角出发的写作、那些作为青年女性面向世界的观看和讲述。
从左至右:笛安、杨好、文珍、郭爽、张玲玲、周嘉宁、孙频、淡豹,2020 年 11 月 24 日摄于北京。
服装、配饰及鞋履均为 Dior
笛安是青年一代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人。她的长篇小说「龙城三部曲」、《告别天堂》《南方有令秧》《景恒街》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也获得了业内人士的称赞,是为数不多的既被市场青睐,又能在纯文学领域广受好评的写作者。作为陪伴一代年轻人成长的优秀作家,她的作品罕有地流淌着一种微妙情感,无论人物身处何种时代,她总能把握住人的情感悸动。这情感当然是复杂的,但她有能力写出一种清澈和迷人。《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是她发表于 2020 年第 1 期《花城》杂志的新作,有一种纤毫毕现之美,洪澄和章志童令人念念难忘。那些年轻人,那些看起来卑微却极为坚硬的生存方式,我们时代的热搜、我们时代的光鲜,都让人心中震颤。小说写得跌宕起伏,是 2020 年最优秀的短篇作品之一。那分明是我们此在的生活,有我们生存的温寒,也有我们生存的薄凉。
长篇小说《景恒街》,笛安著。
孙频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小说家,她以《松林夜宴图》《光辉岁月》《万兽之夜》《我看过草叶葳蕤》等一系列卓尔不群的中篇小说,写下了她对于历史、对于人的生存的理解,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独特思考和洞察的优秀作品。凭借这些作品,孙频足以被视为新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中篇小说《天体之诗》塑造了与我们想象中大相径庭的下岗女工形象。作为纪录片导演,「我」记下了李小雁的一生,她笨拙、沉默,渴望成为好学生、好女人,盼望好的爱情、家庭,以及命运。20 世纪 90 年代初,她从南方回到小城,成为国企工厂女工,不料两年后面临下岗。最终,与她争吵的厂长掉进了电解池,她被指认为凶手。再后来,她从世间消失。「可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相信,我是一个多么想美好的人。」小说中,李小雁竭力表达道 —— 这是酸楚的句子;这是不被生活驯服的句子;这是让李小雁的生命丰饶而有蓬勃之气的句子;这是让读者念念难忘的句子。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多么想美好的人」的挽歌,以及一个女人在最不美好的境遇下如何渴望美好。
中篇小说集《假面》,孙频著。
文珍是有极强艺术风格的小说家,2020 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出版。读文珍的作品会深切意识到她的当代性,她的笔下人物与生活有一种切肤感和亲切感。短篇小说《小铃铛的算法人生》实在是一篇生动有趣的作品,活泼地表现了我们时代青年女性的生活本身 —— 当然,也并不只是如此。文珍的作品里有一种幽微和深入,她总能以小切口切入我们时代的内部,去观照那些年轻女性的生存。而和身处北京的文珍不同,周嘉宁的写作有一种独属于上海的都市感。这种都市感不见于城市风貌而见于人物的内在腔调。《基本美》令人印象深刻,那里不仅有一代人的成长印迹,也有一个人如何与她的时代相处的秘密。
短篇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文珍著。
淡豹曾以非虚构写作闻名。当她开始进行虚构写作,她的作品中便有了其他写作者没有的、对社会问题的非凡敏感。小说集《美满》使她广受关注。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性,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权力,什么是亲情和婚姻 —— 她有她的困惑、她的思考、她的痛点。她是那种渴望将她心之所思融于笔端的作家,因此,尽管她的小说里总有一个个故事和人物,但在人与故事之外,你总会触摸到她尖锐、犀利的对于生存的理解。郭爽笔下的人物有一种「丧」,而这种「丧」又与一代青年人的生活现状密切相关。《离萧红八百米》尤其好看,作品中有两个人的生活、爱情和不一样的生存法则,但是它又莫名地拥有一种跨越时空的魅力,一如它的标题,投射了遥远的另一个时代。张玲玲和杨好是当代文学领域的新面孔,作为曾经的非虚构写作者,张玲玲的虚构作品《嫉妒》让人惊讶;而杨好的出场同样惊艳,她既是艺术史研究者,也是一位小说作者,《黑色小说》因表达方式的殊异而别有一种阅读快感。
小说集《美满》,淡豹著。
以上谈及的只是众多青年女性写作者中的几位。今天的青年女性写作者,远比我们所记录下的更庞杂。她们中有人在期刊发表作品,有人只出版长篇作品,有人则只在网络上写作。她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广,足迹也足够辽阔 ——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成都;纽约、洛杉矶、伦敦、温哥华或埃塞俄比亚 …… 她们写下我们所在的城市;写下冬天的雪,春天的雨,夏天的花朵和秋天的落叶,以及,生命中忽然到来的「木星时刻」。一些作品让人心生温柔、涟漪泛起;一些作品让人环顾四野、掩面叹息;还有一些,只是让人静默无语,想到远方以及远方的那个人。
中国地域辽阔,中国女性生存结构又是如此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要讲当代青年女作家的写作,必须提到另两位远在边地的作家。一位是李娟,她一直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陪伴母亲,以缝纫和经营小杂货店为生。许多人都喜欢她写外婆和妈妈的文章,她离开家,把兔子或小耗子留给她们,她们同这些小动物说话,就像跟她说话一样。「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怜得很 …… 你回来了就好了,我很想你。」叙述人是女儿,是外孙女,娇憨、生动又深情。「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暂时的快乐,因为这『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
李娟能将生活日常中的细微处写得甜美而温暖。书写一个非传奇性、非戏剧化、非景区化的新疆是李娟带给当代文学的新气象。这个女青年身上葆有对自然的美好情感,她和她母系血亲一样,天然地具有与土地、天空以及动物和谐相处的能力,她也依凭这样的能力使自己的写作连通了地气和人气。在李娟的文字之下,一个富有文学象征意义的阿勒泰世界正日益显露出光芒。
散文集《九篇雪》,李娟著。
还要特别提到远在宁夏西海固的作家马金莲。马金莲是回族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她在农村生活二十多年,结婚生育,与她笔下的那些女人是母女、姐妹、婆媳、妯娌关系。她讲述西海固女性热气腾腾、辛苦劳作的日常生活,也讲述她们辗转曲折的心路。借由她的作品,我们看到那些在广阔的一眼看不到边的土地上收割庄稼的回族女人们,她们收割莜麦、燕麦和高粱;秋去冬来,她们卧浆水、腌白菜;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料理一家人的三餐;还有生育、哺乳、教育孩子 …… 女人们鲜活而劳作不息的生活在这位作家笔下事无巨细地呈现,有滋有味,富有活力。当然,马金莲的作品里并不只有女人,她只是借女人的视角书写整个西部世界。她描绘固原小城的百姓,扇子湾、花儿岔等地人们的风俗世界 —— 在纸上。她画下亲人的面容,刻下他们的悲喜哀乐、烟火人生。
短篇小说集《1987 年的浆水和酸菜》,马金莲著。
今天,有许多人是不屑于谈论或阅读女性文学的,又或者,会带着一种情感或性别上的猎奇。那是偏见。对女人和女性身份的强调、对女性生活和女性写作的强调,对女作家的强调,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性别对立,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多么丰富、芜杂、辽远,它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对峙。女人的话题里固然有儿女情,有家务事,但是,话语的另一端,还连接着川泽、湖海、天地;连接着勇气、智慧、力量。女人的世界里当然有女人,但也一定还有男人和世界;有儿女情深,也一定有山高水长。
去年 3 月,我和《十月》杂志一起,向不同代际女作家发起了进行「女性写作」的邀请,希望以此推动女性写作的发展 —— 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远离表演性、控诉以及受害者思维;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它应该对两性关系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这是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 —— 它是丰富的而非单向度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的关系,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自然。
从左至右:郭爽、张玲玲、周嘉宁、笛安、文珍、杨好、淡豹、孙频。尽管这 8 位女作家不能全然代表(她们也无意代表)当代女性写作者的风貌,但她们的作品已然触及了这个时代变幻莫测的生存图景。
服装、配饰及鞋履均为 Dior
令人惊喜的是,邀约得到了作家们热情、及时而有行动力的回应,尤其是青年女作家,她们贡献了一批意味深长的作品:当孙频写下那位在深夜汾河里游泳的特立独行的迷人女性,当文珍写下青年女工林雅的灰暗人生,当淡豹写下一个单亲家庭女孩的成长轨迹,当张天翼写下那位绿皮火车上面临隐秘两难的女孩,当蔡东写下男人对“她”的不舍和眷恋 …… 从行文到立意,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清新而凛冽的气息,那是冲击,亦是惊喜。读着那些作品,我深刻认识到,一批气质卓然的女性写作之苗已经孕育,并不由想到 Virginia Woolf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莎士比亚妹妹」的期许,那已是 90 多年前了:
假如我们惯于自由地、无所畏惧地如实写下我们的想法;假如我们能够躲开共用的起居室;假如我们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从他们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去观察人 …… 我们独自前行,我们的关系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那么机会就将来临,莎士比亚的死去的诗人妹妹就将恢复她一再失去的本来面目。她将从那些湮没无闻的先行者的生命中汲取活力,像先她死去的哥哥一样,再生于世间。
某种意义上,Woolf 对「莎士比亚妹妹」的描述里,包含有对女性写作的新期许。
与前辈作家相比,当代青年女性写作者所处的文学环境和时代背景都有了非同小可的变化。灾难之际,我们看到这么多女性劳动者,感受到女性精神和女性力量,这一切超乎想象。我们从未像今天、像此刻这样真切认识到女性的确「能顶半边天」。我们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听到这么多有趣的女性之声,比如李雪琴、杨笠 —— 这就是我们切身感受的现实,是现实的一面。而现实的另一面则是 2020 年不断出现在热搜、又逐一「消失」的女人 —— 那位杭州被丈夫杀害的妻子,那位眼睁睁在镜头前倒下的拉姆,那位流泪哭泣迷恋假靳东的中年女人,还有那个被唤作「喂」的女人 …… 这些女性的声音,这些女性的命运,还没有在新一代女作家笔下切实体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的《82 年生的金智英》。这是令人遗憾的。
虽然我们看到了新女性写作的微火,但我们面临的也更加棘手:怎样才能把文学的触手伸向时代深处,捕捉、辨认、记录这个时代女性生活的改变?作为女性写作者,该如何书写我们的当下,如何刻印「拉姆们」的生存?这是新一代女作家所面对的疑难。
那是很多年前了。留学多年的学者蒋梦麟回到民初的中国,家门前的学校已经变成一所女校,他看到了新的中国女性:「大概一百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在操场上追逐嬉笑,荡秋千荡得半天高。新生一代的女性正在成长。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流行的中国歌更是声闻户外。」
如果说这是他所见的外部变化,那么大伯母则为他讲述了十多年来发生在青年男女身上的变化。在这位老年女性看来,青年男女的有些想法实在要不得,这些「要不得」包括:认为菩萨是迷信,认为应该把佛像一齐丢到河里;他们还说男女平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认为国外药丸比中药好;还认为没有鬼。在这些青年男女看来,唯一不朽的是为人民国家服务。
是的,从晚清到「五四」前的 1918 年,中国各地的许多女孩,她们的生活中开始经历识字、学堂、报纸、旅游等带来的冲击。她们的内心世界及生命轨迹,开始有了与母辈不同的,或重大或细微的改变 —— 一些人通过女学堂认识了一生的女性友人,一些人学到一技之长,一些人凭借女学生身份获得一份完美的爱情与婚姻,也有一些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旨趣与奋斗方向。当然,还有一些女性,她们借由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今日回望,那是中国新文学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开端 —— 一百年,中国新文学发生着变革,而无论文学内外,中国女性的精神气质和身体形象也都今非昔比。关于何为女性之美、何为女性写作之美的标准也在慢慢改变。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生死场》,从《倾城之恋》到《玫瑰门》、《长恨歌》;从《一个人的战争》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再到今天的青年女性写作,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中,一种柔韧、强劲、暗暗流动的力量一直驱动着我们的时代,一如一首诗中所写:
美发生着变化,像一只蜥蜴
将皮肤翻转,改变了森林;
又像一只螳螂,伏在
绿叶上,长成
一片叶子,使叶子更浓密,证明
绿比任何人所知的更深。
你手捧玫瑰的样子总好像在说
它们不仅是你的;美发生着变化,
以这样仁慈的方式,
为了别样的发现,永远希望
分离事物与事物本身,并将一切
在片刻间释放,变回奇迹。
诗句来自美国诗人 Richard Wilbur 的《美发生着变化》。我以为,它包含着一种迷人的对女性文学、女性精神的理解,也包含着一种对女性力量的认识。事实上,美一直在变化,美一直在被重新定义,被「她们」定义。我们越来越确信的是,无论是女性文本的美,还是女性身体与精神气质的美,都在发生着细微而重大的改变,如同我们从这些青年女作家身上所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