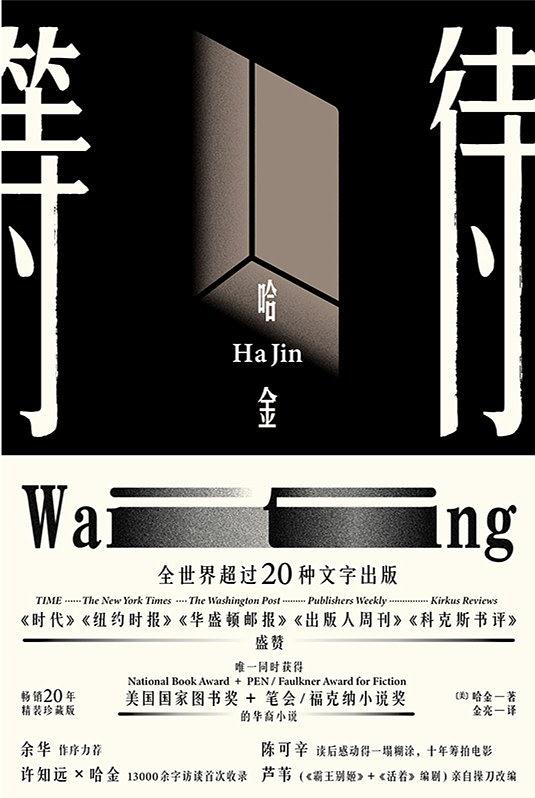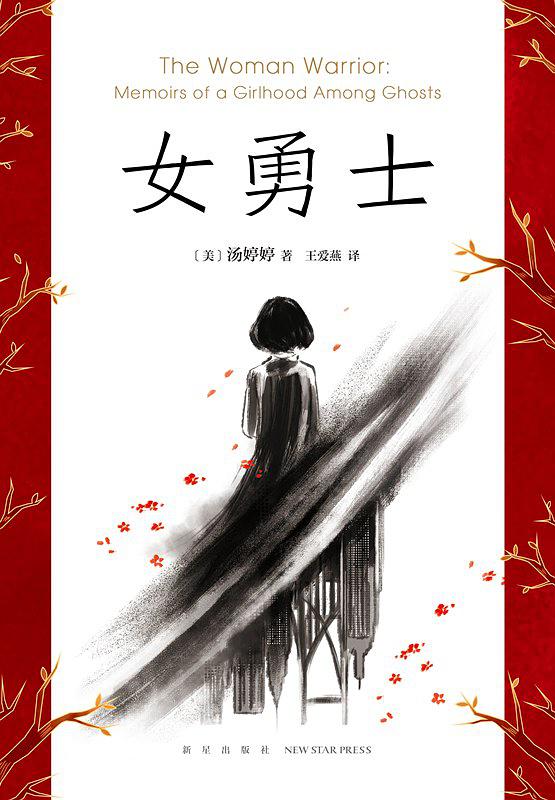许知远&哈金:创作要趁早,趁有生命力的时候
【编者按】哈金长篇小说《等待》近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磨铁·铁葫芦再版,首次收录许知远与哈金的对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哈金提议去湖边走走。梭罗的瓦尔登湖,离波士顿半小时车程。他没有智能手机,不知Google Map,翻开庞大的印刷地图,确认2号路的转弯处。
瓦尔登湖比我想象的小得多,只要努力,我似乎也可以游一个单程。梭罗的小屋遗迹犹在,你可以辨清火炉、床与书桌的位置。
“我独自生活,在林中,离任何一个邻居都有一英里。 ”遗迹的铭牌上引用了《瓦尔登湖》中的一句。
我从未对梭罗的隐居岁月产生过特别的兴趣。相较而言,新英格兰的文人中最吸引我的是爱默生。比起梭罗遁世式的反抗,我更钟情爱默生式的呼喊。他要唤醒仍在沉睡的美国精神,把它从对欧洲的精神依赖中解放出来。年轻时,我也曾希望扮演类似的角色,颇用心地读了他的那些雄辩滔滔的散文,着迷于其中神性与人性混合的崇高感。
我没对哈金说出这些。面对他,我总处于一种放松与紧张并存的情绪中。放松源于他宽和的性格、缓慢的语速、英语发音中仍然浓重的中国口音,当然还有他东北孩童式的笑声。紧张则是对自己深切的不自信,我担心自己无法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同行对待,更重要的是,不能就他最钟情的诗歌展开交流。忘记是在哪里读到的,他说唯诗歌、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评论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常是迫不得已之作。我偏爱的却是后一种。
2008年夏天,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他。我们都是书展的演讲者,有几次共进晚餐的机会,我记得他罕见的谦逊,还有清晰的立场.,他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
我读过他的《等待》,完全被他洗练的语言与文字间的情绪所折服,那种政治严寒之中的个人世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充分又富有节制地表现过这样的中国。考虑他三十多岁后才开始用英文写作,这成就更显惊人。我也记得他说起《等待》的书稿,修改了四十遍。那年的香港书展,除去一贯的炎热气氛,我也模糊地意识到一种新时代情绪的来临。
接下来几年,我再没有见到他。但仍陆续读到他的长篇、短篇集,它们不再让我有初遇《等待》时的惊喜,却保持了一贯水准。对我而言,英文原作总比中文版更有吸引力,不知这是缘于语言的陌生感,还是我恰好能在他的英文中找到节奏感。在一段时间里,这种节奏感是我的镇定剂,每当我觉得内心烦躁时,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他的书,读上几段。他的作品像是个诚实、镇定又疏离的老朋友,陪你不急不慌聊上几句。偶尔,这也激起你不恰当的雄心,你也可以这样写。他的英文写作,似乎充满了你熟悉的中国味道,而且没什么生词。
康拉德的英文怎样?纳博科夫的节奏又是如何?哈金常被归入这个行列,他们都来自另一个语言系统,最终以英文小说闻名,为英语书写增添了元素。
我们绕湖一周。梭罗时代的孤独感早已消失,情侣们在水中接吻,少妇在沙滩上读书,旁边有儿童在奔跑。哈金头戴Red Sox的棒球帽(我忘记问他,是否也是棒球迷),穿蓝色竖条衬衫,用一把大伞做手杖。“余华压根不愿意迈步子,阎连科倒是走满了一圈”,他喜欢带朋友到此地,也是尽地主之谊。自1985年来布兰迪斯大学读书以来,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三十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波士顿。他曾以为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回国做一个英美文学的教授,业余还可以做翻译。后来他不仅留在美国,还准备进行一场“鲁莽”的试验,不仅移入一个新的社会、自然环境,还要移入它的语言深处。他竟成功了。他常觉得自己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缘,但此刻,他为两种文化都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在湖畔,我们的谈话跳跃,他说起村上春树语言中的音乐感;说起布罗茨基,他承认这个俄国流亡者的散文很了不起,却不太看得起他的英文诗歌中刻意的押韵,也觉得他过分轻浮,把与一个希腊女人的床笫之欢也写入文字中,我略显迟疑,为什么不能写?还有宇文所安天才的唐诗研究,他自己也正着手一本李白的英文传记,他最初的文学兴趣正是来自黑龙江小镇上读到的唐诗。
我们也说起了林语堂。哈金不仅属于康拉德、纳博科夫的传统;也属于容闳、林语堂的传统,他们都是中国人的英文写作者,尤其是后者,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风靡一时。如果放在更大的一个范围,还有谭恩美、汤婷婷等,他们都是中国经验的书写者。他们的题材与风格也象征了中国的变化。林语堂描述的是一个深陷民族危机,却有强烈文化魅力的中国,谭恩美们描述的是那些广东移民神秘的、风俗式的东方经验,而哈金的书写主要集中于国家意志与个人选择间的紧张关系。
“林语堂能量大”,他说起后者浩如烟海的写作,他在中美间的外交作用,他编纂的英汉词典、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还有刚刚发现的《红楼梦》的英译稿。在中国,林语堂常被弱化成一个幽默散文作家,或许还不是最好的那一类。
“在中国,人们讲究才华,在这里,能量(energy)才是关键”,哈金说起他初来美国时教授的话。比起写出漂亮的句子、段落,那种持续性喷涌的创造力才是关键。
许知远:我们先从对中国的记忆开始谈吧,您离开中国应该已经整整三十年,对山东、东北这些个人化的记忆现在还浮现得多吗?
哈金:很多啊,特别是东北,我小的时候基本在东北长大,北方那种风土习惯,还有地域、景观、街道,还是经常想起来。做梦也经常回去。比如说有一个叫亮甲店的小镇,我在那儿长了十三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回去过一趟,发现那个镇子怎么变得那么小,几步就走到头,但小时候就觉得很大,空间感觉不一样。最近我弟弟又回去了,说那里都变了。
有时候记忆也是模糊的,或者说记忆它本身也在被创造,有些东西一不留神就出来了。我知道我是在金州出生的,但那个房子肯定早早就没了,但我记忆中好像还有个房子在那里,好像就在公安局对面吧,因为我妈在公安局工作过一段时间。
许知远: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对乡愁(nostalgia)的质疑,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哈金:从理性来讲,我们汉语所说的乡愁里面的“乡”已经不在那儿了,就算回去也不在那儿了,你也不属于那儿。人变了,乡土也变了,什么都变了,你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里,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说到我们的感情,是我们自己在变,逝去的青春和年华已经不可挽回,从内心出来一种依附感,但没有实际的参照,只是自己的一种情感而已。
许知远:过去二十年您主要靠英文写作,近几年又开始用中文翻译自己的小说。您的写作跟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
哈金:我自己一直说汉语是我的第一语言,也是我的母语,语言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已经29岁了,英语说shaped,已经塑造成形,很多情况并不是我们自己想不想,而是实际的问题。比如说,我主要翻译的是短篇,就是因为有的杂志需要短篇,但短篇翻译根本就不赚钱,不像长篇字数多,没有人愿意做,所以短篇小说最好自己翻译。我最近用汉语写诗,不是说我一定要回到汉语,而是我觉得从这儿起步,基础比较稳一些。我还可以重新用英语写,让这些诗在英语里出现,会比较新鲜。
所以实际上都是从具体的小事考虑,不得不这么做。
许知远:那二十年英语写作的经验怎样塑造了您的思维和理解方式?
哈金:就是比较理性,想问题不能含糊,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有根据,而且每句话当中一定要有内容,有信息。不像汉语,往往有的时候你的辞藻有文采,就略过去了,但英语得讲究,好的文章就是每一句都增加分量,增加内容,这一点很重要。
许知远:这两种语言最重要的区别在哪儿?
哈金:英语特别讲究。它甚至和别的语言也不一样,是一种比较硬朗的语言,就是要承载内容的语言。比如用意大利语写歌剧很容易,开元音讲究情感,而英语没有这些东西。
许知远:诺曼·马内阿也说过这个问题,他刚来纽约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语言。把他的作品从罗马尼亚语翻译到英语,很清晰,但罗马尼亚语里那种模糊的、暧昧的东西都消失了。
哈金:是。汉语里有些东西如果用英语翻译过来,你就会觉得很蠢。比方说万箭穿心,心本来就这么大,怎么能承受住一万支箭呢?要想翻译这个词,你只能说十几把锥子扎心。英语如果不讲究理性,别人会觉得你胡说。
许知远:也有人把您和康拉德、纳博科夫放到这个传统里来看,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英语写作?
哈金:他俩不一样。康拉德基本不怎么会说英语,他写作的英语因此也特别书面,但因为他懂好几种语言,包括波兰语、法语,所以他的英语同时也非常强壮、优美。纳博科夫因为康拉德语言的这种书面性而有些看不起他,觉得这完全是礼物商店里的东西。他与康拉德不一样,纳博科夫最大的优点是幽默和俏皮,他能玩。其实他也是书面英语,但俄国人喜欢双关语,纳博科夫用很多双关语,在英语中本来都是不让用的。一开始他的朋友艾蒙·威尔森(Emon Wilson)就说,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这种杂志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作。但他继续做,做着做着就成了他的风格,他打破了一个传统上禁止的界限,他也因此成为他们那批人中的一个高峰。
许知远:刚开始写作时,怎么发现自己独特的腔调?
哈金:其实我并不是很注重这个英语里边叫voice(腔调)的东西。但因为我写诗,我知道我不能写标准的英语,我和美国人没法比,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是不行的,我只能写跟别人不一样的,因此我主要是从诗歌这方面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许知远:为什么说对腔调没这么注意?
哈金:因为这个东西是会随着你写不同的东西变化的。很多诗人也不承认,比如我的导师弗兰克·比达特,觉得那根本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我想他们的逻辑在于,写作的腔调是随时变化的,随着不同场景、人物,那个声音随时需要修正。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注重,但我要写的英语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一开始就很清楚。
许知远:那您怎么评价自己的英语的风格?
哈金: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的情况不一样。纳博科夫是在剑桥读本科,而且是贵族,再加上英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一开始他奶妈用的就是英语,而我是半路出家,二十几岁前没见过说英语的人。我觉得对于英语写作来说,最难的是你怎么用英语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写得好。现在我希望能写出一种语言,让别人一看就觉得是外国人写的,但还是觉得非常自然非常好。当然这是我自己想象的一种英语,能不能做到还不清楚。当我写非虚构类作品的时候,比如《在他乡写作》,就不需要我刚刚提到的这种英语,只需要直接用标准的英语写出来就好,这并不难,难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写作。
纳博科夫和康拉德他们其实留出了很多空间,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别人写这么好,达到高峰了,你不可能又跟上去,这样可能就是死路一条。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模仿什么魔幻现实主义,这条路人家已经走到极致了,你再去走,你能走到哪儿去。像纳博科夫、康拉德,他们在中长篇上做得最好,但都不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在诗歌上也都没达到很高的成就。
《洛丽塔》
许知远:对您来说,诗歌、长篇和短篇小说,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哈金:长篇小说需要长时间来做,好几年才能完成一部。这个我也能做,但我还有工作,而且最近几年我太太病了,我自己不能完全沉浸在一个长篇里头。因此,对短篇比较适应,只能说做一点是一点吧。好在诗歌我还是在写,一直在写,用汉语写完之后再用英语写。不过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做出来。
许知远:从最初的《词海》到最近的《背叛指南》,最近二十年您的英文写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哈金:其实也没太大变化。可能最大的变化是难度,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你知道的多了,标准也不一样了。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读书读多了,你就能做好。我们都是人,人在不断地走向死亡,不可能还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那种能量。我们知道的很多,但我们的创造力却没有那么旺盛了。
许知远: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吗?
哈金:不管强不强烈,这种感觉肯定会有的。汉语里说一个人有才华和英语当中说有才华其实是两个概念,美国人和英国人说一个人有才华往往是指一个人的能量,特别是作家、艺术家。有能量以后能创造很多东西,并不是哪个句子写得好这种局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的整体被视作是有能量,能够不断地创造。能量和天才被视为一个东西。而我们汉语里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种情况,所谓读书多了就下笔如有神,确实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生命中的某一个点,如果一个人病得要死的时候,是不可能下笔如有神的。英语语境里所说的才华,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能量,不可能越来越多,只能越来越少。而问题也就在这儿:你知道得多,学得多,技艺也高了,但不一定能做好。这便是我为什么说写作、创作要趁早,趁你有生命力的时候来做。
许知远:除了康拉德、纳博科夫那个传统,另一个传统是中国人英语写作的传统。您怎么看这个传统中的人,比如林语堂?
哈金:林语堂是中国人,但也不能说他是中文概念中的才子,他不同于鲁迅,他是一个高产的人,写了几十部作品。这是需要能量去支持的,因此他是属于西方语境中比较有才华的人。最近刚发现他的一个手稿,是他用英语翻译的整部《红楼梦》。你就能看出他的能量。能量大,学问也大,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很快拿到了本科学位,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一年半又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确是个超人。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传统文人,讲究幽默.,讲究情致。像我这一代,你父亲那一代,是从地上长上来的,林语堂也是农家子弟,但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出国以前他在中国就一直是畅销书作家,是教授了,而且他第一本书是在美国卖的,是国际畅销书。不像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学、高中,这几年大部分都是乱七八糟的,我和莫言、严歌苓这些人实际上都没上过中学。林语堂他们这一代有英语情结,有可能我们下一代也是,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就学英语。
许知远:您怎么看林语堂的写作本身呢?
哈金:他是一个能脚跨中西文化并把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大家,特别在散文方面。不过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最成功的小说是《京华烟云》,但可以看出不管是结构还是一些细节,都是从《红楼梦》借过来的。不过他所写的《生活的艺术》,以及另外几部,确实是优秀的作品。
许知远:1949年以后的另一批人,谭恩美(Amy Tan)、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这些作家,您如何评价?
哈金:他们这个系统的人基本不懂汉语,可能谭恩美会说一些,但读写都不行,是标准的在美国长大的ABC。你不能说他们是华语作家,只能说是华人美国作家。谭恩美是很优秀的作家,这些年来也有好多本畅销书。而汤婷婷比较独特,应该说她是美国学校里教得最多的作家,学校把她的那本《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作为课本来讲。我也教过,但就我的感觉而言,学生不是特别喜欢,以后我就不教了。她有点类似美国亚裔文学上的开山鼻祖,不管写得好坏,她在文学史特别是在美国文学史上,都是有位置的。
《女勇士》
许知远:可以说他们的共性是都在美国写中国经验吗?林语堂时代是一种浪漫化的中国印象,到了谭恩美,就是神秘化的、东方主义式的中国。您怎么看这种中国经验的变化?
哈金:首先有一点,他们是把中国拿到美国的系统中去写的,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华人文化当中长大的。汤婷婷就非常明显,她把中国的神话完全弄过来了,那是他们祖辈的经验,也是一种神秘的神话。整个亚美文学当中都有这个问题,总是试图去寻找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往往追溯到中国或者日本,这种现象都是正常的。
而像我们这些作家不一样,我们来美国之前就只知道中国,特别刚开始,除了中国以外其他根本一无所知。即便慢慢知道多了,你对世界的看法、感觉和印象还是由那些中国知识来包容和影响的。但这不是坏事,你要是都按美国的来,那和别人就没有区别了。你在另一种语言当中,或者你在两种语言之间,可以站在一旁来观察,比较理性客观。
许知远: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和您所写的中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哈金:他们不懂汉语,虽然他们家庭中还是有很多中国成分,但家庭传统已经美国化了。你不可能让他纯粹、真实地写中国,而且其实真实本身也是个问题,什么是真实?哪个中国才是中国?问题其实就是看作家本身了。你生活的经历不一样,自己感觉不一样,写出的东西就不一样。这是没有办法要求别人的。
一方面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可能确实和中国现实经验没有多大关系,但有的时候,从广义上说,也可以说这样很好。这便是我一直强调的“真实的印象”(the impression of authenticity),就是说那种真实的感觉本身便是虚构的,是创造的,我们事实上没有真实的尺度。比如《落地》里讲的故事是美国经验,但美国人不相信的。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个女孩对一个和尚特别好,但他跳楼了。他们说你这是多愁善感,这不可能,你故意把故事甜蜜化了。但生活中确实有这个女孩,就是她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让媒体注意到这个和尚是受剥削的人。这件事确实发生了。有时候真实的东西往往你还不能直接照用,你还要想一想究竟如何处理。
我很早写过一个故事,原型是我们当兵时候一个很有名的翻译,他父亲是张作霖手下一个高级军官,奶妈是俄国人。他是俄文翻译,跟着代表团去苏联谈判,结果病了,但他坚决不吃苏联方面给他的药,说那是敌人的东西。他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人,但坚决不吃。他们只好把他往回运,在路上山洪把桥给冲走了,耽误了时间,人就死了。这是真人真事。我写小说的时候,写成是苏联方面给他动手术他不接受,即便这样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傻瓜,都不相信是真的。其实我还故意把真事压低了,真实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
许知远:您的哪本小说离您的经验最远?
哈金:应该是《背叛指南》。这个事情几乎没有我的经历,可能感情上有些自己的投入,但是整个细节完全是创造的。而别的作品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甚至《战废品》,毕竟我在朝鲜那边待过,那边的人怎么说话、风俗习惯我都是知道的。
许知远:那写作的过程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哈金:其实这个故事在心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写这本书,我夫人也说这是个好题材。关键在于我怎么写这个问题,我得有方法,最后就写了两个故事,一个现在,一个过去,找到角度把它们结合到一起。很多东西都是偶然的,比如《热与尘》(Heat and Dust),我在那本书里学了很多。我教那本书的时候,学生就说,这两个故事经常分家,因为主人公并没有和上一个主要人物有血缘联系,这便是那本书的弱点,所以我知道我得把这一点克服。还有一些国内的因素,比如《潜伏》,我太太看那个电视剧看到最后特别生气,结局余则成就和另一个女的结婚了,从此和那个在乡下怀孕的老婆没关系,她特别不喜欢这个结局。我就把那个作为起点开始写。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偶然的,最后融合到一块儿去了。
许知远:处理陌生的和熟悉的经验,感受上有非常大的区别吗?
哈金:你说的这点相当重要。陌生的经验往往造成隔阂,你并不会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是必须注意那种探索,因此细节必须做好。其实到了纸上,什么都是想象,哪怕是直接的经验,你处理不好,体验生活也是没有用的。纸上是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必须要掌握好。
许知远:在《自由生活》《落地》里面,您开始处理美国移民的经验,而之前写的大部分是中国经验,我特别好奇,这种转换是怎么发生的?
哈金:其实《自由生活》那本书我从读研究生开始就想做了,但那时刚出中国什么都不知道,光知道有那么一些事情。要通过活在这儿很多年后,慢慢写了好多本书以后才敢写,因此这种转变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自然的。这种转变还跟教学有关系。教学就是一天到晚都和学生在一起,长期下来就成为你的一部分,轮到自己写的时候,就不觉得这是一个大坎儿。《南京安魂曲》那本书确实是一个大坎儿.,实在太远了,全是靠材料做的。
许知远:那您怎么评价《南京安魂曲》?
哈金:那本书实在太难写了。文学作品很难写好,你从正面来写,就容易成为一种宣传;从侧面写,比如从我选的那个角度,这个人的很多事情没有太多戏剧性,你又不能创造。那真是个坎儿,写完之后心里就放下了,但国内作家也都知道,这种硬题材不好碰,我只能说我尽最大努力了。有人说,英语写作事实上就是写作技巧。这确实需要技巧,我写个句子,结构是怎样,每一个细节的选择,细到什么程度,细节跟别的地方怎么联系,怎么转折,这些很多很小的东西,实际上是很难做的。
《南京安魂曲》
许知远:您写一本书要修改过很多次,在修改中有没有一个中心原则或者说尺度?
哈金:因书而异吧,《南京安魂曲》那本书我就挺强调感情的流动,虽然表面上安静,但又是流动的。这很难做,但最后我觉得差不多还是做到了,特别是最后创造了一个叙述人。
其实还有一个原则,在改的过程当中,不光要把文字做好,还有许多细节,有的句子底层的意思一开始是意识不到的,在改的过程当中才会意识到它们的联系,哪里需要做多或减少.、阐释的过程。
许知远:到美国三十年,您对美国经验怎么看?
哈金:我觉得美国是一个优秀的国家,它最大的不同是空间大,美国自然资源丰富,自然而然给人创造很多机会,很多人都能够找到他的位置,社会空间也大。我觉得这是美国跟别的地方最大的不同,也是一个最大的优越性。美国前几年还闹油荒,不久过后发明一个新的采油技术,现在便石油过剩了。在这方面美国不得不说是得天独厚的。
许知远:在美国写作时,一方面是发现崭新的美国经验,一方面是重新发现自己的中国经验。这应该是一个双重的过程吧?
哈金:对。经验往往是没意识到,或者说把它意识化了,就像我说的,它是一个阐释的过程。以前有些东西不觉得很有意思或有意义,重新来看,它就更有价值。
许知远: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中国经验,您之前没有想到,但事实上是非常特别的?
哈金:有好多。比如说,美国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工具,甚至吃饭也是,而中国文化里一双筷子就足够了。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里面很多东西一抹就过,但西方很细,一个萝卜一个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上升到别的层次,西方人特别讲究职业性,不管有什么事他们都害怕,一定要找职业的人来做。中国人不一样,一个个都是万金油,病了以后喝点什么姜汤,这种事美国人是不敢的。
当然还有别的,总的来说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所理解的苦难、贫穷不一样。我有学生在美国,说在这儿有管理房子的人会给他打电话,说他家里的池子不行,得换,但他其实觉得挺好的。他们的贫穷概念和我们的确实不一样,很多所谓的穷人其实生活得也很好,成为中产阶级是真难。
许知远:您为什么这么强调苦难和苦难经验?
哈金:苦难本身不重要,但对苦难的体验和感觉是重要的。为什么中国传统上会送很多人去体验生活,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真的体验,因为心灵不在那儿,感受不了,这种体验就是无效的。但有些作家,特别在英美,他实际上足不出户,他照样能写,比如福克纳。实际上不光是经验的问题,关键在于他心灵特别敏感。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许知远:您夫人生病以来,会给您带来一些关于生命的新看法吗?
哈金:其实我们一开始结婚感情不是很深,我们也是别人介绍的,而且不在一块儿。特别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她觉得很陌生,但慢慢在一块儿,有什么事儿都在商量,还一块儿出去干活,慢慢地互相依赖。在美国没有别人,就是靠自己,自己这个小家,慢慢就好像是互相依存的一部分了。从她病了以后,因为当时病得很重,说只能活两个月,我经常提醒自己,千万别做将来悔恨的事情。我每天都在对付死亡这件事情,因为不管怎样,你都得面对,这样反而我脑袋一清醒,就好多了。这也便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把这个空间作为自己的天地,就行了。
许知远:当年的东欧作家移民到美国,他们似乎有一个更直接的传统可以接上去。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移民者接在了唐人街的传统,但似乎中国传统里面的异端——流亡(exile)文学的传统好像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哈金:流亡文学只能在国内找到。像屈原、杜甫你都可以说是流亡,但在中国外面就不行了。而反过来,像马内阿他们的传统是犹太人的传统,犹太民族是流亡的民族,所以他们的文化根基就在于流亡,最早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化知识的传统,所以很容易和西方文化接轨。他们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中心。而对于中国、日本,整个亚洲除了印度以外都难,但印度也不存在流亡的作家,他们主要的作家其实都生活在国外,他们的环境跟中国不一样。
许知远:那您怎么看待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作家?
哈金:印度有好多种语言、好多种文学,但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所以用英语写的好作品就成了官方文学。当然也有作家在西方长大,虽然写印度的事情,但他们并不是写印度经验,所以印度人并不接受。这类作家就在两种文化之间来去自由,而且他们也确实在两个国家之间生活。像我有个学生,他就是在德国用德语和英语写作。他每年在印度住半年,在柏林住半年,像这种生活的状态,就不存在流亡了,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一种经验。
许知远:过去二十年有种说法是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您可能也算其中的一部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哈金:我并不是很认可这个说法。我现在觉得,某段时间有一个新的概念,另一段时间又有另外的概念。我觉得最终还是看作家在一个语言当中的位置,看他能给这个语言带来什么。比如你看纳博科夫,他也是没有和俄语切断,一直到最后都还在翻译普希金、奥涅根。所以,我不相信全球文学,我认为一个作家最终还是靠语言来决定的。但作品可不可以超越语言呢?小说偶尔有可能,但诗歌是比较难的。一部特别优秀的小说像《1984》,翻译成哪种语言都可以,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经验。
许知远:在情感上您觉得自己跟哪个英语作家更亲近?
哈金:我只能按书来。很长时间里奈保尔对我影响很大,但你知道这个人在政治上很保守,他是种族主义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确实很糟,但他是个伟大的作家。还有纳博科夫也对我影响很大,不光是文学,这些作家怎么生活,也很重要。
许知远:我也很喜欢奈保尔的小说,他的非虚构作品写得特别好,我觉得他观察的角度是从个人的身份危机出发的。那您的立脚点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核心?
哈金: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就是在纸上生存,这就是我的立足点。很多问题没必要去弄复杂,你在做一本书,能够争取花大量时间把它做好,这是最主要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你想做这个做那个,往往太分散了,最后什么也做不成。你说的那种身份挣扎对我来说感觉不强。关键还是在于能做一件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许知远:那对您来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哈金:倒也不是要求什么实际的结果,可能就是在已经有这么多别人的著作过后,你是不是还能再加上一点东西吧。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写作要看文学史的作品——放在那之后,你在这个系统当中仍然幻想要去做得最好的话,你需要思考会有什么结果。
许知远: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您给英语世界加了什么东西?
哈金:我不知道。我有一些短篇小说被放在了美国的课本上,还有几首诗也不断地出现,可能带来了一种声音,但这种声音有多大的价值现在我还不好说。但我慢慢地做下去,有些东西不是你要做就能做的,你想到的事情往往真正到时候都做不了。很多东西都是偶然的,但有的时候你要有一种幻觉,如果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会很有意义。幻觉其实是真正的驱动力。尼采说,the duration of great sentiment that makes a great man,就是说你让这种幻觉不断地延长,最后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许知远:当幻觉开始减少的时候,您怎么办,去读文学史吗?
哈金:其实也不是读文学史,就是读书,也不光是读书,慢慢你就知道了一些关系,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到最后可能什么都做不成,但你仍然应该这么做。你想象天上到处都是星星,在星星当中你能在哪一个位置,虽然这就是一种很狂妄的想法,但有时候不得不这样想。
许知远:中文写作传统中哪些特别显著的特征对您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哈金:其实我用汉语写诗,有些时候一些句子词语自然而然就会有英语中所说的echo(回声)。还有一种影响,就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中国诗歌,我们一开始的教育没有别的东西,当时家里给我们当兵的寄了几本课本,课本里有些古诗,开始就是记住那些诗,这自然而然塑造了你对世界的感受,这是你想改也改不了的。写出一个句子来觉得好,其实你说好的背后,可能是李白、杜甫这些人在影响你,也就是感受、判断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虽然你不一定意识到。
许知远:现代汉语传统中有对您影响大的吗?
哈金:一开始鲁迅影响很大,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只有鲁迅,没有别人。所以你不管喜不喜欢鲁迅,都吃他的奶长大的。但慢慢地就少了。
许知远:那现在您对鲁迅是什么态度?
哈金:我觉得他很有思想,而且杂文写得很好,他的小说里有一种洞见。《狂人日记》里,中国社会就是吃人,历史都是吃人。但问题就是,他真正写小说就写了两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太短了。他没有继续做下去,因此他并不是优秀的艺术家。不像林语堂一辈子不断地写,鲁迅有点把自己的才华挥霍掉了,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可悲的。像《野草》那样的作品,鲁迅写得太少了,像散文诗似的,就那么一本。
另外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他太强调功能了,能够给中国人的灵魂治病,但事实上中国人没有什么变化。文学根本没有那么多功能。所以说其实就是他错了,也使后面很多人跟着写错了。
许知远:您在文论里比较林语堂和索尔仁尼琴,您觉得他们有高下之分吗?
哈金:他们俩完全是两种人,也不能说谁好谁坏。林语堂那种人不入美国籍,他一定要回中国,所以他后来就到新加坡,最后是国民党退到台湾了,在台湾给他盖的房子。在这意义上,他完全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并且他很会生活,还特别喜欢法国南部。索尔仁尼琴就不同,他在乡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五百亩地里就他家自己盖了个帐子围起来,还跟苏联一样。最后回去他是一句英语也不说的,还是一口俄语,里里外外完全还是苏联人,而按现在的说法,林语堂是标准的世界公民。
许知远:林语堂、钱穆当时曾发过一个声明,一个文化中国始终存在。对您这一代来说,这种“文化中国”是不是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
哈金:对,而且我们没有这种印象,我们甚至都不是文化人,跟他们上一代两代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中国出来,但并不是文化人,只有革命文化。上一代人比如余英时等,他们都是学富五车,哪里像我们,我到哪儿去找图书馆,我们还是从底层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作家,他们对林语堂非常反感,因为林语堂代表的是一种士大夫的传统。而这些作家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工人、劳动者,我们出来就是给人干活的,对他们来说林语堂就很隔阂。
许知远:这种无根感是怎样塑造您的思维和写作方式的?
哈金:其实有没有根我觉得无所谓,关键是习惯了。当然也因为我父亲是部队的,所以从小跟着家里到处走,也不能说哪里就是家乡,至少我没有这个概念。现代人往往就很容易想象一个小镇,或者在海边,或者随便哪个你觉得安全悠闲的地方,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想象而已。这种想象谁都会有的,但你要理性,其实那根本不现实。你只能说在你的纸上,在你自己的工作,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投入,那就是你的生命。
许知远:那您怎么看李翊云,她算年轻一代吧?
哈金:对,她是年轻一代很好的短篇小说家,长篇我觉得她还没写到,可能还年轻。她好像对爱尔兰那些作家比较亲近,所以就跟大陆作家又不一样,跟美国作家也不一样,跟整个华语作家都不一样,比较独特。
许知远:成功对于您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1999年您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那相当于是个分水岭。
哈金:思维方式倒不影响,但压力很大,别人给你的期待不一样,坎儿就不一样了。坎儿就是你往上爬,明明跳不过去,但还要跳,并且这个坎儿一定是往上升的,因为标准不一样了,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
许知远: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和文学无法分家,西方也一样。当您写作时,会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考量吗?
哈金:不很多。但有些作品,特别在修改的过程当中,你看得出会有政治意义,但你不能回避。你只能考虑在这个处境当中怎么把这个作品做得最生动。
许知远:在这方面其实一直是有争论的,一派认为政治和艺术、文学完全无法分开,另一种就是认为政治会伤害艺术本身。您怎么看待这种争论?
哈金:其实那种说法说到极致,便是乔治·奥威尔说的,任何艺术都是宣传。我承认西方所说的,诗歌语言是一种政治语言。你用英语写作,而这又是一种强大的语言,这是没办法的。但我觉得不管是纯政治还是纯艺术,都很难做到。就像T. S.艾略特说的, only through times,time conquered,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能被征服。你把这个话语引申,只有通过历史,通过现实,通过社会,你才能征服这些我们眼下的东西。政治的东西你不能回避,但你可以通过政治把政治给征服,要超越它。
许知远:您觉得未来的中国离散文学,会变成重要的一支力量吗?
哈金:肯定会变成一支,但多重要就不一定,要看个人。如果能真正出来一个两个天才,那自然而然这个流派就成主要的了。关键就看有没有真正的天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