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高考机会都很难获得的孩子,他们的“门”在哪里?
2018年06月06日 11:08:58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婷
马上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年高考,我们总会再次反思高考制度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有没有改进的办法;与此同时,却也有不少孩子,仅仅为了能够获得高考的机会,便要经历漫长的坎坷与挣扎。
马上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年高考,我们总会再次反思高考制度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有没有改进的办法;与此同时,却也有不少孩子,仅仅为了能够获得高考的机会,便要经历漫长的坎坷与挣扎。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背后是流动人口的日益增长。简单来讲,“流动儿童”一般离开了原户籍地,跟随务工就业父母迁徙;“留守儿童”留在原户籍地,但长期与父母分离。近几年,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受流动影响的儿童”,其中包含了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可以用来更为确切地描述流动人口影响下的儿童教育问题。

图为2000-2015年间,流动及留守儿童的构成。从中可观察到“受流动影响的儿童”,2015年较2010年出现了下降,但1.03亿仍然是个庞大的规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尽管公共政策层面已为此出台了很多保障,但非京籍儿童的教育,仍然面临种种困境。最典型的,便是高考难。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约80%的流动儿童会选择父母务工所在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其余的孩子,则会选择各类民办打工子弟小学或民间教育机构。
我们最近探访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家民间教育机构“科蚪实务学堂”。由于学力落后、未及时申请学籍,“科蚪实务学堂”的孩子们很多难以获得高考机会,陷入“难归难留”的困境。这样一群连高考机会都很难获得的孩子,他们的机会之门在哪里?
许多像“科蚪学堂”一样的民间教育机构,力图在职业教育与升学教育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帮助孩子们获得一技之长的同时,习得更丰富的人文素养。透过这个规模并不大的民间学堂,我们可以看到流动儿童教育状况的一角:在焦虑与困境中,仍然有不少力量,致力于探索升学之外,给予孩子们良好教育的可能性。
探访及撰文| 新京报记者张婷
热烈与安静
同班的孩子学力差距很大
从5号线天通苑北站出来,一路往北,到达昌平区北七家镇。穿过一条绿树掩映的小街,一片公用篮球场背后,就到了“科蚪实务学堂”的小院。
我们到达学堂的时候,是个周五的早晨,孩子们正在上“批判性思维”课程。班上共有11个孩子,围坐在大大的书桌前,老师上一堂课已经提前布置了课后作业以及这堂课的讨论课题。讨论的题目颇为“接地气”,包括:家长能否打孩子?霍金去世,不认识的人有资格纪念吗?以及堵车是否都因为“外地人”?孩子们有备而来,课堂气氛热烈,不时发起针锋相对的争论。

批判性思维课,老师正在讲解如何思考与表述一件事情的四个层面。受访者供图。
“你对霍金熟悉吗?你都不认识他,发什么朋友圈?”霍金前不久去世时,此类质疑不时浮现,有学生在课堂讨论上反驳了这类观点:难道只有我们熟悉的人去世我们才难过吗?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去世,也是人类的损失,我们当然也会感到难过。而讨论到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与人口问题,有孩子则发出质疑:城市到底是谁的?如果说城市是大家的,那拥堵就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外地人”太多。这堂课最后,同学们则共同决定了期末的讨论辩题:如何看待快手封杀“社会摇”。
孩子们的讨论实际上比我们想象中更切中要害,讨论的气氛也热烈得多,乍看之下这堂“批判性思维”课程颇有几分西方大学课堂的思辨氛围,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各抒己见,老师不时需要把有些“过于热烈”的讨论拉回到轨道上来。不少孩子都告诉我们,批判性思维是他们最喜欢上的课。

绘图课,同学们正在绘制吉他、显示器、叶子、枪等。受访者供图。
批判性思维之外,学堂还设有心理课程、性教育课程、绘画课程,也有常规的语文(阅读)、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在阅读课上,授课教师张鑫会要求学生们必须上台做阅读分享,几堂课下来,同学们很快习惯了站上张鑫特意准备的“红地毯”上,面对大家做分享。第一学期的必读书目包括《上学记》、《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阅读的分享书目则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到张爱玲、卡福卡、马尔克斯都有,涵盖的范围更广。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来选择自己的分享书目,有的孩子会为了一本书写上长达3页纸的读后感。学堂的老师们都观察到,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求学困境,但他们实际上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渴望,而这种渴望几乎是本能的。
在另一堂英语课上,课堂气氛则安静的多,老师在用“she has left her work”作为例句,讲解“现在完成时”的构成。英语程度好的孩子,已经能够用“have/has+过去分词”的结构完成不少表述。但不少孩子显然仍无法理解这个时态变化,在回答问题时,还无法分清楚“she ”跟“her”用法的不同。虽同在一个班级学习,但孩子们的学力水平高低不均,还有的孩子因英语基础太差,无法选修英语课程。
对此,学堂采取一定程度的分层教学,对不同学力的孩子搭配不同程度的教材,提供不同程度的选修课。但对于大部分公选课程来说,学堂只能采取“就低不就高”的授课标准,优先保证学力程度较低的学生能赶上教学进度。
学堂之前
大多数孩子的受教育之路都很破碎
科蚪学堂刚刚起步,招收的孩子不多,但班上的十几个孩子,来到学堂之前的受教育之路大多都是磕磕绊绊,缺乏系统化的教育经历。李志明(化名)最初在公立学校就读,但因为跟老师产生矛盾转而退学;后来去了一家实验性很强的私人学校,每日需要诵读四书五经,“也不教为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要把四书五经死记硬背地记住”。后来家长对这种实验教育产生了质疑,李志明又换了学校。
班上不少学生的受教育经历都有类似的特点:较为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常常因为转学等原因耽误上学进度,甚至不得不留级。如果说流动儿童群体本身就面临教育之路破碎化的风险,科蚪学堂的孩子们则是流动儿童中的流动儿童——受教育经历较为破碎的特点更为突出。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 ,作者: 杨东平主编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的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全国的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全国每6个人当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两个群体的总数约1亿人。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这占据了中国儿童总人口的38%,也就是说,全国每10名儿童中就有约4名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在同样出版于2016年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则统计了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状况,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总数的37.9%,其中0-14周岁流动儿童为68.7万人,0-19周岁流动儿童和青少年合计93.3万人。而在北京市普通中小学(含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总数为48.36万人,其中约37.87万(占比约80%)的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约8万流动儿童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其余约2.49万流动儿童在高收费民办学校就读(每学期学费在1万元以上)。
这表明,大多数流动儿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都更倾向于选择在公立学校就读,但由于进入公立学校就读需要有“五证”等(务工就业证明、住所证明、户口簿、暂住证、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证件要求,也有不少家长会选择入学条件相对宽松的民办学校。在此意义上,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对公立教育形成了有益的补充。但不管在公立学校就读,还是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非京籍儿童都面临着中高考的难题。

《长乐路》,作者: [美] 史明智,译者: 王笑月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3月
这让人想到前不久出版的《长乐路》中,花店店主赵士玲一家的故事。赵士玲从山东枣庄老家来到上海,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花店,赵女士有两个以“太阳”做为名字的儿子:大阳和小阳。儿子大阳跟随母亲在上海读书,他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从上海的初中毕业时,大阳既是一千米短跑冠军又是写作比赛一等奖获得者。他是班上的优秀生,如果继续学业,赵女士觉得他一定能考进一所名牌大学。
但到了高中阶段,考虑到无法在上海高考,大阳不得不回到了山东枣庄的学校。他估摸着,以自己在上海的优异成绩,回到枣庄也能是班里最拔尖的学生。但入学第一天,他就慌了。他发现同学们所学的教材,比他此前所学的难度大很多,他根本无法赶上同学的进度。面对从优等生到差等生的落差,大阳的学习积极性也逐渐消沉,迷上了去网吧、打游戏。最终,大阳没能参加当地的高考,选择了退学。
或许是吸取了大阳的教训,赵女士的另一个儿子——小阳选择从小在枣庄读书。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面临从小与家人分开的命运,成为一名“留守儿童”。
困境与目标
培养珍贵的普通人,在升学之外找到生活道路
科蚪学堂的创始人欧阳艳琴,本身曾是名留守儿童,正是18岁以后的大学教育,开启了她的思辨之路,让她真正体会到了求知的美好。
欧阳艳琴在创办科蚪实务学堂以前,是名资深的调查记者。2015年,她离开新闻传媒行业,创建了专注流动儿童教育的“科蚪”。“科蚪”创办于东莞,最初专注于流动儿童的科技教育,在初创的一年多时间里,科蚪以社区空间的形式,为63个6-11岁的流动儿童提供科技教育,孩子们在这里做木工、做食物、学习机器人相关课程。2017年初,科蚪搬到了北京,同时调整了课程设置,使得课程更加大众化。
科蚪学堂的许多孩子,或许无法像欧阳艳琴一样,能“幸运地”参加高考。“家长和孩子当然希望能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但不少孩子在原户籍地并没有学籍。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希望和焦虑常常都是虚幻的。”欧阳艳琴对现实的残酷跟困境了解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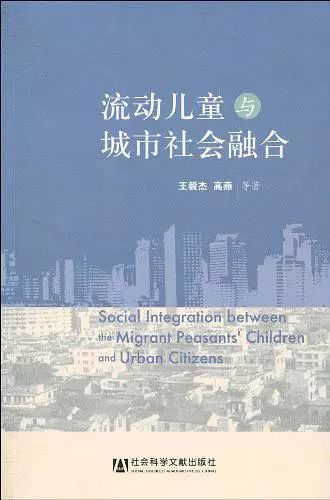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作者: 王毅杰/高燕/等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
科蚪学堂的孩子不少都陷入了“难留难归”的困境。继续留在北京上学,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以后无法参加高考;要回老家上学,必须在原户籍地有学籍,而不少孩子的家长并没有为孩子在原户籍所在地申请学籍,导致孩子无法回乡高考。顺利回乡的学生,也面临着转学带来的环境变化、教材变化等挑战。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收录了学者对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去向的跟踪调研,文章使用来自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连续五年的跟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尽管也有学生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一类大学,但总体来看,这些学生“初中后”的整体教育成就不容乐观,高中(含职业高中)阶段升学率不足40%;大学升学率不到6%。
在这样的困境之中,很多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孩子和家长实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科蚪学堂也只能以微薄的努力做好这其中的“一步”。蝌蚪学堂的目标是培养珍贵的普通人,希望孩子们离开学堂时,是自信、勇敢、自尊、笃定的城市新民。而具体的方式,则是提供比职业学校更丰富的人文教育、比公立学校更偏向实践的一技之长。如此,即使面临升学困境的孩子,也有希望在升学意外找到一条通往有尊严的生活的道路。
在一场演讲中,欧阳艳琴解释了“科蚪”名字的由来:“科蚪”(kidsdoit),实际是个拟声词,它来源于对敲门声的模仿。
在我们的城市中,实际有数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城市的边缘敲门。命运无常,现实充满困境,而如同“科蚪”所寄望的,“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了孩子的敲门声,希望你能至少为他们打开门。”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