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父亲缺乏权威,于是人们信奉“强硬少年”希特勒
2018年03月14日 10:27:01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爱利克•埃里克森
或许尽快遗忘发生之事可以在德国或其他地方推动人类的进步,但纳粹的黑色奇迹——精心策划,又很快失败——只是一种当时全世界潜在发展趋势的德国版。这种趋势仍然存在,希特勒的阴魂在期待它。
编者按:在历史长河的某段时间里,希特勒和他的同党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伟大、勤奋、好学上进的民族的军事政治领袖。为了阻止这群满口谎言的“专家”对整个西方文明构成威胁,全世界的工业大国联合起来进行了抗击。西方世界希望,德国人能再次成为易于驯服的“好顾客”,重新追求文明,永远不重蹈覆辙。
或许尽快遗忘发生之事可以在德国或其他地方推动人类的进步,但纳粹的黑色奇迹——精心策划,又很快失败——只是一种当时全世界潜在发展趋势的德国版。这种趋势仍然存在,希特勒的阴魂在期待它。
善良的人们相信心理学奇迹,如同相信经济奇迹一般。发展中的文明在自身进步中存在毁灭的隐患,它分裂了曾经的道德水准,威胁了不完整的个体,甚至释放出充满破坏性的力量。在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中,他几乎只字不提他的母亲,还确切列举了自己优于父亲的反抗手法。冥冥中,隐患潜藏在了不可视的心理问题里。
以下内容来自《童年与社会》,面对希特勒的童年,历史只能教导那些不急于遗忘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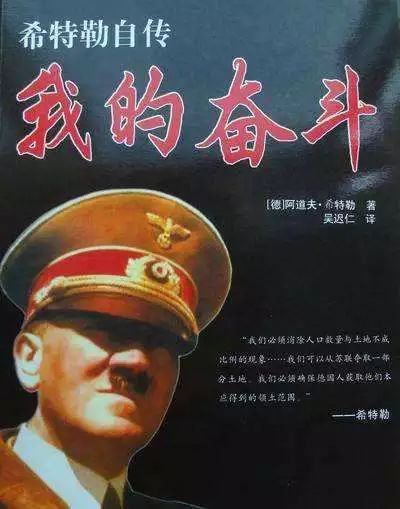
《我的奋斗》
我应当以布朗·派珀那甜美而迷人的口吻开始我的报告。以下是《我的奋斗》中所述的希特勒的童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个被德意志殉难之光所照耀的小镇河边旅馆,居住着我的双亲,他们在血统上是巴伐利亚人,国籍则为奥地利。父亲是一名尽职的公务员,母亲献身于料理家事,并以永远同等的爱关怀着她的孩子们。
这句式结构,这音调特征,都预示着我们在听一个童话。我们的确可以将它作为试图创造现代神话的一部分来分析。但是神话无论新旧都不是谎言。试图证明它毫无事实根据是没有意义的,声称这虚构产物是假话和胡言乱语也是徒劳的。
史实同具有深意的虚构混合形成了某个纪元的现实,它引起了善良人的惊叹,也点燃了人们的野心。受其影响的人们不会去质疑它的真实性和逻辑性,少数无法克制怀疑的人们会发现自己的质疑理由苍白无力。因此,批判性地研究神话,要求我们分析它的想象和主题部分与受其影响的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
病态的仇父心理?
“……父亲是一名尽职的公务员……”
除了这里对父亲略带伤感的描述,希特勒在第一章用相当大的篇幅热切地声明,他的父亲或者“这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他去做公务员”。他已经在青少年初期便明白,他对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毫无欲望。他同他的父亲差距太大了!
尽管他的父亲也在青少年初期反叛过,在13岁逃离家庭,想成为“更出色的人”。然而在23年之后,父亲却重返家中,成为无关紧要的公务员,“没人记得很久以前那个小男孩了”。希特勒说,这徒劳的反抗使他的父亲过早衰老。然后,希特勒确切地列举了自己优于父亲的反抗手法。
这是否揭示了一种病态的仇父心理呢?如果说这是一种狡猾的宣传手段,那么是什么给了这个身在奥地利的德国人信心,让他相信自己少年时期的故事能够说服蛊惑绝大多数德意志帝国的人?
显然,虽然许多德国人的父亲的确有小希特勒那样的父亲,但并不是所有德国人的父亲都是那样。然而我们知道看上去令人信服的文学主题未必是真实的。它只需要听起来真实可信,好似唤醒了某些深切的过去。那么问题是,是否由于这位德国父亲在家庭中的位置令他如此行事,以致让希特勒形成了关于父亲的内在图像,而这个图像或多或少又和他本人的政治形象相符。

希特勒
表面上看来,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的地位或许同维多利亚时期“随同父亲生活”的版本十分近似。但是教育模式却很难一概而论。它因家庭和成员而不同。
我将在此展示一个关于某种德国父亲的身份模式的印象主义版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高尔顿那些混杂在一起的照片表现了其想表达的主旨那样。
当父亲从工作岗位回到家中,似乎连墙壁看上去都“挤成一团”。而母亲——通常作为家庭中非正式的主人——则表现出足够令孩子们意识到的异样。她急于满足父亲的突发奇想,以免惹怒他。小希特勒屏住了呼吸,因为父亲可不赞成“胡言乱语”。
也就是说,父亲既不喜欢母亲女性化的情绪,也不喜欢孩童玩耍的样子。只要他在家,母亲就得唯命是从。他的行为揭示了他可不喜欢母亲趁他不在的时候和小希特勒纵情玩耍。他总是像呼喝孩子们一样对母亲说话,打断提问,期待顺从。小希特勒感到所有同母亲在一起时的愉悦都会刺痛他的父亲,而她的爱和赞美——有利于日后获得满足和成就——只能在父亲不知道或者同他明确的期许相悖时才能获得。
母亲在心情愉快时,会向父亲隐瞒希特勒的“胡言乱语”或者所做的坏事。当父亲回到家中的时候,她通过数落小希特勒来表达自己的不悦,让父亲为这些错误向小希特勒施加体罚,尽管错误的细节他并不感兴趣。儿子是邪恶的,惩罚总是事出有因。
后来,当小希特勒去观察同众人在一起的父亲时,他注意到父亲向上级献媚,以及注意到父亲与同事们饮酒欢唱的时候表现出极度多愁善感,这让他获得了悲观主义的首要因素——对人类尊严的深切怀疑,或者至少是对“老头子”的怀疑。当然,小希特勒也对父亲怀有尊敬与爱。
然而在青春期的暴风骤雨中,当必须用他关于父亲的内在形象来解决同一性问题时,希特勒形成了严苛的德式青春期个性。这是一种公开的反叛和“秘密的罪孽”的奇特混合物,伴随着愤世嫉俗的不良行为和恭顺的服从、浪漫主义以及消沉的意志,倾向于摧毁个体的精神。

希特勒
在德国,这种模式有其渊源。它总是碰巧形成。的确,有些父亲在他们的孩童时期深深厌恶这种模式,并极度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远离这种模式。但这一期望每次都在危机发生时令人失望地落空了。另一些试图抑制这一模式的父亲,却只能徒增他们及孩子的神经质。通常,当孩子了解父亲对自己没有能力打破恶性循环而感到不开心时,这一情绪化的无能为力会令男孩感到同情和厌恶。
那么,是什么令这一冲突具有如此普遍的宿命性呢?是什么——以一种无意识却具有决定性的方式——使得德国父亲的冷漠与严苛同其他西方国家的父亲的类似特性截然不同?我认为区别在于,德国父亲基本上缺乏真正的内在权威性,这是一种由文化理念和教育方式综合形成的权威。
这里所说的德国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的是德意志帝国。在探讨德国诸事之时,我们提及的是德国保留区,以及那些“典型的”单独实例。德国父亲内在的权威看上去深深地扎根并建立于古老的农村及小城式的安逸、城市文明、基督徒的谦卑、职业化教育以及社会改革的精神之上。重点是,当德意志帝国的图像占据主导,工业化渐渐打破了早年的社会阶层化时,所有这些并不能承担起其在民族范围内的综合含义。
严苛只有在自愿服从能带来义务感与尊严感时,才会富有成效。然而,事实看来,这似乎只能将过去同与经济、政治以及精神体系的变化相一致的现在联合起来。
其他西方国家有其自身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如同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那样,在接管贵族阶层的特权中,逐渐对贵族理念产生了认同。这里我不禁想到每个法国人心中的法国骑士,或者每个英国人心中的盎格鲁—撒克逊绅士,或者每个美国人心中具有反抗精神的贵族。民主革命融合了革命理念,创造出“自由人类”的概念(这一概念假定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可缺少的自我否定,以及不断革命的警觉性)。
因此,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同生存空间问题联系起来。德国的统一性从来不会包括这样的意象,它不会到达能影响到潜意识的教育模式的必要程度。一般德国父亲的统治地位和严苛性不会同亲切以及尊严混合起来。亲切和尊严都来源于参与集成化的事业。
通常,父亲宁可在日常或者决定性的时刻,代表德国顶级军士及公务员——“穿着代表直接权威的制服的”的那些人——的习俗以及道德标准。他们将自由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出让给官衔或者终身抚恤。

童年的希特勒
此外,以传统形式指导青少年处理冲突的文化习俗也出现了解体。举例来说,在过去,漫游的习俗十分流行。男孩大约在希特勒宣布自己反对意见的年纪,要离家去异乡做学徒。正是这习俗导致希特勒的父亲离家出走。在前纳粹时期,一些分离仍会发生,带着父亲的雷霆之怒和母亲的眼泪,或者反映在更温和的抗争中,这些抗争因带有更多个性化和神经质而不太有效,或者会受到压制,并不是因为父子间的关系破裂了,而是男孩同他们自身的关系破裂了。
经常只有男性教师们受到影响。男孩扩展他们对整个中产阶级——在男孩眼中是由“区区市民”组成的可鄙世界——的理想主义或者愤世嫉俗的敌意。我们很难解释市民这个词语的内涵。它同固定的公民意思不同,也同在年轻的革命家阶级意识中被过分扩大的资本家意识相左,尤其是同那些自豪的国民或者那些有责任感、接受平等的义务、作为个体维护自身权益的市民不一样。
它意味着成年人背叛了青年和理想,在那些琐碎而又卑微的保守主义中寻求庇护。这种形象经常被用来说明所有“正常”实为腐败,以及所有“得体”实为软弱。作为“自由自在漫游的鸟儿”,青少年男性会沉溺于一种对自然的浪漫幻想,同许多叛逆者分享幻想,接受那些年轻领袖——他们也是专业且具有忏悔心的青少年——的领导。
另一类青少年是“孤独的天才”,他们会写日记、诗歌和论文。在15岁时他们会哀悼唐·卡洛斯。唐·卡洛斯说出了绝大部分德国青少年的怨诉:“在20岁,不朽之业仍一事无成!”其他青少年——有理智的犬儒主义者,有行为不端者,有同性恋者,也有种族歧视者——则会组建各种小组。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去除这些个体的父亲们的影响,遵守某些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本质:自然、祖国、艺术、存在性等。
这些是纯粹母亲的超然形象。相对于父亲那令人害怕的形象而言,她是唯一不会背叛这位怀有反抗之心的男孩之人。有时他们会假设母亲公开或者私下里赞成——如果不是妒忌的话——这种自由,父亲则被他们认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无法表现出充分的敌意,那么他们便会故意挑衅,因为反抗就是他们全部的人生经验。
在此阶段,德国男孩宁可死也不愿意意识到事实真相,即这种朝着乌托邦方向发展的极具误导性的主动精神会引发深层的内疚感,最终导致精疲力竭。在童年早期实现对父亲的认同这一问题涌现出来。错综复杂的通向捉摸不定的命运——现实——的道路会最终让男孩成长为市民,一位同其他人一样带着永恒罪恶感——因为了钱财、妻子和孩子献出了天赋而产生——的“区区市民”。

纳粹支持者
这记述带有典型的漫画般的讽刺效果。然而我坚信,无论是明显的类型还是隐蔽的模式都在现实中存在。实际上,这种存在于早熟的个人反抗与顺从的市民精神之间的分裂是一种更强烈的因素,构成德国政治的未成熟性。这种青春期的反抗是一种个人主义以及革命精神的失败。
我相信德国的父亲们不仅不会反对这种反抗,事实上还会无意识地培养它,把它作为一种维持他们对于年轻人家长威信的方法。一旦一个家族中的超我在童年早期稳固地确定下来,你便可以给年轻人一条绳索。在这条绳索的羁绊下,他们不会让自己走太远的。
在德意志帝国的品性中,这种独特的理想主义反抗与恭顺服从的结合导致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德式道德准则是自我否定且残酷的,但它的理想典范却飘忽不定,甚至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德国人于公于己都很严厉,但缺乏内在权威的极端严苛会引发苦难、恐惧和恶意。因缺乏一致的典范,德国人行事倾向于带着盲目的自信、残酷的自我否定和极端完美主义追逐许多矛盾的、带有毁灭性的目标。
在战败和1918年的革命之后,这种心理上的矛盾与日俱增,以至于在德国中产阶级中酿成大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包括渴望成为其中一员的工人阶级人士。他们对在战场上失败的上层阶级的奴性,突然失去了意义。通货膨胀威胁到他们的养老金。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群处于摸索中的大批民众并没有准备好获得自由公民或者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角色。
很显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的形象才能迅速说服如此多的民众,或者说麻痹了更多人。那么,我不认为,那些贬损传言所勾勒出的希特勒的父亲,以他显而易见的粗鲁举动,成为一名典型的德国父亲。这样的事情在历史的进程中频繁发生:一种极端的甚至非典型的个人经验刚巧与一种普遍的潜在冲突契合,以致危机状态将这种个人经验提升至重要位置。
事实上,我们应该记起的是,伟大的国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境外人士作为他们的领袖: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岛,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童年模式,也构成德国民众在阅读了希特勒年轻时期的故事之后发出深切感叹的基础。“无论我的父亲有多么固执和独断……我在拒绝对自己几乎无益的要求时,和他一样固执和倔强。我不想做公务员。”
这种个人启示与精明的宣传的组合(与高声和坚定的动作结合在一起)终于建立起普遍的信仰,这正是那些德国青年所等待的郁积于心的反抗:没有作为他的父亲、君主或者神的任何老家伙能挡在他热爱德意志母亲的道路上。与此同时,这证明了那些成熟的男性,那些曾经背叛了他们青春期反抗的人,不配再指导德国青年,从今以后青年们要“创造自己的命运”。无论是父亲还是孩子现在都认同了领导者——一名从未屈服的青少年。
心理学家过度强调了父亲的属性对希特勒的历史形象的影响。
希特勒这名青少年拒绝在任何内在意义上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换句话说,成为皇帝或者总统。他不会重复拿破仑的错误。他是元首,并美其名曰“兄长”。他接管了父亲的特权,然而没有过度维持这一形象。

希特勒和其他将军
他将父亲称为“稚气未脱的老家伙”,并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定位——一名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却依旧保持年轻的人。他是坚不可摧的青少年,选择了远离市民娱乐、商人安稳与精神平和的职业——一名党派领导,利用个人崇拜、制造恐怖以及精明地怂恿成员们投身于没有后路的犯罪行动来聚拢人心。他是个利用了双亲的失败的无情家伙。
“我的职业问题解决得比我预期的还要迅速……在我13岁时,父亲突然亡故。母亲感到有义务继续让我接受那些有利于从事公务员职业的教育。”希特勒因此得了严重的肺病,然后“所有我为之而战的,所有我秘密渴望的,突然变成了现实……”他母亲不得不允许这个生病的男孩去追逐她曾经否认的事情。他被允许去做一名艺术家。他投身于此,却在国家艺术学校的入学考试中失败了。然后他的母亲去世了。现在,他在自由了,且孤身一人。
职业上的失败以及早期学业的失败,使得其个性中的力量以及男孩子气的韧劲得到了合理解释。众所周知,当他挑选下属时,希特勒在弥补类似的市民失败。他侥幸由此逃脱只是因为德国人习惯于为学校的失败镀金——以有隐藏天分的可能性理由。德国“人道主义”教育一直在宽恕与哺育式教育分道扬镳的人,并训诫那些诗歌中对乡愁蔓延的美化。
在对待德国内外的“老”一代过程中,希特勒从此扮演起顽固、狡猾和愤世嫉俗的角色。事实上,无论他何时感觉到他的行为需要公开的辩护和道歉,他总是如同《我的奋斗》第一章中所述的那样先设置好舞台。
他那激烈的长篇演说集中在一名外国领导者——丘吉尔或者罗斯福——身上,将对方描述为封建暴君以及“老不中用”。接着他创造了两个形象,一个滑头的富家子弟以及一个颓废的玩世不恭者——达夫-库珀和艾登。在众人中,他选取了这两人。看上去,希特勒这个强硬的青少年只要比其他垂暮之人强,德国人就能勉强接受他那业已破裂的允诺。
希特勒从不是任何人的兄弟
“……母亲献身于料理家事,并以永远同等的爱关怀着她的孩子们……”
除了在他的童话中的某些补遗,希特勒几乎只字不提他的母亲。他谈到,她有时仁慈地为他这位男孩中的英雄卷入打架而担忧。在父亲去世之后,她感到“有责任”——尽职胜过爱好——让他继续接受教育。之后不久,她也过世了。他说,他尊敬自己的父亲,但更爱母。
“她的孩子”对她已经没有更进一步的阐述。希特勒从不是任何人的兄弟。
毫无疑问,希特勒——作为极具表演性和歇斯底里的冒险家——对于母亲有一种病态的依恋。但这不是此处的重点。因为无论是否病态,他巧妙地给予了母亲两种形象,每一种都具有极高的宣传价值:充满爱的,孩子气的,被烹饪稍许困扰的,这类母亲被归入温暖舒适的背景;巨大的如同大理石雕像一般,理想中的纪念像。
尽管希特勒很少提到自己的母亲但他在描述中却经常提到超人母亲形象。他的德意志帝国童话并没有简单地说他出生于布劳瑙是因为他的双亲居住在那里。不,原文是“命运指定了我的出生地”。
它并不是因为自然法则而发生的。不,原文是“命运的低劣把戏”令他“出生于两场大战之间那段平静而有秩序的时期”。当他贫困时,“贫穷将我紧紧拥抱于臂弯中”。他同时发出慨,“悲伤女士是我的养母”。但他随后学到把所有这些“造化弄人”赞美成“神的智慧”,使他坚定决心服侍自然这位“残酷的智慧女王”。

希特勒
当一战爆发,“命运大发慈悲地许可”他成为一名德国步兵,同样“无情的命运之神,用战争衡量国家与人类”。在战败后,他站在法庭前为他首次革命性的举动辩护,他确信“历史之神的不朽判决会微笑着撕毁”陪审团的裁定。
命运,忽而狡猾地令英雄沮丧,忽而又仁慈地迎合了他的英雄主义,撕毁了那些心怀不轨的老头子们的判决。这是一种遍及大部分德国人理想主义的初期意象,典型地表达了一名青年英雄的主题:他在国外功成名就,回归后解放他那“被囚禁的”母亲并提升了她的地位。这与俄狄浦斯王的传奇有浪漫的相似性。
在超人母亲的意象背后,存在有关母性的双面形象:母亲有时显得爱玩闹、孩子气和慷慨大方;有时则背信弃义,与阴险的力量沆瀣一气。我相信这是一种父母在家长制社会中留给孩子的常见印象。
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以种种方式保持着不负责任和孩子气的一面,成为斡旋者和中间者。因此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丈夫因难以理解她的孩子气而恨她,孩子因她身上冷漠的父性而恨她。由于“母亲”通常会成为“世界”的一种潜意识模型,因此希特勒对母性形象的矛盾性成了他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之一。
元首与母亲和家庭保持着模棱两可的关系。在精心策划的国家幻想中,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男人,超人母亲形象一会儿试图毁掉他,一会儿又被迫护佑他。他一直同其斗争,也一直在取悦她。但他在生命旅程的终点也不承认女性能够成为同伴。他坚持将爱娃·布劳恩塑造为一名忠诚的女性,但不久后仍亲手射杀了她。传说如是结束。其他男性的太太们在总理的庇护下生儿育女,而他自己,根据他的官方传记作者所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他不懂任何家庭生活,也不知道邪恶之事。”
希特勒把这种对女性的矛盾作为一种图像,带进他同德国的关系中。他公开蔑视广大乡村同胞,尽管他们也是德国的组成部分。他在这些人面前表现得异常激动,用他那狂热的吼声喊着“德国,德国,德国”,来恳求他们相信这个神秘的国家本质。
然而,德国人对于人类和整个世界总是倾向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大多数族群或国家中,世界基本上被感知为真实的“外部世界”。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世界的特性时常发生变化,并总是趋于极端。他们所体验到的世界,或是作为年龄和智慧上极端优秀的存在,成为他们永恒向往与流浪的目的地;或是一副卑鄙、狡猾、敌人环绕的模样,那些敌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背叛德国;或是一个神秘的生存空间,通过日耳曼式的勇气赢得,并在上千年中用于青少年的扩张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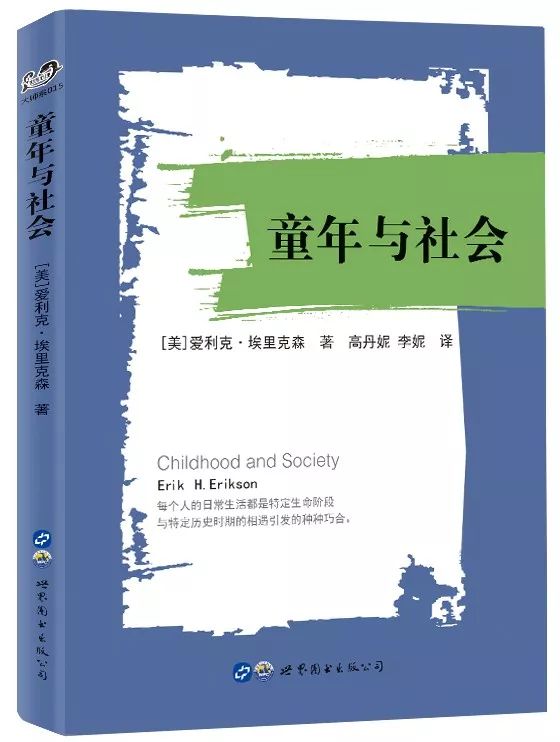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