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洲》全译本问世 80年前的自传小说讲述非洲故事
2017年09月13日 20:22:37
来源:凤凰文化
v\:* {behavior:url(#default#VML);} o\:* {behavior:url(#default#VML);} w\:* {behavior:url(#default#VM
日前,丹麦著名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经典小说代表作《走出非洲》全译本无删节版问世。布里克森是与安徒生齐名的丹麦“文学国宝”,获两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海明威认为她更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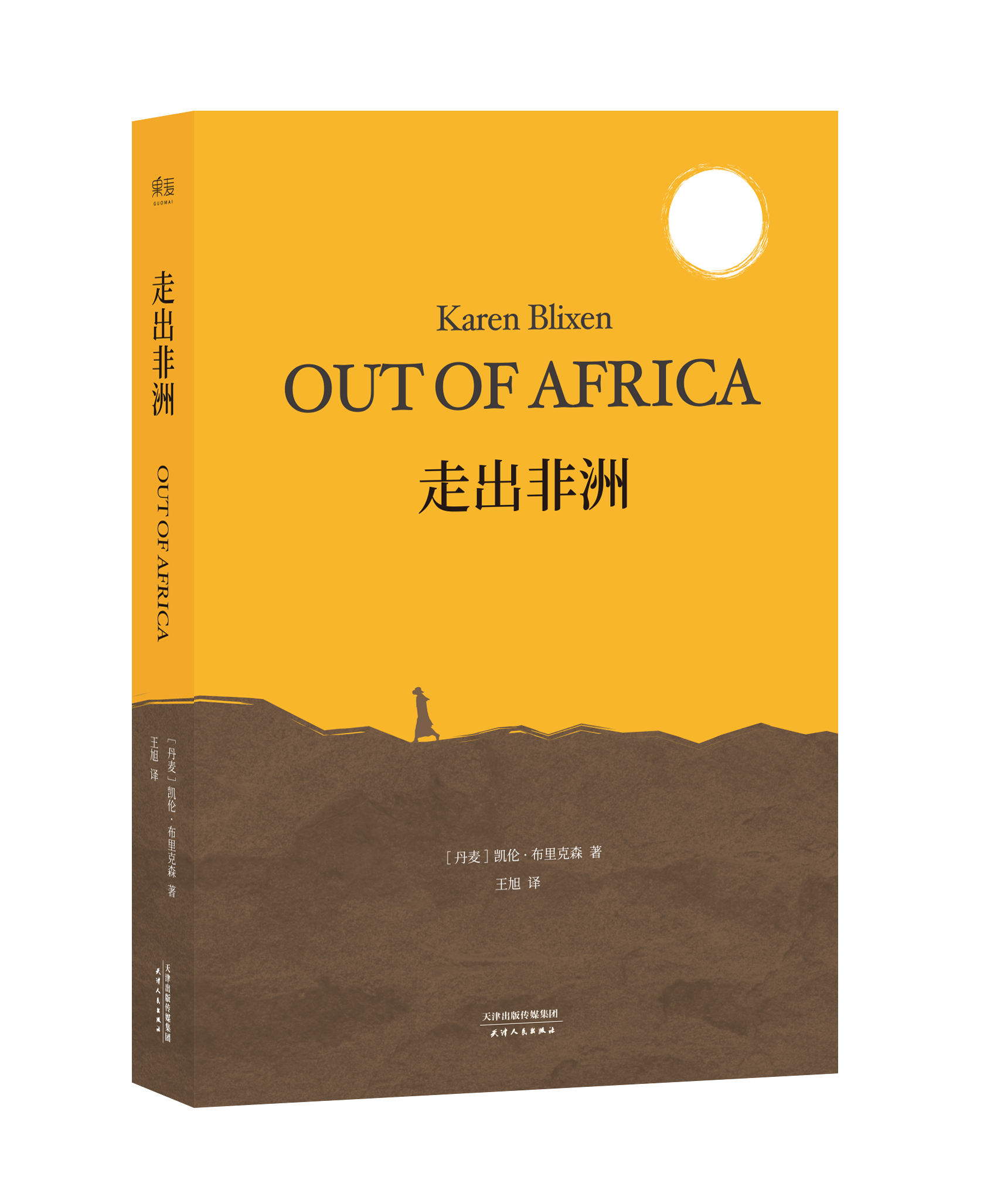
《走出非洲》,[丹麦] 凯伦·布里克森著,王旭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版
自传体小说讲述非洲感人故事
《走出非洲》描绘了1914年至1931年,凯伦·布里克森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的故事。作者匠心独运,将众多的人、事、景、物融于一炉,字里行间流露着对非洲和非洲人民的真挚情感。小说记录了白人和土著居民的交往、土著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作者经营农场的艰辛和她的爱情,缠绵悱恻。书中关于非洲大地自然风光的描写最是脍炙人口。
《走出非洲》发表于1937年,是作者的自传体小说。该书出版后,在东非和英语国家持续畅销,多次再版,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全世界流行,常年位居亚马逊北欧国家作品销售榜单第一名。书中有很多意蕴绵长、感人至深的故事,例如书中的《鹦鹉》小故事,记录了英国贵族和中国妓女的爱情故事。
“二十世纪最唯美的一本书”
凯伦·布里克森的作品确实影响了海明威等一大批作家,海明威也认为布里克森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作者麦卡勒斯很喜欢《走出非洲》,对凯伦·布里克森非常推崇;《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认为《走出非洲》是“二十世纪最唯美的一本书”。
《走出非洲》在国内也拥有众多读者。著名歌手、诗人周云蓬曾在微博上称赞道:这两天听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真是一篇好小说。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中,著名影星张艾嘉倾情朗诵《走出非洲》内容,反响热烈。
《走出非洲》改编的同名电影,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于1985年上映,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七项奥斯卡大奖,已成为影史经典。
该书编辑表示,该书为全新无删节版,译自权威底本,在追求译文准确的同时,尽量保留作者细腻的文风,期望能让中文读者更好地欣赏这本世界文学经典之作。
创作素材源自苦难的人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凯伦·布里克森在欧美各国声誉卓著。1954年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词中说:这项奖应该授予凯伦·布里克森。其实早在她刚刚登上文坛的时候,就崭露头角,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的称赞和提携。
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她先后用英文、丹麦文发表《七篇哥特式的故事》《走出非洲》《冬日的故事》等作品。《走出非洲》为她赢得巨大声誉,使她获得两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与安徒生齐名的丹麦“文学国宝”。
凯伦·布里克森之所以能写出《走出非洲》这样的经典著作,与她的生平有很大关系。她在1885年出生于丹麦伦斯特德一个贵族家庭,十岁时,政治家兼作家的父亲自杀身亡,死因众说纷纭。随后,她跟随母亲过上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成年后,她与丈夫在东非肯尼亚经营咖啡园,一再失利受挫,她与远房表兄瑞典男爵布罗尔·冯·布里克森-芬内克的不幸婚姻,更是在其情感生涯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印记。
悲惨的童年、不幸的婚姻生活、失败的农场生意,虽然让她经历了很多磨难,却也给她提供了丰富创作素材。
新书试读:埃萨的故事
战争期间,我有个厨师,名叫埃萨。他是个性格温和、非常理智的老头儿。有一天,我去内罗毕的麦金农杂货铺买茶叶和调料。一位女士走过来跟我说,她知道埃萨在为我做工。这是一位个子矮小、脸上棱角分明的女士。我说:“是啊。”“以前他是在我那儿做工的,”这位女士说,“现在我想让他回来。”我告诉她,很抱歉,她不能带走埃萨。“哦,我可不觉得这样,”她说,“我丈夫是政府官员。请您回家后告诉埃萨,我想让他回来,他不回来,我就把他送到军队的运输部队去。我也知道,除了埃萨,你家还有足够的仆人。”
回到家之后,我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埃萨。第二天晚上,我才想起来告诉他,我说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女主人,把那位女士的话转告给了他。让我吃惊的是,埃萨立刻就乱了手脚,陷入了恐惧和绝望中。“我的天啊,姆萨布,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他说,“那位女士说什么就会做什么的。今天晚上我就得离开了。”“简直是无稽之谈,”我说,“他们不可能把你送到运输部队去。”“上帝救救我吧,怕是现在都晚了。”埃萨说。“但是埃萨,你走了,我上哪里去找厨师?”我问他。“啊,如果我被送到运输部队,或是直接死掉了,你也不会有厨师了呀。而且我确定,我这次是死定了。”
在那段日子里,人们非常害怕运输部队,所以我说什么,埃萨都不愿意听。他向我借了一盏防风灯,用一块布把他所有的财产包起来,然后就摸黑去了内罗毕。
从那天开始,他离开农场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后来,我去内罗毕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有一次是在去内罗毕的路上和他擦肩而过。 他变得更老更瘦了,脸颊凹陷,头顶上的黑发变成了灰白。在内罗毕市里,他是不肯跟我说话的。但如果我们在平坦的路上相遇,我就会停车,他会把头顶上的鸡笼放到地上,安心地站着和我聊天。
虽然他和以前一样举止温和,但他还是变了,而且变得很难交流。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心早就跑到了很远的地方。命运折磨着他,他一直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不得不利用我想象不到的资源生活。这些生活经历磨练了他,让他的心思变得透明。和他谈话,就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好像已经通过修道士见习期,进了一家修道院。
他问我农场上的生活。土著仆人们总是觉得,一旦他离开,其他仆人们就会对他的白人主人极其凶恶。他问我:“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我说,有人告诉我,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他就说: “你是知道的,如果再打上十年,我肯定会忘记怎么做你教我的那些菜了。”
这位瘦小的基库尤老人站在横贯非洲大平原的路上,脑子里居然有和布瑞拉特-萨伐仑一样的想法。这位美食家说过,如果法国大革命再持续五年,蔬菜炖鸡肉的烹调技术就会失传。
很明显,他刚刚表达的遗憾主要是为了我。为了结束他的这种“怜悯”,我转移话题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想了一分多钟,然后像从很远的地方把思绪拽回来似的说道:“姆萨布,你记得吗? 你曾经说过,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太累了,它们每天都得套着牛轭拉车,不会像农场山上的牛一样有一天休息的时间。现在,我和那位女士一起生活,就很像那些印度柴禾承包商的牛。”土著人本身其实对动物并不会抱有什么怜悯,所以在埃萨心里,我的那些关于牛的说法一定是很牵强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才会一直看着远处,眼神里充满了歉疚。况且这个话题又是他自己提到的,他心里估计会觉得莫名其妙。
战争期间我的大部分烦恼都来自信件。那时,不管是寄出去的还是收到的信,都会被内罗毕的一个矮个子瑞典审查员拆开。这个审查员整日昏昏欲睡的,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可疑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的生活太单调,所以他才对信件里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兴趣。他读着我的信,其实就像是读杂志上的连载故事一样。 我常常在信里写一些威胁他的话,专门让他去读。我说,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些威胁付诸行动。战争结束之后,他或许是记起了我的这些威胁,又或许是他幡然醒悟了,后悔了,所以就派人跑过来,告诉我停战的消息。他派人过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家。他走了之后,我去树林里散步。周围一片静寂,一想到此时法国和佛兰德斯前线一片静寂,而且所有的枪支也安静下来,我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正是因为这种静寂,欧洲和非洲才变得非常近,就好像从这片树林中的小道就能走到维米岭山脉似的。从树林里走回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是埃萨带着行李站在那儿。看到我,他立刻开口说道,他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是一幅画,镶嵌在玻璃下面,还加了外框。画上是一棵树,笔画非常仔细,上百片叶子都被涂上了鲜亮的绿色,而且每片叶子上都用红色墨水写了一个很小的阿拉伯字母。我觉得这些字应该都出自《古兰经》,埃萨解释不清它们的意思。他一边不停地用袖子擦拭着玻璃,一边说这绝对是一份好礼物,是他在受折磨的这一年里,拜托一位内罗毕的伊斯兰老阿訇帮我做的。这位老人一定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把整棵树画下来。
之后,埃萨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
法拉和威尼斯商人
有一次,一个朋友给我写信,信里描述了一场新上映的《威尼斯商人》。当天晚上,我把信又拿出来读了一遍。读着读着,整场喜剧就在我面前变得生动起来,好像就在我的房间里上演似的。于是,我把法拉叫过来,和他聊起这出喜剧。我给他解释了其中很多的细节。
和所有身上流着非洲血液的人一样,法拉也特别喜欢听故事,但要保证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单独在房间里,他才肯听。因此,每当仆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屋,法拉就会站在桌子的另外一头,瞪着双眼,一脸严肃地听我讲故事。此时,如果有人从农场经过,隔着玻璃向我的房间里望去,就会看到我在讲,法拉在听,他会感觉我们正在讨论家务事。
当我讲到安东尼奥、巴萨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纠纷时,法拉听得特别专心。故事中的交易数目庞大,过程复杂,或多或少地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因此非常符合索马里人的口味。讲到关于那一磅肉的条款时,他问了我一两个问题。显然,这协议对他来说有点奇怪,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人嘛,很可能是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故事慢慢地变得血腥,他对故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当我讲到鲍西娅走上舞台时,他竖起了耳朵。我想,他很可能把她想象成了部落里的法蒂玛。聪明机智、善于迂回,正准备扬帆出海,打败所有男人。有色人种通常不会偏袒故事中的任何人物,他们只对设计得极为巧妙的情节感兴趣。在现实生活中,索马里人有着很强的价值观,天生就有一颗义愤填膺的心。但在小说中,他们就不会那么较真了。因此,法拉同情的是那个马上要损失一大笔钱的夏洛克。
对于夏洛克的败诉,他很不服气。 “什么,”他说,“那个犹太人真的放弃索赔了吗?他怎么能
这么做呢。那磅肉就应该归他。他毕竟花了那么多钱,得到这点肉一点儿也不为过。”
“没办法呀,他又不能一滴血不流地把那块肉割下来。”我说。
“姆萨布,他可以用一把烧红了的刀去割,那就不会流一点儿血了。”法拉说。“但是,”我接着说,“他只能割下来一磅肉呀,多一点儿少一点儿都不可以的。”
“谁会怕这个,尤其是一个犹太人?他可以每次只割下一点点,手边就放一个小秤,割一点儿,称一下,直到够一磅为止。没有朋友给这个犹太人这么建议吗?”
所有索马里人都会做出非常戏剧性的表情。此时,法拉全身的动作举止基本上没有变化,但面貌却狰狞起来,好像他本人此时就站在威尼斯的法庭上,面对着安东尼奥的朋友们,面对着威尼斯总督,为他的朋友或同伙夏洛克打气。他眼神闪烁,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面前的商人安东尼奥。商人此时裸露的胸膛正抵在刀锋上。
“姆萨布,他可以每次割一小点儿,很小的一点儿,就能让那人痛不欲生。甚至在没有割完一磅肉之前,就能让他难受好长一段时间了。”
“可是在故事里,那个犹太人放弃了。”我说。
“是啊,夫人。那真是太可惜了。”法拉说。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