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如何“吐槽”卡夫卡、海明威、艾略特、乔伊斯……
2017年09月13日 16:21:10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博尔赫斯
对海明威来说,哈里·摩根是一个堪称楷模的男子汉。海明威向“垮掉的一代”展示屠杀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样的小说只能使人感到沮丧,在我们心中连尼采式的寓言的寓意也没有留下。

博尔赫斯
1936年,博尔赫斯的父亲健康迅速恶化。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从10月16日开始,博尔赫斯开始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家庭》杂志“外国书籍和作者”栏目的主编。该专栏持续三年之久,博尔赫斯创作短文二百余篇,内容涉及作家生平、创作、作品评论和新闻性的“文学生活”。这些“豆腐块”式的文字从梦魇、隐喻、时间谈到《神曲》的修辞意图、侦探小说的叙事法则,从莎士比亚、卡夫卡谈到曹雪芹、紫式部,是读书笔记和作家札记辑录。博尔赫斯相信许多“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乃或街谈巷议中都可能有着堪与经典媲美的东西。
凤凰文化在阅读中发现,在这个栏目中,有些名字被反复提及,其中赫胥黎4次,福克纳、乔伊斯、卡夫卡等各两次,读者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间,或者是对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博尔赫斯的判语也往往有所差异,对比看来,更是饶有趣味。
譬如,在评论卡夫卡的《审判》时,博尔赫斯指出了卡夫卡“那百试不爽又充满无数细小障碍的虚构作品”或许来源于芝诺,在对卡夫卡的整体介绍中,他又称赞了《中国长城建造时》,《豺与阿拉伯人》等短篇小说,而“《美国》是他的小说中最有希望的一部……《审判》、《城堡》的结构完全像埃利亚的芝诺的那些永无止境的悖论”。
博尔赫斯认为乔伊斯是“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也可以说是最好的作家”,《尤利西斯》“ 有些句子和段落不比莎士比亚逊色”。但“乔伊斯的头几本书并不重要”,随后创作的作品也“不过是没有生气的同形异义问自己游戏的交织物”,“很难说这种串连不是失败和无能”——这本书指的是《芬尼根的守灵夜》。
他热情地赞美了福克纳在小说形态上的巨大突破,“是少有的几位注重小说形式和小说结局及性格的作家”,“他的能力远在其他作家之上”,他赞美《不败者》的有血有肉,“如走近大海或感到清早的来临”,也不客气地地指出“《野棕榈》是他作品中最不理想的一部”。
在《赫胥黎家族》一文中,博尔赫斯指出,“或许我们最好还是像赫胥黎家族那样来对这个世纪提问”。在评论《和平主义百科全书》时,他也赞美了赫胥黎“他的论据是理智的”,“令人尊敬地不偏不倚”。但是在讨论《小说、散文和诗歌》时,博尔赫斯又毫不留情地指出,“虽然散文和游记显示了赫胥黎合乎情理的悲观主义,那种几乎让人受不了的清醒。小说和诗歌却显示了他创作上不可救药的贫乏。”
此类精彩论述在《文稿拾零》中俯拾皆是,凤凰文化特摘取了博尔赫斯的几则毒舌评论,与读者分享。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如果结合博尔赫斯全集的已经出版的前两辑,还有更多精妙评论等待读者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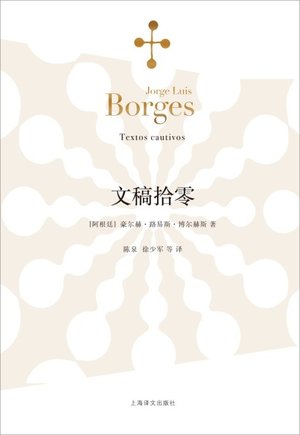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年6 月
阿道司·赫胥黎《小说、散文和诗歌》
进入“人人文库”,跟尊敬的比德和莎士比亚、《一千零一夜》和《培尔·金特》平起平坐,在不多久之前还是一种封谥。最近,这扇窄门开了:皮埃·洛蒂和奥斯卡·王尔德进去了。这两天阿道司·赫胥黎刚进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能买到他的书。这本集子共十六万字,分为价值不等的四部分:小说、游记、散文和诗歌。散文和游记显示了赫胥黎合乎情理的悲观主义,那种几乎让人受不了的清醒。小说和诗歌却显示了他创作上不可救药的贫乏。怎样评价这些忧郁的作品呢?不是水平不够,不是愚蠢,不是特别乏味,只是毫无用处。它们引出(至少在我身上)无穷的困惑。只有某些诗句除外,例如这一句,关于时间的流逝的:
创伤是致命的,然而是我自己的。
诗歌《杂耍剧场》模仿了勃朗宁,短篇小说《蒙娜丽莎的微笑》想写成侦探小说,都或多或少让人看出了他的意图。尽管作品算不上什么,但让我看出它们想成为什么。这一点我倒是感激的。这本书中的另一些诗和另一些短篇小说,我甚至无法猜测为什么而写。因为我的行当是理解书,所以极其谦卑地作此公开声明。
阿道司·赫胥黎的名声我一直认为是过分的。我知道他的文学,就是那种在法国自然地生产而在英国带点做作地生产出来的文学。有些赫胥黎的读者没有感觉到这种不舒服,而我始终有这种感觉,从他的作品中我只能得到一种不纯洁的乐趣。我觉得赫胥黎一直在用借来的声音说话。
黄锦炎译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托·斯·艾略特*
“圣路易斯布鲁斯”的不可思议的同胞,托·斯·艾略特一八八八年九月出生于神话般的密西西比河畔的圣路易斯这个精力充沛的城市,是有钱的商人和基督教徒家庭的孩子,在哈佛大学和巴黎念过书。一九一一年回美国,修学热门的心理学和玄学。三年后去英国。在那个岛国(最初也曾犹豫过)找到了他的妻子、他的祖国和他的名字;在那个岛国发表了最初的散文—两篇有关莱布尼茨的技术性文章以及最初的诗歌《大风夜狂想曲》、《阿波里纳斯先生》和《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在这些处女作中,拉弗格对他的影响是明显的,有时是致命的。作品的结局缺乏生气,但某些形象却异常清晰,例如:
我要成为一双粗壮的巨爪,
飞快地插入那宁静的海底。
一九二○年,他发表了《诗歌集》,也许这是他的诗歌作品中最参差不齐、风格不一的一本,因为—收入了绝望的自白《衰老》和写得很一般的《局长》、《大杂烩》和《蜜月》—犯了生造法语的毛病。
一九二二年发表了《荒原》,一九二五年发表《空心人》,一九三○年发表《圣灰星期三》,一九三四年发表《磐石》,一九三六年发表《大教堂凶杀案》,题目很漂亮,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第一部博学而晦涩,曾使(现在仍使)评论家们不知所措,但比晦涩更重要的是诗的美。再说,这种美的感受是先于任何评论而且是不取决于任何评论的(对这部诗歌的分析有很多,最谨慎、最中肯的要数弗·奥·马西森在《托·斯·艾略特的成就》一书中的分析)。
艾略特像保尔·瓦莱里一样,有时在诗歌中表现出阴郁和无能;但像瓦莱里一样,他是一位堪称典范的散文家。他那部《散文精选》(伦敦,一九三二年)囊括了他的散文精华。后来出版的那部《诗歌的用途与批评的用途》(伦敦,一九三三年)则可以忽略而无伤大雅。
《磐石》(第一段齐诵):
鹰在苍穹之巅展翅翱翔,
猎人和猎狗群围成一圈。
啊,有序的星群不断轮转!
啊,固定的四季周而复始!
啊,春与秋、生与死的世界!
思想和行动的无穷循环,
无穷的创造,无穷的试验,
带来运动的知识,不是静止的知识;
是说话的知识,不是沉默的知识;
是对可道的认识,和对常道的无知。
我们的一切认识,使我们接近无知;
我们的一切无知,使我们接近死亡。
然而,接近死亡,不能使我们接近上帝。
我们在生活中失去的生命在哪里?
我们在认识中失去的智慧在哪里?
我们在传播中失去的知识在哪里?
二十个世纪来天宇轮回,
使我们离上帝更远,离尘土更近。
—托·斯·艾略特
黄锦炎译
*此篇初刊于1937年6月25日《家庭》杂志。
弗兰茨·卡夫卡《审判》
埃德温·缪尔夫妇刚把这本书写幻觉的小说译成英语(原文写于一九一九年,作为遗著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二年译成法语)。情节与卡夫卡的所有短篇小说一样,极其简单。主人公不知怎么地被一桩荒唐的罪案困扰,他无法查明告他的罪名,甚至不能与审判他的无形法庭相见;法庭则不经预先的审理终审判决他绞刑。在卡夫卡的另一篇小说中,主人公是个土地测量员,应召去一座城堡,但他始终无法进去,统治城堡的当局也不承认有这么回事。
在另一篇中,主题是讲一道一直没有送到的圣旨,因为人们在信使的路途中设置了障碍,还有一篇中,一个人到死也没能去走访一座邻近的小镇……谁也不会说卡夫卡的作品不是梦魇,就连作品的古怪的细节都是。所以,《审判》开头一章中抓住约瑟夫·K的那个人的紧身黑衣“有许多扣眼、纽襟、扣子、口袋和一条看上去很实用的皮带,尽管谁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的用途”。所以,审判厅那么低矮,挤满走廊的听众好像都佝偻着,“有的人还带来了大枕头免得头撞天花板”。
卡夫卡的感染力是无可争辩的。在德国,许多人用神学来诠释他的作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弗兰茨·卡夫卡对帕斯卡和克尔恺郭尔是很虔诚的—但也不一定非那样做不可。一位朋友给我指出了他那百试不爽又充满无数细小障碍的虚构作品的先驱:埃利亚学派代表人物芝诺,阿喀琉斯与乌龟的没完没了的比赛就是他创造的。
黄锦炎译
欧内斯特·海明威《有钱人和没钱人》
一个文人想象出的一个为非作歹的人的故事不会是真的。写这个故事有时有两个打算。其一,想让这个为非作歹的人原本不是那么坏的人,而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穷人。他的胡作非为是社会造成的。其二,美化他故事里邪恶的诱惑力,并用轻松的笔法延长有关残忍的描述。如同我们见到的,这两种手法都是浪漫主义的,它们在阿根廷文学中已有杰出的先例,如爱德华多·古铁雷斯描写粗犷的大自然的小说和《马丁·菲耶罗》……海明威在这本书的开头几章,似乎并不在意这两种尝试。书中的主人公,基韦斯特的船长哈里·摩根和同名海盗一样为非作歹。后者袭击了坚不可摧的巴拿马城,还给总督送去了一支手枪,作为足以征服那座要塞的炮兵的象征……海明威在小说开头几章,没有令人吃惊地叙述种种野蛮行为。他的态度是中立的、无动于衷的,甚至有些厌恶。他没有着重描写死亡。哈里·摩根不忍心杀一个人,他以此为荣,且不后悔。看了刚开头的一百页后,我们认为叙述者的语气与被叙述的事件是一致的,与纯粹的吓唬和哀怨保持着相等的距离。我们认为,我们正面对一部由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人写的作品。他还写过《永别了,武器》。
小说的最后几章毫不留情地让我们看清了事实真相。那些用第三人称写成的章节向我们做出了奇特的披露。对海明威来说,哈里·摩根是一个堪称楷模的男子汉。海明威向“垮掉的一代”展示屠杀的目的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样的小说只能使人感到沮丧,在我们心中连尼采式的寓言的寓意也没有留下。
接下去,我翻译了一小段小说,内容是在美洲进行的自杀。
“几个人从办公室的窗口向下跳,其他的人安静地在车库里向两辆轿车走去,发动机已开动。另一些人则采用传统的方法—使用柯尔特或史密斯威森自动手枪……这些制造得那么完美的武器,只要手指一按,就可以结束人们的内疚,消除失眠,治愈癌症,避免破产,替处于难以忍受的境地的人们找到一条出路。这些值得赞赏的美国武器携带方便,效果可靠,专门用来结束一场变成噩梦的美国梦,除了家里人对身上的血污得进行一番清洗外,没有其他不适合之处。”
徐尚志译屠孟超校
威廉·福克纳《野棕榈》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写过小说形式史,或者说小说形态学史。假设有一部这类公正的历史书,当中肯定会突出威尔基·科林斯、罗伯特·勃朗宁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名字。当然,也会以显而易见的公正突出威廉·福克纳的名字。科林斯开创了由小说中的人物叙述故事的方法。勃朗宁的叙事长诗《指环与书》分十次,通过十张嘴和十个心灵,细腻入微地描述了一桩罪行。康拉德让两个对话者逐步猜测和编织第三者的历史。同儒勒·罗曼齐名的福克纳是少有的几位注重小说形式和人物结局及性格的作家。
在福克纳的代表作—《八月之光》、《喧哗与骚动》和《圣殿》—中,技巧总是必不可少的。但在《野棕榈》里,他的技巧与其说吸引人,不如说使人不适;与其说有理,不如说使人发闷。这本书包括了两本书和两个并行但相悖的故事。第一个故事—《野棕榈》—讲的是一个男人被淫欲送进坟墓;第二个故事—《老人河》—讲的是一个目光无神的青年企图抢劫火车,在监狱里度过漫长岁月之后,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给了他无用、残酷的自由。第二个故事相当精彩,当中总是以大段的篇幅一次又一次地插入第一个故事。
毋庸置疑,威廉·福克纳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为了与此相一致,我认为,《野棕榈》是他作品中最不理想的一部。但是,就是这部著作(如同福克纳的所有著作一样)中也有描写深刻的章节。他的能力远在其他作家之上。
徐少军王小方译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
乔伊斯的最新作品*
《孕育中的作品》终于呱呱坠地,这一回的名字叫《芬尼根的守灵夜》。据说,这是在文坛不懈耕耘十六年之后得到的成熟且光彩照人的果实。我不无困惑地读完它,发现了九至十个并不能愉悦读者的同音异义词的文字游戏。我还浏览了《新法兰西杂志》和《时代》周刊文学副刊发表的令人惶恐的赞扬文章。高唱赞歌的人说,乔伊斯发现了如此复杂的语言迷宫的规律。但他们拒绝使用或验证这些规律,甚至就连分析某一行或某一段都不愿意。我怀疑,他们实际上同我一样困惑不解,也有无用、片面的感觉。我怀疑,他们实际上是在偷偷等待(而我则公开宣布我在等待)詹姆斯·乔伊斯的权威译员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作出诠释。
毋庸置疑,乔伊斯是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也可以说,是最好的作家。在《尤利西斯》里,有些句子和段落不比莎士比亚或托马斯·布朗的逊色。就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里,有的句子也是值得记诵的(比如下面这句:在流淌的河水边,在此起彼落的水花上,是一片夜色)。在这部篇幅很长的作品里,效果是唯一的例外。
《芬尼根的守灵夜》把英语梦呓中的双关语串连在一起。很难说这种串连不是失败和无能。我毫无夸张之意。德语里的ameise是蚂蚁;英语里的amazing是恐慌。詹姆斯·乔伊斯在《孕育中的作品》中造了一个形容词:ameising,意思是蚂蚁引起的恐慌。还有一个例子,或许不太吓人。英语里的banister是栏杆,而star是星。乔伊斯把两个单词合二为一—banistar,把两种景象合并成一个。
拉弗格和卡罗尔玩此类游戏要高明得多。
徐少军译
*此篇初刊于1939年6月16日《家庭》杂志。此处略去《一个阿拉伯传说》一文,其中国王和迷宫的故事已收入小说集《阿莱夫》,见《两位国王和两个迷宫》一文。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