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批评家要越过作家去影响时代的趣味
2017年08月13日 13:58:40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在一团和气的当代文学圈,批评家与作者总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张定浩有时却给人以尖锐乃至严酷的印象。孟繁华说他“批评锋芒在当今批评家里罕有匹敌,他的直言不讳肯定会让一些作家心有顾忌”。

张定浩出生于1976年,现供职于《上海文化》杂志。著有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爱欲与哀矜》、《一种真实》、译著《我:六次非演讲》等。2016年凭借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获首届书店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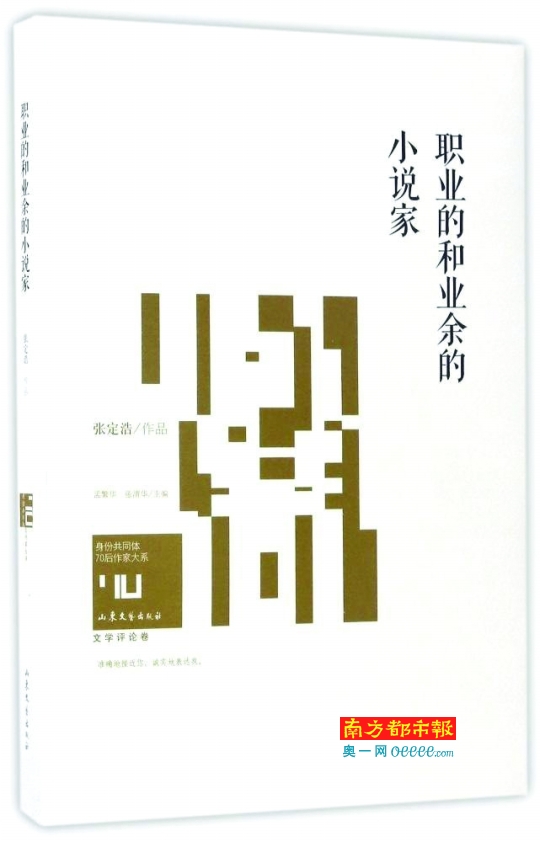
《职业的和业余的小说家》,张定浩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版,42 .00元。
在一团和气的当代文学圈,批评家与作者总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张定浩有时却给人以尖锐乃至严酷的印象。孟繁华说他“批评锋芒在当今批评家里罕有匹敌,他的直言不讳肯定会让一些作家心有顾忌”。他会毫不委婉地指出文本的缺憾,向世人暴露那隐藏的阿喀琉斯之踵。
张定浩的新书《职业的和业余的小说家》,收录近年来数十篇批评文字,对当代文学做近乎全景式的扫描,并在宏阔的视野和丰沛的理论支撑下,努力开辟个人洞见,不能不说颇具分量。
“引发我最初写下批评文章的动因,仅仅是某种作为普通读者对于文学批评界的不满。”张定浩在《批评的作用》一文里坦言。他把批评看作一种“自己可以从中获益的斗争”,“是对于整全的辨识、探寻乃至欲求。”批评者的职能是诚实地做出优劣判断,将作品恰如其分地置放入传统的序列,从局部照亮,进而获得关于文学的整体知识。
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拥有诗人的敏感、细致和善深思。诗歌和文学批评,都是密度极大的写作。这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令人敬畏的学者型诗人,塞缪尔·约翰逊、T .S .艾略特、约瑟夫·布罗茨基……并且让人相信,最好的批评无一例外来自写作者本身。他们通晓文学内部的奥秘,当他们谈论一个作家,或者“仅仅因为谈论他于我们有益”,或者为了通过谈论的对象消灭陈腐、破除定见,进而“影响这个时代的趣味”。
访谈
关于批评
南都:如果如你所说,批评是一个勘破黑暗的斗争,你觉得一个批评者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他在面对文本的时候,能否不存私心,毫无偏见?
张定浩:我说的批评,背景是文学领域,具体来讲就是文学批评,也被称作文学评论,或文论。这三个词,有时候被无意识地混在一起,但有时候也会被人有意识地区分。“文学批评”中的“批”,不是批林批孔的“批”,而是《庄子·养生主》里“批大郤,导大窾”的“批”,是以锋利之言辞切中作品肯綮的意思,其前提是透彻理解作品本身,如庖丁透彻理解牛。“文学批评”中的“评”,从其字形就可以看出,它要表达的,一是出自主观的议论,二是试图用某种公平的标准来比较高下,而说到标准和比较,就要有大量的同类样本作为基础。所以,“批”是如其所是的客观分析,“评”是主观与大数据结合之后的比较。
说到素质,就文学领域而言,像其他艺术领域一样,基本的素质就是才华和感受力,而在此之外,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写作者,他可能需要一点简单的思辨和推理能力,一点博览群书的耐心和一点点的诚实与勇敢。
私心是人性基本构成,“狠斗私字一闪念”并不能造就公正;所有的意见都是一种偏见。一个号称自己没有私心和偏见的批评家是很可怕的,这意味着他拥有最大的私心和偏见,就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一个文学批评写作者要做的,不是不存私心,是随时意识到自己的私心,并加以克服;不是毫无偏见,是努力比任何其他人更为严苛地审视自己的偏见。
南都:你怎么选择你批评的对象(作品和作家)?你觉得批评家和作家,文学批评和写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定浩:我会选择两种对象,一种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是我非常讨厌且觉得名不副实的,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个对象让我觉得尚且还可以有一点新东西要说。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有点像左手和右手,他们面对同一个世界,做的都是类似的工作,只是习惯和方向不同。批评家不是去指导作家的趣味,他是越过作家去影响这个时代的趣味。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写作,其次,它是一种密度更大的写作。
南都:你提到两种批评家,一种是“餐具狂”,“用齐泽克来搅拌余华,用德勒兹来剖析孙甘露,用萨义德来盛放《小团圆》”,一种是“餐具憎恶者”,“手抓食物并做出有煽动性的表述”。你自己属于哪一类?
张定浩:我是前来赴宴的客人,对美食的兴趣大于餐具,对交谈的兴趣大于美食。
南都:你从事文学批评多年,最大的成就感在哪里?是否觉得自己曾经“照亮”或“发掘”了文学地图的某一部分?
张定浩:在线下线上的某个角落,见到(听到)陌生读者提及我文字里的判断,说这正是他一直想说而未说的。我无意做浪漫主义的“灯”或现实主义的“挖掘机”,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自己是某种填充物,抛掷在文明的过去和现在不息的裂缝之间。
关于小说写作
南都:最近和一些作家聊天,有人认为当代小说写作者普遍文体意识淡薄,甚至还不如西方小说刚刚大量译入的八十年代。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定浩:文体并不是一件从没有人穿过的新衣服,甚至它也不应该是一种意识,过去文艺理论有句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这里的“风格”(style),无论从英文还是法文来看,和“文体”都是同一个词,只是新旧译法不同。文体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作家本人,而不是作家此时此刻为了创新或求异而找来的时尚外套。在这个意义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写作者们所谓的文体意识,其实只是一种时尚意识,至于今天的小说写作者,相对八十年代而言,我觉得不是文体意识淡薄,只是曾经的时尚成为今天的基本款,相对而言就不引人注目罢了。文体如人,千人千面,如果仅仅把文体等同于在叙事形式上搞点结构主义的小花样,那就好比认为唯有身着奇装异服者或行为艺术家才是人,似乎多少有些荒唐。
南都:你在《今日先锋何处寻》一文提到,埃科主张“同时面对精英和大众写作”,而在中国,作家们却是“面向文学期刊写作”,这个造成了当代文学的千人一面。对一个青年作者,如何才能避免均质化的影响?在中国,“同时面对精英和大众”是可能的吗?
张定浩:诚恳地面对自身,为己的写作,这大概是唯一能避免均质化影响的方式。为什么在中国“同时面对精英和大众”是不可能的呢?我觉得就人性的层面而言,中西古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如日月,是不加拣择,同时面对所有人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面对大众和畅销是两回事,大众也不等于庸众,有一千个陌生人排队买你的书,和有一个陌生人认真在灯光下读你的书,对我而言它们的意义和重量并无二致。
南都:你曾多次撰文谈到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问题。你个人更倾向于哪一种体裁?为什么中国极少博尔赫斯式的,而更多是欧·亨利或莫泊桑式的短篇小说家?
张定浩:我自己并不写小说,所以谈不上写作的倾向,如果从阅读的角度来讲,令我产生倾向的也不是小说的体裁,而是写小说的那个人。在博尔赫斯那里,作家首先是一个被全部过往文明洗礼过的完整的人,而对欧·亨利和莫泊桑而言,写作是博取尘世声名的一种方式,虽然可能也是艰苦的方式。
南都:你的新书起名叫《职业的和业余的小说家》,“职业”和“业余”,这二者应做如何区分?
张定浩:“职业的”和“业余的”这两个词,在很多领域,有着不容混淆的坚定意义:“职业的”意味着精湛的技艺,一生悬命的事业;“业余的”则意味着外行的粗率,和闲时为之的兴趣。每个业余爱好者若是遇到职业行家,他会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畏惧和敬重,这畏惧和敬重并非总针对眼前这个人,但无一例外会针对这个人所承载的那门深不可测的技艺,并且,就他喜爱的这门技艺而言,业余爱好者都渴盼自己的技艺能够达到职业行家的水平。
但唯独在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职业的”和“业余的”这两个词的指向则充满了混乱,这混乱,归根结底,源于这两个词的具体使用者的混乱。如今,很多缺乏资质的写作者被唤作职业作家,而很多好的作者确实只是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更何况,在文学领域,人们总是赞许天才而非匠人,写作的极境似乎是妙手天成而不是殚精竭虑,这种种结果,使得“职业的”这个词变成一个讨厌的敏感词,写作者避之唯恐不及;而“业余的”则变成一面奇妙的挡箭牌,多数写作者都愿意受它的荫蔽,因它既能挡住来自写作这门技艺(倘若它称得上是一门技艺)严峻的职业叩问,又不妨碍享受来自这门技艺的种种光照和掌声。
聂卫平讲棋时,见到棋手下出非常糟糕的着法,喜欢说一句口头禅,“这不是围棋”。我很喜欢他这个说法,也许这个棋手已经是职业九段,也许这盘棋最终他会获胜,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曾经有几步着法“不是围棋”的事实。“这不是围棋”,这句话里蕴藏着一门技艺超越胜负的职业尊严,同时也能令业余爱好者获益良多。“职业”中有荣耀,“业余”中有谦卑,我相信任何技艺皆是如此。知道何谓伟大小说固然重要,但对普通读者而言,更切身的是知道何谓“职业的”小说家,何谓“业余的”小说家,就像一般围棋爱好者,他与其把心思放在辨识职业九段和超一流棋手的不同上,不如先把职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差异搞搞清楚。
关于诗歌及其他
南都:你在《上海文化》杂志社做编辑,编辑的角色,是否自然地锻炼出一双“批评眼”?
张定浩:我觉得恰恰相反,是应该先有了文学批评的眼力,才有可能胜任做文学批评刊物的编辑。做这个编辑工作,充其量能督促我去关注同时代的写作。
南都:你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写诗和写文学批评之间,感性和理性思维如何切换?你更喜欢诗人和批评家之中哪一个角色?
张定浩:写诗和写文学批评,都既需要感性思维也需要理性思维,它们之间不需要切换。需要切换的是写作对象,诗是写给那些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看的,文学批评更多是写给伍尔夫意义上的普通读者看的。
我不能说我喜欢哪个角色,因为我既不敢自称什么诗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批评家,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可能写诗所带来的幸福感会比写文学批评时稍微强烈一点。
南都:上海的作家引人注目的很多。尤其这几年,金宇澄的《繁花》、吴亮的《朝霞》、王安忆的中篇《乡关处处》,都以上海为背景。这个城市似乎能哺育出特殊的文学,它对于写作者是否具有特殊的魅力?
张定浩:这三位作家我都写过专论。如果说这个城市哺育出某种特殊的文学,我想它可能意味着一种自由的文学,或者说文学的自由。在这个城市,没有中心,没有主流,也就没有所谓反抗和斗争,大家各安本分,各行其是,同时又不闭塞,没有夜郎自大的危险。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