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交换并不总是平衡的,收礼有时比送礼更代表声望
2017年03月27日 11:43:07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阎云翔
礼物的不对称流动司空见惯,尤其是在等级性社会关系背景当中。在许多情况下,非均衡的送礼牵涉到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因而产生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声望。
《礼物的流动》是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得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的成名之作。作者在黑龙江省一个农村生活了七年,并为撰写本书又两度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阎云翔在更新了传统人类学关于礼物交换问题的经典解释理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制度化”的特点,并探讨了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
本文节选自本书第七章《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有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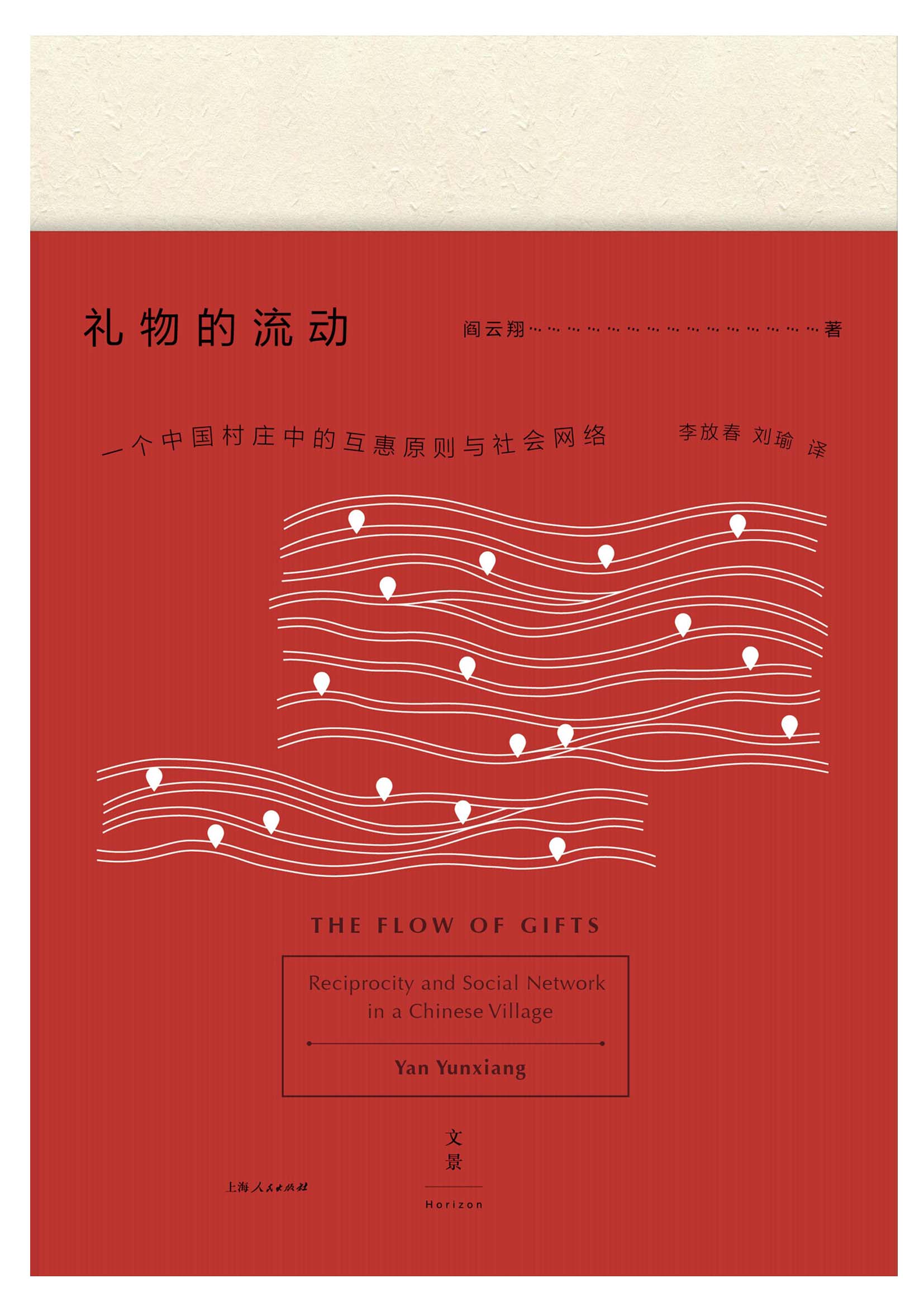
《礼物的流动》,阎云翔 著,李放春、刘瑜 译,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
尽管表达性和互惠性在人情文化的创建方面占据着突出的位置,然而下岬村民的礼物交换却并不总是平衡的。礼物的不对称流动司空见惯,尤其是在等级性社会关系背景当中。在许多情况下,非均衡的送礼牵涉到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因而产生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声望。
大多以往研究的结论认为,是赠礼者通过将收礼者变成债务人而获得声望和权力,因而在非均衡的交换中,礼物通常是沿着社会等级向下流动。葛里高利进一步断言,赠礼者的优越性是“全世界礼物交换体系的共同特征”。
然而,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体系呈现出与这些早期结论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礼而不是送礼被认为是声望的象征。在某些情况下,礼物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向上单向流动,而收礼者仍然保持着对赠礼种类型的非均衡互惠:一种源于家庭的发展周期,另一种源于社会地位的鸿沟。
礼物交换的不均衡
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许多村民抱怨随礼太多,令他们不堪重负。抱怨随礼开销太大的同时,他们又试图向我表明他们并不小气,相反,他们十分懂人情,在随礼时总是力求慷慨。结果,一半以上的下岬农户一年需要在随礼上花费500元甚至更多。谈到随礼上的经济负担,大多数村民坚称他们送出的礼要比收到的礼多。
如果这么多的村民送出的礼比收到的礼多,那么这些礼物流向了何方?换句话说,有没有人收到的礼比送出的礼多?据普通村民所言,答案是“有,是干部”。他们把最近随礼风的兴盛归因于干部们的居心不良。下岬的一个教师说:“现在人们想方设法操办各种典礼,从中收礼,报纸上对‘送礼风’批评得越多,它刮得越厉害,为什么?因为这阵风是从上而刮下来。所有这些新风气是干部们和上面的其他人制造的,因为他们可以收礼,不用考虑回礼。”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然而,当我向村干部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却全都否认他们曾经不回礼。一个干部坚称:“那会使我显得像个不知羞耻、不懂人情的人,没有人愿做这样的傻事,损害自己的名誉。”然而一些地方干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抱怨他们的上司:他们向乡里的或县里的国家干部送礼,但那些人却不回礼。
受访者含混而矛盾的回答给了我很大启发,并引导我就礼物交换的平衡问题做了一项特殊的调查。我发现礼物的不对称流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家庭发展的周期和社会地位等级。前者是每个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过程,下岬村民们对此并未特别关注。后者只在收礼者和送礼者社会地位悬殊时才引起不对称的送礼,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人(大多是干部)确实只收礼而没有尽回礼的义务。
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家庭的发展周期可能引起礼物的非均衡流动。分家后,年轻夫妇需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他们自己的小家庭,他们也得判断要和谁建立长期的礼物交换关系。由于在孩子长大前,他们操办仪式的机会不多,至少十年内,他们只能涉身于单向的随礼。在这期间,年轻的夫妇是注定的送礼者。而且由于人际关系在长时期内可能发生的变迁,他们的一些礼物会得不到回礼。每个家庭都要经历这个时期,但有些家庭要比其他家庭承担更多的风险。如果一个人想在村里出人头地,他就需要尽可能大的社会关系网,因此,他必须冒险给那些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许也不会再有礼物交换关系的人随礼。
在家庭发展的最后阶段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如果一对老夫妇在分家后独成一户,他们必须偿还家庭发展早期所欠的礼债,却难得有机会为自己操办仪式,除非是子女们为他们操办寿宴(据有些村民所言,在随礼中讨回“债务”正是近年来过生日越来越重要的原因)。结果,虽然老年夫妇也从子女那里收到孝敬礼,礼物还是从那些老年家庭单向地流回网络中的其他家庭。
因为随礼与家庭庆典密切相关,单身汉和没有孩子的夫妇也被迫处于单向送礼者的位置。这里单身汉是指30岁以上并独立门户的未婚男子。1991年,下岬村有九个单身汉和三对没孩子的夫妇。此外,有三个30岁以上、将来也不太可能结婚的单身女子,但她们都要么与父母要么与兄弟住在一起,在社会生活包括礼物交换中没有自立门户。这九个单身汉不得不参与亲友的随礼仪式,而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操办家庭庆典的机会。一个62岁的单身汉告诉我,过去30年中,他已经参加了上百次的礼物交换仪式(每年3—4次),但他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回礼。他解释说,他努力把参加仪式的数目压缩到最小,但仍然不得不参加其中一些,比如侄子的婚礼或邻居生孩子的庆典。没有孩子家庭的情形也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理由操办任何家庭仪式,却仍然不得不给近亲们随礼。这些人实现平衡互惠的唯一途径是从礼物交换的循环中撤出来,但这反过来会削弱他们在村中本已低下的地位。除了给亲属随礼的义务,日常生活中物质扶持的需要和精神归属的需要,也驱动单身汉和没孩子的夫妇在礼物交换的博弈中充当着永久的送礼者。
在特定环境下,地位差异会构成打破礼物流动平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在第3章,我讨论了称为孝敬的礼物,它是年轻一辈向老一辈送的礼,不求回赠。事实上,在代际馈赠中,相反的流向是不合理的。这样的送礼象征着年轻人对老人的感激和尊敬,因此,一个人收到的礼物越多,他就越荣耀。老村民常常展示他儿子(女儿、侄子或其他小辈)近期送来的礼物,并乐于听见别人的溢美之辞。在这方面,礼物的单向流动以象征的方式再现了两代人之间的辈分差距。
公共生活中单向的、向上的送礼也存在于下属和上级之间。据一些老人们说,1949年以前,亲属网络之外的礼物交换很少见,很少有村民与外界的大人物有关系。最通常的上下往来是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所有的受访者都说,在庆典性的场合或农历新年期间,佃农要给地主送礼以表达敬意。然而,地主通常不直接回礼,但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向佃农提供好处,比如收获之后允许佃农的孩子们拾庄稼,或在年终举办一场酒宴。当佃农操办仪式时,地主可能派个代表来送礼;他一般不会亲自来,除非双方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村民用面子上的差异来解释仪式上地主的缺席。他们告诉我,地主的面子比佃农的要大,所以即使是地主派人送来了礼物也已经被视为荣耀了。除了地主–佃农的关系,日常生活中还存在一种村民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上下关系。但地方官员很少卷入村庄生活,所以只有一小部分村民涉身于与低层官员的礼物交换关系中。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官员属于一个高不可攀的世界。
1949年后,尤其是在集体化时期(1956—1982年),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制迅速替代了社会生活中亲属关系的支配地位。下岬村的等级体系包括六类等级群体,干部处于顶端,所谓的四类分子处于底层。
这个新的社会等级体系对礼物交换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是,在公共生活中,单向的、向上的礼物交换变得更精致复杂了。与革命前的实践形成对照,由于国家对村庄生活渗透的强度和干部权力日常往复的运用,单向送礼的新模式涉及几乎所有的村民。单向的送礼有三种形式:(1)村民送给干部,(2)低层干部送给上级,以及(3)村民送给城里的亲戚。这种非对称送礼的新形式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社会等级中的单向馈赠
许多受访者回忆,当干部操办家庭仪式时,几乎所有的村民都通过随礼来致意,哪怕并不是每个人以前都与干部有礼物交换的关系。但当村民们操办仪式时,却只有那些与干部有密切关系或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才能指望得到一份回礼。许多普通村民只能希望干部们参加仪式后的宴席,而不指望收到礼物。考虑到集体化期间礼物价值的低廉(五角到一元),以我之见,干部们在乎的主要是收礼本身而不是礼物的经济价值。
集体化时期单方的向上送礼不是强制性的,看起来是群众出于自愿而随礼。其中的奥妙在于,大多数情况下,村民们操办婚礼或其他庆典时,不会向干部发出邀请,尽管他们以前曾给这些干部送过礼。通过这种做法,他们帮助干部避免了回礼的压力。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农村社区,关于家庭仪式的消息总是不胫而走,干部们会轻易地得知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干部想与其下属发展亲密的关系,即使没接到邀请,也能来随礼。换言之,这个机制是牺牲普通村民的利益来保护干部的面子。
此外,意识到这种送礼背后的驱动力,干部并不把自己作为负债人来看待。与革命前的地主或其他庇护人不同,干部们并不以直观的方式回礼,对村民与他们自己之间交换的盈余亏欠故作不知。在第6章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形,那就是“赵大面糊”与林副书记之间的纠纷。尽管赵多年来一直给林送礼,当赵给儿子办婚事时,林却没有回礼。正如一些村民所说,林也许根本没把赵以前送的礼放在心上,因为他从下面收到过太多的礼。我曾经问一个朋友,为什么他再婚时,礼单上的客人明显减少,我想知道这是否与再婚的性质有关。他把我的猜测视为无稽之谈,并告诉我他1977年第一次结婚时,他的哥哥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许多人不请自来参加他的婚礼。其实不是冲着他来,而是为了讨好他的哥哥。这些客人在他1985 年再婚时就不再来了,因为他哥哥在包产到户的改革过程中下台了。我问他如何给这些客人还礼,他说:“对那些势利眼,我给个屁!谁理他们!他们不是我的人情,我不会对别有用心的礼物负责。”在这个例子中,好几十个人同时丢掉了他们的礼物和社会信誉。
我抄礼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否定性互惠”事件,即一方收到礼物但不履行回偿义务的情形。在这个例子中,一个普通村民送了五元礼金给干部,这一点被记录在后者1979年的礼单上,但我在这个村民1989年的礼单上却找不到来自那个干部的回礼记录。当我在闲聊中向这个干部和他妻子暗示他们未曾回礼时,他妻子解释说,因为两家在1979 年以前没有随礼关系(这是在暗指那个村民送礼的动机是巴结干部),又因为那个村民家的仪式是在十年后办的,所以她忘了回礼。后来,她又辩解说,在那个村民给她家送礼前,她丈夫帮了他不少忙,所以他才送礼表达谢意,还人情债。不管原因是什么,这里的潜台词都是,“不回礼无所谓”,这反映了干部对村民的态度。
作为村民与干部之间礼物非均衡流动的结果,村干部通常拥有最广泛的私人关系网络,操办最奢华的庆典。包产到户和其他改革实行以后,干部对资源的垄断权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一些村民不再给他们的领导送礼。饶有趣味的是,由于权力关系和政治环境的变迁,近年来干部们越来越关注与村民们搞好关系,并更留心在礼物交换中回赠礼物。然而,随礼者数量上的差异仍然存在,这生动地展现出村民与干部之间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差距。根据我1991年的调查,普通村民的仪式上,送礼者的数量从不到100人到200 人不等,与此相对照,参加干部家仪式的客人数量却往往超过300人。
第二种单向送礼的形式出现于干部们之间。也许是由于政治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上级的影响力,向上送礼的习俗在传统中国的官僚体系内部流传已久。一个民间传说也许能反映出,在公众的印象中,官员们是如何向上送礼的。传说一个县官的生日即将来临,衙门中的官员们会聚一堂,商议应该向他们的上级送什么样的礼物。最后,他们中最聪明的一个官员提议:“既然县官是鼠年生的,干吗不送他一只金老鼠作生日礼物?”他们纷纷表示赞同,并送了一只金老鼠给县官。县官笑逐颜开,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下个月我要庆贺我老婆的生日,她属牛。”
以村干部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出,干部间的送礼同时沿着纵横两个方向进行。如果一个干部想保持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就不得不参加与其他村同级干部进行礼物交换的横向交换圈。因为这些礼物是在地位相近的同事间交换,通常互惠是均衡的。不过,由于频繁的职务升降,一些离开权位的干部可能会不履行先前的义务,从交换网络中退出。毕竟,这些网络严重地依赖于暂时的政治联盟,这意味着在同级干部间仍然存在很大的礼物单向流动可能性。
毋庸置疑的是,在村干部和乡干部(偶尔涉及更高层次)之间存在着单向送礼。这可能会采取两种形式。近年来,村干部以村委会和村民的名义给他们的领导送礼已成为一条心照不宣的规则。据受访者所言,过去十年中的每一年,成百上千斤的鱼、肉、精米被送往乡政府主要领导的家中。这被当成公事来办,而村民们会被召去运送礼品。村干部解释这件事的堂皇之辞是,群众理解他们的领导如何为公事鞠躬尽瘁,因此他们愿通过微薄之礼聊表谢意。事实上,村民们指出,这种送礼与群众没什么关系,干部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与他们的上级搞好私人关系。
纵向送礼的第二种形式存在于仪式交换中。正如村民们对他们的领导所为,村干部也在乡干部或更高级别的上级举行家庭仪式时向他们送礼,但不指望回礼。比如,我们在第5章分析过的村支书韩告诉我,1990年他算了算自己在随礼上的花销,总共是2600多元,这与其他家庭相比是高得惊人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向上随礼。据韩所说,自从他1981 年当了下岬村的主要领导,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乡政府和其他村的干部随礼。但当他为二儿子举办婚礼时,只有低级别干部来参加。他强调他没有向乡政府的干部发出邀请,因为他不想提醒他们对下面的责任。然而他的上级在自家操办庆典时却从来没有忘记通知他和其他低层同事。他回忆说他参加过现任副县长儿子的婚礼;这场婚礼持续了四天,第三天是专门留给来自全县的村级干部的。在宴席上,他和好几个朋友自嘲道,他们是被召来赞助副县长家的庆典了。
有时,干部间等级化的礼物馈赠可能会采用一种更具强制性的形式。在一个我所目睹的例子中,下岬村长大的退休干部苏先生,正式邀请下岬的五个干部到乡里来参加他小儿子的婚礼。据受访者所言,苏明显居心不良——他想积聚财礼、炫耀名声,因为苏早在50年代初期离开下岬村后就不再和村里大多数人保持随礼关系。“这个人对人情一窍不通,”一位受访者说,“不管他当了多大的官,他不该忘记他的老家和同乡;此外,以前和我们没有往来和好感情,他怎么能想起要让我们给他送礼?但他就这么做了,真是恬不知耻!”
不过,抱怨归抱怨,他还是决定参加婚礼并送分内的礼。为什么?他告诉我,苏的二儿子现在在乡政府中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拒绝邀请是不明智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表示轻蔑的信号。“那是最坏的结果,你知道,与上级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保住饭碗的关键。”
这个受访者不是唯一做出理性决定的人——所有其他村干部都做了同样的事,希望以此保持与苏的二儿子的良好关系。显然,把社会等级纳入考虑之后,双方都做了理性计算。一方面,当苏向以前并无随礼关系的村干部们发出邀请时,他已经考虑到二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村干部们做出了同样理性的反应,使博弈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们把握住了与上级(苏的二儿子)培养关系的时机。但与此同时,他们抱怨苏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情感上的不满,并为自己的举动辩解。
除了村民–干部、干部–上级间的关系,还有比较隐蔽和少见的等级化随礼。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激进时期,那些四类分子在礼物交换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事实上,他们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不敢公开给阶级成分好的村民或干部送礼,因为他们可能被指控为企图腐蚀后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不送礼可能被理解成对以往礼物交换关系的否认或对人情伦理的侵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通过秘密渠道,事先向仪式的主人捎个信,问清他们是否应该参加仪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们的礼物被当众拒绝,尤其如果主人恰好是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的话。1966年,一个地主子弟成分的人参加了他侄子的婚礼。他的礼物被当场拒绝,主人谴责他企图腐蚀革命村民。在下岬,公开的拒绝礼物仅此一次。随礼关系中这种内在的紧张对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这些成分不好的人举办婚礼或葬礼时,他们也担心政治上的麻烦。他们以前送的一些礼绝不可能得到回礼,因为革命家庭中的人可能想与他们断交。由于他们举办家庭仪式的合理性都变得可疑,所以四类分子中很少有人还关心礼物的平衡问题。一个嫁给地主儿子的妇女告诉我,结婚那天去她丈夫家的路上,他们的婚车正好被一支批斗四类分子的游行队伍堵住了。她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的公爹是不是正在挨斗,这又会不会影响她丈夫。得知这批人来自另一个村后,她又转而担心她的婚礼,她说:“那时候,我只希望婚礼能平平安安地办完,谁敢想到礼物?我特别感谢那些来参加婚礼的人,但我也不怪那些不来的人。至少,谢天谢地,没有人来扰乱我的婚礼。”
由于政府对城乡迁移的限制和城乡间巨大的不平等,当村民们与城里的亲戚交换礼物时,村民们也处于不利的位置。一个村民可能以两种方式建立与城市的联系:(1)与那些在实行迁移限制之前搬到城里的亲戚保持好关系,或(2)由于女儿嫁给城里人而与城里人结成姻亲。无论哪一种情况,村民们都被看作低人一等,在送礼活动中,他们总是失多得少。一个村民抱怨,在他结婚前,他曾参加过三次城里侄子家的庆典,但他1971年举办婚礼时,他侄子却没来参加。为此,他感到十分屈辱,索性与侄子断交了。在另一个例子中,当村里的一个姑娘嫁给哈尔滨的一个工人时,她的父母原以为这会提高他们在下岬村的地位并为此而自豪不已。很快,他们发现在城里的亲家那儿他们并不受欢迎。当他们带着土特产礼物送给亲家时,后者却只给了他们一些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家庭用品—这些东西根本不能算是姻亲间恰当的礼物。
正如第2章概述的,社会主义等级制基于三类二元对立关系:干部与村民、城市与农村,以及红的与黑的(就阶级成分而言)。1979年以后,第三种对立已经取消了。经济改革已经削弱了干部权力,并缩小了城乡不平等,但这两种对立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持续存在。因此,反映着社会主义等级特性的单向送礼模式在下岬村仍然具有生命力,非均衡互惠仍然是礼物交换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