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狱文学:从柏杨获奖说到宋琬的监狱诗
2015年06月30日 09:34
来源:凤凰文化
中国是诗的国度,古代,特别是隋唐以后,只要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都学习过诗歌写作。传统中的监狱文学贯穿于整个诗歌史,要以诗人遭遇为考察的起点。
读《看,那个丑陋的中国人》,得知柏杨坐监狱时写的旧体诗获美国“国际诗人联合会”的“国际桂冠”奖,获奖通知说:“作家根据真实经验的监狱文学,其中充满坚定的指控和历史研究。”过去总以为《越狱》一类作品就是“监狱文学”,原来“诗人联合会”所认定的“监狱文学”,其作者应该是真正坐过监狱的人。这是定义“监狱文学”的第一个要件。
当今作家要写监狱生活,临时到看守所或劳改场假装“犯人”待个十天二十天,去体验一下“生活”就是很敬业的了。然而他们人在号子里,并不会有犯人心态,反而会有优越感。他也不可能以犯人的心态观察犯人和看守。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分析曾经的王侯将相,一旦丧失权力,进入牢房“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曾经的王侯将相,进了监狱就失去了原有的身份,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就是犯人;坐监狱愈久,犯人身份愈强固,这种身份意识和由此产生的心态,绝不是“体验生活者”所能获取的。
其二,所写的应该是监狱生活,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即使你是犯人,在监狱里写与监狱生活不相干的作品也不能称之为“监狱文学”。我坐监狱时,有位20 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在狱中写了一本反映家乡革命历程的小说——《悠悠资水》,他是以作家的身份写作的。监狱文学不仅对其所经历的监狱要有宏观的把握,更应有细节的描写,这样它才能进入历史。当然所谓的“细节”既是生活的细节,也包括人的思想情感的细节。
其三是应该具有批判性,如“获奖通知”所说的柏杨的监狱文学“充满坚定的指控”。像我们所熟知的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可以称之为“监狱文学”的经典作品。这两位作者都是监狱的在场者,伏契克还没有能够走出“在场”,他牺牲在监狱。在他们的描写中不仅有真实,也有分析批判,揭示形成作者笔下“真实”的原因。
一、古代文学创作中有“监狱文学”吗?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监狱文学吗?最初我想应该有,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有段名言: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虽然,司马迁说得比较笼统,孔子、屈原、左丘明、吕不韦也没坐过监狱,他们的著作,也不一定是“文学”,但其中有一点表述得很清楚,一个人如果受到冤屈,心有郁结,必然要设法抒发出来,古来最重要的著作大多是遭际不幸者写的。我想世间大约没有什么比无端堕入监狱更令人心情“郁结”了,这是不是更需要“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更需要文学创作以发舒呢?古代文学中
诗歌最有代表性,中国是诗的国度,古代,特别是隋唐以后,只要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都学习过诗歌写作。要考察传统中的监狱文学,首先要回顾诗歌史,要以诗人遭遇为考察的起点。
二、正义的见证
自古监狱人犯,品类庞杂,难以一概而论。最为人们关注的,是那些为了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志士仁人,他们多有监狱生活的经验,也都有文学作品传世。例如文天祥的《指南录》《指南后录》,夏完淳的《南冠草》,张煌言的《苍水集· 采薇吟》等,还有大量的为民族、社会进步而遭受迫害的人们,如谭嗣同、秋瑾、邹容……他们在狱中都有明志抒怀之作。这些名篇名句,以其精警动人而长期传诵,但我认为这些作品很难用“监狱文学”来概括。因为除了文天祥外,大多烈士在被捕或被俘后一般没有纳入诉讼系统,很快被害,像戊戌政变之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八月初九被捕,十三日就拉到菜市口开刀问斩,在狱中时间非常短暂。“六君子”中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三人都以诗名世,刘死前无诗,谭、林各有七绝一首,表现烈士视死如归的坦荡精神,谭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尤为有名。这些作品的意义超出了监狱,它们展示了人类为了美好理想奋斗的艰难历程,是人类正义事业的见证。
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关押三年,他所住的牢房是属于“兵马司”的,但其中并没有其他犯人,文是单独监禁,接触不到其他犯人。因此他虽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反映这段生活经历与这个时期的思想情感,但从中看不到当时监狱的一般情况。人们谈到文天祥也只记得他的《过零丁洋》(此诗写于文被俘后押解北上途中)、《正气歌》这些足以使“贪夫廉,懦夫有立志”的作品。其实他描写个人情感的《乱离歌》(模仿杜甫《寓同谷县作歌七首》)等更有震撼力量,真是一字一泪。在抵抗蒙元的战争中,他献出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整个家庭,他“二儿化作土,六女掠为奴”,可以想见被关押的父亲听到这些消息会有何等心情!他把这些都融入三年的羁押生活之中。在牢房中写诗是他迎接死亡之前每天必做的功课。
三、无可奈何的呻吟
与上述作品相对的是,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不甚光彩的或说罪有应得的人在监狱写的诗有时也会令人掩卷长思的。南朝宋范晔是个有才华和学识的史家,卷入了一场宫廷政变,企图搞掉宋文帝刘义隆,扶持义隆的弟弟刘义康上台,不料被人告密,下廷尉狱等死。宋文帝还念及这个侍从之臣,他有个白团扇,做得非常精致,叫人拿给范晔“令书出诗赋美句。晔受旨援笔而书曰:‘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上循览凄然”。连宋文帝这个“被害人”看了范晔写下的“美句”A,都很难过,不用说我们这些局外人了。范晔在狱中也赋诗为自己“送行”:“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尽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他最后的期待是在刑场上表现得洒脱一些,像临刑前还要弹奏《广陵散》的嵇康,或像慷慨赴死的夏侯玄那样。实际上,他也只是个常人,刚到刑场还能挺住,待“妹及姬妾来别”,则“悲泣流涟”,露出了凡人本色,被与他一起受刑的外甥取笑。我们读到这些,仍然不免令人唏嘘。
大名鼎鼎的和珅在乾隆去世后倒台,被清算,关押在刑部狱,在狱中有诗回首往事,丝毫没有一点觉醒,面对着“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得出的却是“怀才误此身”的结论,不禁令旁观者哑然失笑。还有一首七绝“五十年来幻与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日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睢口是睢水入黄河之口,为治黄关键地之一。和珅与“河神”谐音,死前还搞些装神弄鬼,更为可笑。大多作
奸犯科者进了“官法如炉”的监狱则日渐疲软,即使擅长写诗的,作品也少有昔日的光彩,只可视为秋虫的哀吟。
四、狴犴下的悲歌
古代社会是个人治社会,处理人犯多凭心裁,其中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古代狱讼,程序繁杂,案件只要纳入了诉讼系统,一般是延宕日久,三年五载,极为平常。监狱在中国,照鲁迅的说法是取法佛家地狱的,犯人在其中长期监禁,不死也要脱掉几层皮。清代有本诗选集,名为《清诗铎》是专选与民生苦痛有关的诗作,有一节名为“刑狱”,选诗五六十首,都是写监狱黑暗的。作者或是官员或是士子,并非犯人本身,但他们笔下的监狱也足以令读者胆战心惊的。那么,身处其境、又受到冤屈的犯人自然是满怀痛苦和愤怒,呼天抢地,会用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冤情,有文化的自然也会写诗。
(一)诗人命多舛
虽然“诗人少达而多穷”,但“穷”到坐监狱也不太多。唐代坐过监狱的有名诗人也就是骆宾王、沈佺期、李白、王维、储光羲、刘长卿等人。李白因为支持永王璘,卷入了宫廷矛盾,差点丢掉性命,坐狱、流放都曾经过,而且有诗记录;其他几位都与叛乱和重大政治事件有关,并非是因为写诗得罪。他们在监狱的时间不长,相关的作品也不多。宋代对文人士大夫比较优待,但两宋都有文字狱,这是文人士大夫之间内斗的产物。大诗人苏东坡因为写诗涉及“讥刺”,被新党控告而下狱,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称为“乌台诗案”。苏轼狱中也有诗作,如《狱中寄子由》第二首诗云:“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心似鹿”“命如鸡”一联,把狱中的凄凉无助、未决犯人心情的忐忑不安写得极为生动,千载以下,犹在目前。
(二)含糊的悲吟
清代史家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明初“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诗人更甚。明代开国之初,便以文字狱名世,这在历朝历代中还是很独特的。
有明一代成就最高的诗人高启以三十九岁的盛年就被腰斩于市,与他并称的“吴中四杰”皆以诗名世,他们中除了张羽投江自我了断之外,杨基下狱后死于劳改场,徐贲死于狱中。以咏白燕有名、被人们称作“袁白燕”的袁凯官拜御史,朱元璋搞严刑峻法,太子朱标再处理时,时有宽大,朱让袁评论谁是谁非。袁凯说:“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朱元璋认为袁两头都不得罪,太滑头,下狱。后侥幸释放,袁便装疯,得以善终。历洪武、永乐两代的“神童”解缙(即刘宝瑞说的“解学士”)因正直触怒永乐帝死在监狱。这些死于监狱的诗人留下的诗作却不多,是他们写了诗没能拿出监狱,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写,不知道。当恐怖弥漫了整个社会之后,人们变得彻底无声了。
明中叶的全能型的艺术家徐渭(字文长,徐文长的故事也流行于江南)因杀妻罪在狱中关了七年之久,他在狱中为官员写的字、作的画都有流传到现今的,独不见他在狱中写的诗编入集中,也很奇怪。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得罪权宦刘瑾下狱,他把《狱中诗十四首》编入自己的集子中,并注明“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锦衣狱作”。同时的“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四次入狱,或弹劾贵戚,或得罪权宦,有近百首狱中诗传世。读他们的监狱诗觉得很像阮籍的《咏怀》诗,其风格都是“情寄八荒之表”“作汗漫语”的,缺少具体的描写,这里举一首写得稍具体点的:
湫宇夕阴阴,寒灯焰不长。
气栖递微明,飘忽如清霜。
人云网恢恢,我胡寓兹房。
墉鼠语床下,蝙蝠穿空梁。
惊风振南牖,徂夜倏已央。
於邑不成寐,辗转情内伤。
但也失之笼统雷同,如果删去“人云”一联,看不出是描写“监狱囚禁”的诗。读明人的诗集感到明代是有监狱、无监狱文学的时代。
(三)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明清两代之政,鲁卫之间而已,文人的境遇也差不了多少,清代比明代多了一层民族压迫。清初满洲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刻意打压江南士人(这里反清最烈),连续发生“奏销”“科场”“通海”等大案,冤死者、牵连入狱者成千上万,这有点类似明初。明清不同的是,明代永乐之后,朝政走上正轨,单纯因为写作受到惩治和迫害的士人很罕见;清代则不同,满洲统治者对于汉族士人的警惕,贯穿始终(后来清代内政外交上举措失当,大多根源于此),特别是“康雍乾”的一百四十多年间,统治者强悍,很有管控能力,他们往往要深察到臣工和士人们的五脏六腑,常常因为语言文字兴起大狱,而且来得突然与恐怖。它好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一种恐怖气氛。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正是汉族文人终日惶惶然的写照。当然龚自珍写下这对名联时,文字狱高潮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如果这首诗写于乾隆时期肯定堕入文网。龚自珍生活的嘉道时期,极权统治已经疲软,统治者已经没有那么大精力和力气关照每个文士的一言一行了。
考察“康雍乾”三代,令人奇怪的是还有士人写作,犯忌敏感的文字也时有漏网;清代诗歌在艺术上开拓不大,但在内容上却格外丰富,增添了许多前代所没有的内容,特别是清初和清中叶以后。上面说到的一些有良心的官员士子关注到监狱的黑暗和被羁押人员的苦难就是一例。
对那个时代的士人我们应该怀有同情的理解,仅仅一个“庄史案”被杀的就有千余人,株连的上万,其中能写诗的文人不少,也有侥幸逃生的,但当事人几乎无人敢记此事,只有顾炎武在诗中悄悄地纪念优秀的史家吴炎、潘柽章等。后来顾炎武也陷入“黄培诗狱”,被关押了半年。他留下的狱中诗仅数首,也只抒发了入狱后的愤懑,很少对监狱本身做深入的描写。雍正时期最重要的文字狱案之一的查嗣庭案,嗣庭入狱死后还被戮尸,自然文字全毁。其堂兄查慎行是康熙间文学侍从之臣,又是著名诗人,致仕在家,已经七十八岁,也被株连入狱。慎行传世的集子编辑完备,但狱中诗也极少,仅有《诣狱集》一卷,在狱中作诗六十首左右,大多还是悔过感恩之作。汉族士人受迫害最严重的康雍乾时期,系统地、有意识地描写狱中生活,展示清代监狱实际情况,可以称为创作监狱文学者少之又少,但当时社
会气氛的压抑和恐怖只能曲折地表现出来。
明清之际,社会矛盾纷纭复杂,统治者对士人的管控有所放松,士风有个自由放任期,士人勇于正视人间苦难,并形诸诗文。清初著名诗人宋琬两度因冤入狱,写下了大量监狱诗,说明了这种士风未完全泯灭。
(四)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宋琬的监狱诗
宋琬是山东莱阳人,宋家是莱阳著名的乡绅。其父应亨是明代的官吏,死于抗清战争,很壮烈,崇祯皇帝为之“素服”并“深自引咎”。入清,宋琬入仕为官。清廷对他很有戒心(宋琬在清为官履历几乎与在明朝的父亲类似,可见朝廷记得那个“殷顽”宋应亨)。顺治间,宋琬两次入狱,虽然起因都是受人诬告,但案由都事涉谋反,可见朝廷对于这类家庭出身官僚的疑忌。
宋琬前后坐牢三年有余,他是个有心人,不仅在狱中写了不少纪实诗篇,而且还写了一个杂剧《祭皋陶》。自汉代以来皋陶是狱神,犯人入狱首先要参拜祭祀皋陶。《后汉书· 范滂传》言:“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坐系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宋琬就根据这个题材写了一出《祭皋陶》。此剧创作于狱中,其目的就是表达对“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宪”一类冤狱的感受。千百年来人们追求司法公正,把平反冤案的官员视作“青天”,希望求得光明,然而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人们毫无权利可言,司法公正只是一个梦想。
宋琬第一次出狱后还把狱中写作的诗歌五十六首编为一集,名《北寺草》。“北寺”指京师监狱,“草”指诗,“北寺草”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狱中诗,或监狱文学。
这次入狱在顺治七年(1650 年, 庚寅)的冬天。宋琬从南方调回北京任吏部主事,到京后即入狱。其自述入狱原因有“文字缠余孽”的句子,可知与文字有关。顺治九年(1652 年, 壬辰)正月出狱,在狱时间一年有余。第二次是顺治十八年(1661 年, 辛丑)族侄诬告宋琬兄弟“通贼谋反”,下刑部狱,于康熙二年(1663 年, 癸卯)十一月三日释放出狱,在狱两年。这两年的监狱生活较上次受的刺激更大,留下的作品更多(其“监狱诗”共有二三百首),而且其作品风格有了明显的转变,宋琬本来是以承继明代前后七子自命的,崇尚盛唐风格, 从狱中出来后,明显地转向学宋,从崇尚比兴转向注重写实的赋体。
宋琬用诗记录了那个时代诉讼与监狱的黑暗和恐怖,读之不寒而栗。入狱的前奏是被捕。第一次被捕的印象是惊恐与新奇:
刘雪舫馈泉酒赋谢
仓卒槛车征,骨肉成死诀。
幸荷国恩宽,未即赐臣玦。
待罪爽鸠庭,呼天口流血。
甲士月践更,刀镮俨罗列。
嫚骂谁敢嗔?供顿讵能缺。
充肠藜藿甘,伴寝锒铛热。
惊看肤已枯,空余骨未折。
捕快槛车上门,抓到狱中,任凭呼天抢地,招来的只是狱卒的叱骂和惩戒。每天面对的是难以下咽的牢饭和使人难以安眠的手铐脚镣。第二次下狱是在杭州浙江按察使A任上。逮捕他的是京城来的“缇骑”(缉拿人员),全家入狱。这次更是恐怖与悲惨。他在《九哀歌》写到一家妻小被逮现场:
九哀
有妇有妇勤耕织,薄宦驰驱到江国。
突如其来缇骑至,举家相对无颜色。
小臣系罪理所当,何意妻孥辕亦北。
一家大小,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傻了。这次诏狱是针对宋氏全家的。组诗《九哀》是写其全家的不幸。他的两位兄长全死于冤案,稍好一点的是仲兄死在全家被逮之前,而年逾花甲的大哥死于初入狱时,尸体被席卷而出:“仲兮衔冤发愤死,广柳车中一长恸;伯兮衰老遘谗贼,齿牙落尽眼复瞢。藁葬圜扉席作棺,刍车麦饭谁为送?死而为厉魂安归?披发叫天天欲动。”宋琬与伯兄相差十七岁,小时曾被兄嫂养育,失去丈夫的老嫂子被关在家中“菅麻久换绿罗裙,藿藜堪抵明珠颗。虽无儿女共牵衣,婢妾哀哀饥且裸”!早已出嫁而且守寡的妹妹也被牵连,破家亡产,两个儿子被卖为奴……
鲁迅说监狱:“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宋琬的监狱诗充分展示了这个地狱给他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苦难。《壬寅除夕作》写于第二次入狱一年以后的除夕:“木囊随假寐,铁索换垂绅。陆续冤谁雪?嵇康性已驯。粞糠充亚饭,藁秸捋重茵。雀角无完屋,鸰原已化燐。死应为厉鬼,痛欲彻高旻。邱嫂悬丝活,孤儿对簿频。踝枯还受榜,血溅不遑颦。履虎宁遗类,连鸡到比邻。事同朱并罔,狱与洛阳均。瘴隐层霄日,霜飞六月辰。隶人咸惨淡,法吏亦酸辛。”其自注“孤侄及同系诸人,每就讯,呼号震天,司谳为之悯默,吏卒有泪下者”。诗中的“木囊”四句写尽了犯人所受到的生理与精神上的双重迫害。陆续是东汉的洛阳官吏,被诬下狱,他身被“五毒”A,身体上受到极大痛苦。嵇康是魏末“竹林七贤”之一,是一身傲骨,极为自尊的士人,然而到了这种地狱似的监狱,如狱卒所说的,到了我这里,是虎也得给我卧着,是龙也得给我盘着。屈辱是敏感的诗人不能忍受的,但是看到寡嫂命如悬丝、孤儿(侄子)在狱中所受的肉刑以及这个案子牵连的亲朋好友,乃至街坊邻里(古代诉讼有个怪现象,证人也与犯人一样被抓到监狱关起来),他又不能不坚强地活下来,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宋琬诗中还描写了黑牢的具体情况。他的《狱中八咏》分别咏“芦席片”“煤土炕”“折足凳”“砂锅盆”“黑磁盌”“土火炉”“苦井水”“铃柝声”。其中“煤土炕”“苦井水”最能显示北京诏狱的特点。诗人在组诗中写到北方土炕和炕上的半片芦席与“象箪翡翠床”齐等,似是庄生的自我调侃,可是在《土炕成》一诗中写道:“欲破愁牢用火攻,融泥施锸罕人工。锒铛作枕铺牛荐,瓦缶为炉热马通。”自注云:“戴就下狱,薰以马通,不死。马通者,矢也。”这才是监狱的土炕,施工简单,不见砖石,只是用泥水堆就,再用火一烧,就成了炕,而用以加热的燃料竟是马粪,其环境可以想见。“苦井水”在京城一级的城市中大约仅北京存在,直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北京手工开凿的井大多也是苦的(有个别地方打出甜水井,往往用“甜水”为地名,如“甜水井”之类),市民仅作洗濯用,如洗衣服之类,人畜饮水要买甜水。失去了自由的犯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了。《苦井水》中写道:“病渴限重扃,寒浆汲辘轳。笑问江湖客,中泠胜此无?”披枷戴锁的犯人,又有重重监门的限制,即使是“病渴”(糖尿病)也不能随时喝到水,待狱卒送来的水是狱中的苦井水,可是在“病渴”的宋琬饮来,却美如甘露,如同天下第一泉——“中泠泉”水。这不是阿Q 式自我安慰,而是生活在狱中犯人的真实感受。坐了监狱的犯人,一切享受皆成虚幻,唯一还能实现的是对口腹的追求。“口腹”之求是可高可低的。渴极了,饿极了,充肠的藜藿、润口的苦水都成了人间美味。
北京的气候是冬天苦寒、夏日酷热,监狱里比外面更要翻倍。冬天有热炕还好熬一些,伏天最为难过。不仅闷热难挨,空气湿度大,各种爬虫诸如土鳖、蜈蚣、多足虫夜里极为活跃。他在《煮枕行》写到这些虫子“宵行昼简出,希踪狐与貉。伺我鼻息酣,分曹向阡陌。觉后鲜完肤,梦中频蹙额。痛痒难为状,罪浮于虿螫”。这些虫豸像狐狸一样,昼伏夜行,犯人睡觉时它们在人脸上、身上爬来爬去留下细微但痛痒难熬的创伤。这比披枷戴锁还难受。
清代北京较现在多雨,也多集中在五、六月,大雨一来势如滂沱。1963 年我经历过一次连下两周的大雨,连穿的衣服都发霉长毛。宋琬的《苦雨叹》写到连下“十旬”的大雨:“昔年癸巳长安居,冥冥大雨十旬余。彰义门中驾筏渡,千家百室无完庐。今年癸卯在西曹,灾蒸羁束方郁陶。银河倒注日复来,俄顷床足生波涛。”水漫室中,床飘浮起来了,这样的屋子怎么住?
鲁迅还说监狱负有“榨取人犯亲属的金钱,使他们成为赤贫的职责。而且谁都以为这是当然的”。冤狱榨取了宋家多少钱财,失考,但从宋琬变卖自己心爱之物来看,肯定不少。如《鬻帖》《鬻画》《鬻砚》《鬻觚》《鬻炉》《鬻字》《鬻磁杯》《鬻画屏》《鬻裘》《鬻帽》等诗所提及的变卖之物,大多是价值不菲的,其中不少还是稀世珍奇。康熙间山东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高度评价宋琬的收藏,言其所藏多精品,如南唐后主收藏的王献之二帖,其他如赵孟頫的帖及《百马图》、黄子久《浮岚暖翠图》、文徵仲《松下高士图》等都是难得的精品;《鬻磁杯》中的磁杯乃是隗嚣宫旧物,王士禛说此盃“内有鱼藻文”,是极罕见的汉磁。这些古董乃是宋家数代积累的结果,它们不仅是财富,更是精神上的故交与依托。“一别分明同坠井,余生今已类浮萍。”(《鬻觚》)“浑似故交零落尽,几回长叹拂吴钩。”(《鬻砚》)“纷纷轻薄迷真赝,不忍重看双泪垂。”(《鬻画》)它们已经是宋琬生命的一部分,离别之痛,自然撕肝裂肺。
宋琬笔下的监狱不仅是个苦难的符号,还是一个生动可感的现实存在。在他的诗中描写了监狱生活的方方面面,狱中也有心情略好的时候,例如这样一个春夜:
春夜吟
白日欲落不肯落,高墉传箭收鱼钥。
隔户啾啾啸且啼,人耶鬼耶然疑作?
谁云此地夜如年,欹斜之屋七九椽。
官家许住不取值,日高犹枕墙砖眠。
独不记为郎时,盎中无米恒苦饥。
羸马东风可吹倒,平明跨出犹恐迟。
这首诗可能写于第一次坐监狱之时,头两年他考中进士,在户部担任河南司主事(相当于财政部分管河南省的处长),也就是诗中所说的“为郎时”。这段生活,记忆犹新,诗人拉来与坐监狱对比。说坐监狱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放心睡觉了,即使在“天长了,夜短了”的春夏,狱吏早早锁了监号回家了,任凭号中的诗人进入梦乡,连隐隐的哭泣是人是鬼也不能干扰了。这比“起五更、爬半夜”(清代京
官上朝大约三四点钟就要起床,上衙门办公则在七时点卯)骑着匹瘦马,顶着春天的风沙上班强多了。
读书自然是愉快的,使他忘记了这里是监狱。伏天酷热,一场大雨浇灭了烈日炎炎,顺便把檐下台阶冲洗得干干净净,身心备感清爽:
雨中读书
檐溜扫阶除,濯足因及膝。
欻尔新魂清,忘其在请室。
残书代高枕,佳辰聊散帙。
古人生我前,忧乐端非一。
为乐何多方?医忧苦无术。
幽幽泣鬼神,往往托纸笔。
当时每见嗤,千载遥相恤。
我忧竟何如,辘轳井中。
此诗是讨论“何以解忧”的,他认定“幽幽泣鬼神,往往托纸笔”,读书写作不仅能够忘忧,而且上友古人,下求后世的知音。
有时苦闷极了宋琬也与呢喃的燕子或啁啾的喜鹊对话:
双燕歌
双燕复双燕,去岁春明江上见。
今年知我在罗网,飞飞万里来相唁。
忽似天涯绝域中,跫然骤得逢亲串。
支颐强起暂为欢,抚事哀歌泪如霰!
吁嗟我生太荼苦,羽毛摧剥肌肤贱。
鸿雁高翔哪肯顾?鹡鸰梦断空凝盼。
东风夜夜吹归心,故园桃李开迎遍。
燕兮少留听我语,狱吏虽苛不嗔汝。
长安挟弹多少年,汝今衔泥向何处?
……
虽然也有悲哀,但更多的还是温情。燕子仿佛是老相识了,头年开春在江南见过,现在相逢于狱中,真是空谷足音。诗中还表达了对燕子的关心。
当今浪漫的小青年称“七夕”为中国的情人节。宋琬在监狱度七夕时,写下了他与喜鹊的对话:
窟室昧昏晓,不知七夕过。
唶唶暮檐鹊,毛羽半摧磨。
见人如惭沮,敛翼坐高柯。
借问尔何为?衔尾填银河。
比如人间役,髡钳城旦科。
万古有程期,风俗非传讹。
支机石安在,牛女年几何?
鬒发何不霜?岁岁颦双蛾。
契阔展须臾,此夜停凤梭。
……
此诗很长,写得很有趣,喜鹊因为充当鹊桥,头顶磨秃了,似乎不好出门见人了,只好坐在高高树枝上与诗人对话。诗人是犯人,三句话不离本行。问喜鹊你判的是“髡钳城旦”刑吧A!借以嘲笑喜鹊的“毛羽半摧磨”。后面还写到天上牛女一年一度会面时的排场,并说天帝本来可以造一座天桥供牛女相会,但天帝还是支持牛女的鹊桥相会,目的是要喜鹊在人间传播神仙相爱的场面。
还有篇《狱中之羊赋》也很有趣:狱中来了一只小羊,它不是供宰杀的畜牲,而是与犯人一样,是待罪于囚室的“犯羊”。它也同犯人一样吃囚粮,而且配给额与犯人平等,日给三升。三升对于犯人可能不够(犯人有关伙食的一切开销都由这三升出),对小羊则绰绰有余,这只“犯羊”长胖了,宁静而驯良,仿佛它知道这里是狱吏的天地,见到他们便分外恭顺,然而这免不了骚扰和虐待,小羊也只是“应节而跽,咩然悲鸣。龁龁兢兢,似黯人声”。弱者的苦难,诗人格外悲哀。世间许多受苦人,因其不幸而愤恨外界一切人、一切物,也有人因自己的不幸反而对他者的苦难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怜悯。
牢饭对于出身世家的宋琬来说太粗糙了,难以下咽,有位忠心的刘姓仆人常到外面乞讨(大约是到宋琬熟人或友人家告帮),以改善他的伙食。一天傍晚,他拿回些粳米饭来,诗人很喜悦:“我仆行乞归,不虞明日饭。香秔白如玉,未饱身已健。”可是半夜这碗来之不易的米饭竟便宜了“耗子大爷”。“鼷鼠率其群,蠕蠕仅盈寸。噬肯念予饥,但欲充尔膳。”这些一寸大的小耗子不管不顾,从饿者口中夺食。人们愤怒了,“设罗当穴口,小童不胜懑。贪饕祸所聚,黠巧奚能遯?”老鼠虽狡猾也难逃围捕。被抓到的耗子马上显示出可怜相,“畏人仍奉首,磬折如九顿”。这些小东西立起来打躬作揖,向人赔罪。诗人心软了:“我心方恻恻,弗忍诛其困。欢然脱拘绁,三窟纵横奔。”打开羁绊,给它们一条生路吧。毛茸茸的小老鼠欢天喜地、窜回鼠洞了,枵腹的诗人内心平静了。这是《缚鼠词》写的一出小喜剧。
犯人最富有的是时间,可以从容、仔细观察平时不注意的事情,如宋琬就观察到七夕之后,喜鹊秃顶,羽毛凋零(可能是季节性脱毛),以印证老百姓关于鹊桥的传说。他笔下的小鼷鼠出来行窃与放归时动作的差别、“犯羊” 的拟人动作都是观察来的。宋琬原来诗风是承继明代前后七子,崇尚盛唐,注重格调、气象、比兴,他狱中诗则多用赋体,向杜甫晚年的格调和宋代诗风转变。
诗人两度进刑部狱,从中级官员一下成为犯人,而且犯的是涉嫌谋叛的罪行,家人亲戚跑了,而二三老朋友站了出来:
感怀五首
昔在狼狈初,金铁贯两肘。
家人乃星离,仓皇各奔走。
须臾不自谋,形骸竟何有!
急难夫为谁?赖我二三友。
谁云鲍叔牙,此义今遂朽?
这是对于故交的写照,他们义薄云天,帮他渡过难关。宋琬更幸运的是两次入狱让他新结识了一些古道热肠的朋友。
第一次入狱后,也有“平生金石交,弃我如蜣蛄(屎壳郎)”的,却有位从未谋面的朋友携带美酒来探监了,宋琬激动地写下《刘雪舫馈泉酒赋谢》。“雪舫”名刘文炤。他是皇室外戚,甲申之变,全家殉国。文炤年十五,跑了出来。清定鼎之后,刘文炤四处游走,交结明遗民。刘文炤到狱中探望宋琬或有深意。
清顺治间北京官场称“比部(即刑部)多诗人”,刑部大牢中来了一位名诗人,引起刑部风雅官员的关注。《张举之再直西省伤余在系之久赋诗志感》写道:
君在白云曹,我坐黄沙系。
送我入狱门,呼天共垂泣。
男儿患难在仓卒,叩人门户遭其嚏。
君也慷慨念畴昔,俄顷经营到纤细。
自解重裘覆我身,浆酒霍肉纷相继。
夜卧不复忧桁杨(刑具),低头稍觉安徒隶。
张举之大约是直接负责宋琬案子的,但他也是个画家,是个风雅之士(施闰章有赠给张举之诗),自然会对宋琬产生惺惺相惜之感。大难临头,亲友恐惧、躲得远远的,很难深责。即使求上门去,也会遭其“嚏”(“嚏”用得真好,它不是刻意的“唾”,但不经意的“嚏”更令上门者尴尬)。此时作为执法的官吏为犯人从衣食到狱中待遇“俄顷经营到纤细”,不能不说是个异数。我想此时刚入清不久,士人身上仍存留着我行我素,不守制度的明代习气,他们还未体会到满洲统治者的厉害。
诗人施闰章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刚刚到刑部工作就特地到狱中与宋琬订交。他为《北寺草》写的序说:“自吾好为诗,通籍而求当世缙绅,同辈得一人曰宋荔裳。既读其集数卷,悦慕之不得见。会入直西曹,见荔裳非所,大嗟异,遂定交阛墙间。”“定交阛墙”的双方如果都是犯人还可以理解,而施、宋二人身份正相反。宋琬《寄怀施愚山少参》歌颂了这种不同凡俗的友谊:“昔我陷虎吻,微躯蒙羁绁。君方拜法曹,顾余两悲咽。愧乏平生欢,定交在狱。”这在康熙以后是难以想象的。其他的刑部官员到狱中看望宋琬的还有赵宾、郜焕元等。宋琬顺治八年第一次冤狱结束后,在吏部为郎,与施闰章、赵宾(锦帆)、丁澎、严沆、陈祚明、张文元等人唱和,被称为“燕台七子”。
宋琬长于歌行,读其长歌,真有长歌当哭之感。读其监狱诗,“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绝不是一种泛泛之论。
康熙二年冬天,第二次冤狱结束后被免官,宋琬在吴浙一带生活了八年。康熙亲政之后,康熙十一年宋琬投牒自诉,其案得到彻底平反,有诏以原官起用。
(本文节选自王学泰《清词丽句细评量》 东方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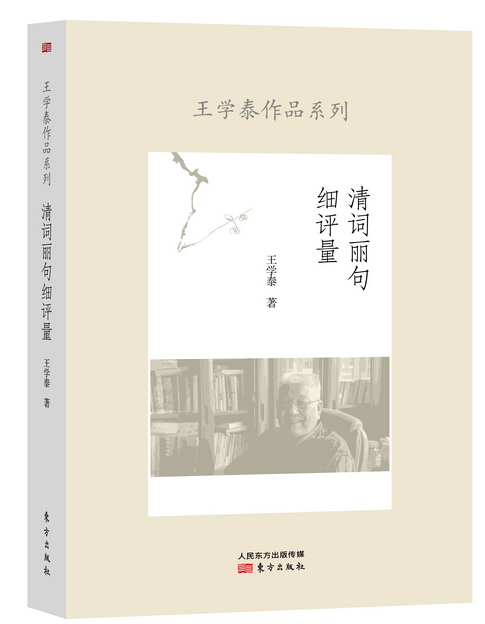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